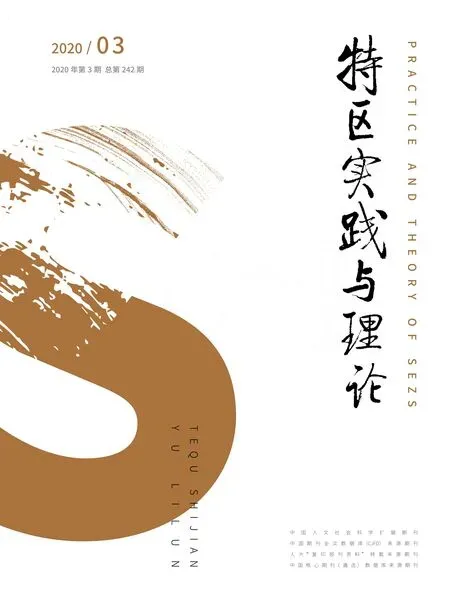在仕與隱之間
——用行舍藏、孔顏之樂與儒家“士人傳統”
林存光 徐凱旋
春秋戰國之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在政治秩序與社會結構的激變過程中新興的文士階層逐漸形成并奮然崛起,文士階層的“精神覺醒”及其“思想自由,學無拘禁”①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頁。的時代狀況最終孕育和催生了諸子異說蜂起與百家爭鳴的多元化思想發展趨勢。在此歷史進程與發展趨勢中,孔子卓然創立私學而“以師儒立教”,②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頁。可謂充當了引領時代風氣的精神領袖。孔子及其弟子后學在當時堪稱新興士人階層的杰出代表,在諸子百家中,他們不僅代表著中國上古三代以來的文化大傳統,而且在塑造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士人傳統”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主導作用。其中,以孔子和顏回(名回,字子淵)師徒為代表或由他們所引領和塑造的“士人傳統”,不僅擁有一種天然的關切和參與政治的樂政情結與家國情懷,而且堅定地秉持這樣一種具有典范意義的特殊態度取向,即他們既懷抱著一種崇高的人文理想和篤定的道德操守,堅守著一種道義擔當和經世濟民的深沉信念與政治立場,又能夠在仕與隱、窮與達之間矢志不渝地追求修齊治平的偉大目標,而且生死無悔地樂在其中。毫無疑問,這一“士人傳統”至今仍對我們有著重要而深刻的啟示和教育意義。茲就此略論一二,以求教于方家。
仕與隱:中國傳統士人的人生抉擇
在中國歷史上,由于時代的局限導致了讀書人單一而狹窄的人生出路,以至不得不在入仕做官與避世隱居之間做無奈的抉擇,成了中國傳統士人的宿命。
在后人看來,晉代采菊東籬的偉大詩人陶淵明是隱士的象征,而清新淡雅的菊花,也成了隱士高尚品格的寄托。然而,就陶淵明的一生來說,將其完全看作是一位純粹避世歸隱的詩人文士,是有失偏頗的,雖然避世歸隱可以凸顯其作為文人雅士的獨特情操,卻無法真正章明其作為一個儒家士人的內心追求與精神品格。作為一個儒家士人,陶淵明的一生可謂是在仕與隱的抉擇中痛苦徘徊,五仕五隱浮沉宦海的人生旅途,將士人心懷天下卻又無可奈何于現實的苦楚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許正因為此,一方面,面對政治現實,他不得已而選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的田園隱居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心懷蒼生社稷而切切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仕與隱,是橫亙在古代文人志士面前的一道難題,大體而言,自先秦到如今,出仕為官以實現青云之志從來都是文人志士人生奮斗的主旋律,而宦海浮沉、因厭倦權力斗爭而歸隱也是每個文人志士聊以自慰的情懷寄托所在。
仕與隱的故事在古代典籍之中屢見不鮮,而每一個故事的背后都是擺在士人面前的一道關乎著人生價值選擇的難題。在儒家經典圣書《論語·微子》篇中,曾多次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與避世隱士相遇的情境,從孔子師徒遇見隱者的故事中,我們不難推斷出那時的國家政治是如何的敗壞,以及身處亂世中的孔子師徒與憤世嫉俗之隱者們的無奈與失望。然而,他們之間卻存在著一個重要差別,即孔子師徒不愿意廢棄和背離“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不愿意像隱者那樣采取一種完全避世退隱的生存方式。盡管他們明知“道之不行”或“道之難行”,但他們卻不愿意輕易放棄行道于世的努力。不過,他們既不是簡單地拒斥入仕做官,卻也并不把入世行道的政治情懷簡單地等同于入仕做官的人生選擇。
如所周知,在中國歷史上,新型的士人階層興起于春秋戰國之世,乃是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有產物,其中孔子儒家式的士人可以說是其理想類型的杰出代表,他們生活在晚周衰亂之世,立身于仕與隱之間,汲汲于以講學、游說、諫議的方式參與政治、干預時政,以期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然而,德與位、道與勢、義與利之間的錯位、緊張與矛盾卻為講學修德的孔子師徒制造了難以化解和擺脫的精神困境,而且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中一時難以馴服和徹底改變的貴族統治階級的世襲特權以及諸侯力政、列國紛爭的時局和暴力盛行、苛政虐民的狀況,而無奈地在“道之不行”(《論語·微子》)的現實際遇中艱難地求生存,并在自身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信念的激勵和指引下努力逆行。
總的來講,孔子師徒關切政治,并試圖參與和干預時政,然而,他們既不同于那些單純地熱衷于功名富貴而“湛心利祿”的仕進之徒,同時,他們也不像周游列國途中所遭遇到的那些憤世嫉俗的隱士,唯求避世以全身。他們樂于與人同群,①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并積極思索和探求人之所以為人、群之所以為群的道理,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說法,其講學立教的核心關切可以說正是人與人如何而能夠“成社會而共生活”②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載自《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5、302頁。的問題,而這恰恰是人類社會之群居性的根本問題所在。對他們而言,恪守學與仕、講學修德與入仕為官之間的恰當分際是十分必要,亦是至關重要的。
如所周知,孔子講學立教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是培養道德人格健全、富有人文教養的從政人才,即致力于修己化人、經世濟民的士人君子。就此而言,我們只可說好學修德、修己化人、經世濟民而非“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準確地說,乃是他的理想信念或政治信仰,正唯如此,對真正的士人君子來講,講學修德相對于入仕做官來講具有根本的價值優先性。而且,在孔子看來,踐行孝悌親親之道而其影響所及能夠“施于有政”本身即是“為政”(《論語·為政》)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甚至可以說,對于孔子儒家而言,為學、從政與志道事實上是密不可分或一體相關的關系,為學即從政,從政即須道義擔當,道義擔當即意味著應造福人民大眾。盡管孔子弟子子夏嘗有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孟子亦曾講“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但學與仕畢竟是不容混同的,故荀子曰:“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荀子·大略》)相對于“仕”而言,“學”不僅具有根本的價值優先性,而且,“仕者”應遵循君子之“學”或“道”的指引和范導。故孟子又言:“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亦因此而對污漫、賊亂、貪利、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的“今之仕士者”提出了最嚴厲的批評(《荀子·非十二子》)。
綜合來講,對于權力勢位,孔子儒家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是既不鄙薄和拒斥,亦不貪求和迷戀,他們堅持“以德致位”的道德信念和政治原則,認為權力勢位的獲得和運用應服從德性和能力的原則,即權力勢位應由富于仁德修養和治理能力的士人君子掌握并加以正當而合理地運用。正唯如此,故他們深切希望并極力主張統治者治國理政應遵循“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上》)或“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的基本原則,以便能夠使具有仁德和才能的士人君子居于高位以推行和實施德教仁政。而當其面對“道之不行”的困厄和“君子之難仕”(《孟子·滕文公下》)的遭遇時,他們卻并不怨天尤人(《論語·憲問》),或者篤定地堅守“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的人生態度,或者直言不諱地嚴厲批評當世之無道和“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的狀況,甚至高調采取“以德抗位”“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和“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的抗議諫爭式政治立場。因為他們深知窮達有時或賢有不遇,①如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曰:“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知道什么是自己義所當為不當為者,什么是自己能力所無法掌控的,他們對于自己矢志不渝地努力為之奮斗的人生目標和什么才是人類共同體生活的美好愿景充滿堅定的信心,并深信應以正當的政治行為方式來實現其追求的共同體政治的理想目標。他們講學立教、“修道立德”,篤定地堅守并樂于遵循仁愛禮義的原則而采取救世的行動,既不會因得志而背離道義,亦不會因窮困而喪失志節,故孔子曰:“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孔子家語·在厄》)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曰:“遇不遇,天也。動非為達也,故窮而不(怨。隱非)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窮達以時,德行一也。”孟子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故現代學者蕭公權先生曾如是評論道:“蓋‘君子’以愛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為要君取位之真正目的。合于此而不仕,則為廢‘君臣之義’。不合于此而躁進,則為‘干祿’,為‘志于榖’。二者皆孔子所不取。故孔子譏荷蓧丈人為潔身亂倫,而復嘆仕為家臣者之無恥。孔子自謂其‘無可無不可’,正足見孔子不拘執于必仕必隱,而一以能‘行道’與否為出處之標準。”②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8-39頁。在我們看來,這一評價無疑最中肯且精準切中了孔子儒家式士人君子的真實用心所在。
“用行舍藏”與“孔顏之樂”:孔顏師徒超然獨立的人生信念與心靈境界
在我們看來,只有對孔子儒家式士人君子的真實用心深有體會和領悟之后,我們才會真正理解孔子何以謂顏淵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據《孔子家語·六本》篇,“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待祿,慎于治身”。意即“顏回具備君子的四種品德:實行道義時很堅強,接受勸諫時很虛心,得到官祿時戒懼而警惕,立身行事時很謹慎”。①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186頁。另據《致思》篇,顏回曾自述其志曰:“回愿得明王圣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斗之患。”在孔門弟子中,顏回品德高尚,為孔門四科中德行科之首徒,其志向之高遠殊非其他弟子所能比。而且,顏回既懷抱著治平天下、造福人群的遠大理想與政治抱負,又能夠深明窮達有時、無怨無悔地依乎仁道而行,故當孔子師徒困于陳蔡之際時,弟子中亦唯顏淵能夠深切理解孔子當時的處境與內心的想法,其言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正唯如此,亦唯有顏回之仁德與好學深得其師孔子的贊賞與好評,如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
在孔門弟子中,唯顏回能夠與其師孔子最為靈犀相通而志同道合,而且,亦唯有孔顏師徒在得志時能夠本著自己的初心而推行其遠大的政治理想與抱負,不得志時亦能守其初心、藏道在身以待時。②錢穆先生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曰:“有用我者,則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則藏此道在身。”“身無道,則用之無可行,舍之無可藏。用舍在外,行藏在我。孔子之許顏淵,正許其有此可行可藏之道在身。有是夫是字,即指此道。有此道,始有所謂行藏。”(《論語新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58頁)。對此,孟子亦最能心領神會,故有震古爍今之名言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總之,孔顏師徒之真實用心,即在用行舍藏之間,既不屑屑于躁進求仕以干祿,亦不憤憤然避世退隱以廢倫,而唯以能“行道”與否為行止出處之標準,其中透顯出的正是一種堅忍不拔的人生信念與超然獨立的大丈夫氣概。
孔顏師徒身處無道之亂世,他們當然知道自己面臨著什么樣的政治際遇,對于“道之不行”“君子固窮”與“君子之難仕”的生存困境更有著自覺而明確的意識,但他們能夠坦然地面對、看待和接受自己所處的客觀情勢與遭際命運,并愿意為改變整個時代的處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乃至不論處于什么樣的遭遇和境況之中,他們亦都能夠始終保持著一種曠達而樂觀的心靈平靜。孔子一生只有短短數年入仕為官的機會和經歷,入仕為官的挫折并沒有使孔子喪失信心,反而激發了他周游列國、以道救世的激情和熱忱。盡管孔子有時也曾表露過歸隱的念頭并無奈地感嘆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而且,他對那些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士人表達過自己的嘉許贊賞看法,如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孔子家語·六本》)但身處無道之亂世的他事實上卻從未放棄過以道救世的努力。當然,這一努力主要是通過講學立教、游說諫議的方式來實施的,而且,孔顏師徒樂在其中。故孔子自述其為人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并如是評價顏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面對仕途的挫折和富貴利祿不可求的現實際遇或者簞食瓢飲的陋巷生活狀況,孔顏師徒又何以為“樂”、何以能“樂”呢?世俗之人以富貴利達或仕途得意為樂,反之,富貴利祿之不可求或仕途失意乃是其最“不堪其憂”者,故在這一方面孔顏師徒無疑是相當“失敗的”,然而,殊不知孔顏師徒卻別有其憂與樂所在,他們對這方面的失敗毫不在意,乃至即使身處最艱危的生存困境之中卻仍然能夠“弦歌不輟”或“不改其樂”,因為其憂在“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而其樂卻在其志道修德而好學不厭的人生價值追求與自我實現過程。換言之,孔顏師徒之“樂”,可以說是他們在通過好學修德、改過遷善的方式而致力于不斷提升和完善自我德性人格、實現自我人生價值與意義的不懈努力中所達致的一種心靈的平靜與安寧、喜悅與快樂,體現了一種“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超然獨立于窮與達、貧與富、貴與賤、仕與隱之間中道而行、圓融無礙的心靈境界。故“孔顏之樂”,亦即是君子之樂,好學之樂,師友相得之樂,群居講學、修道立德之樂,內省不疚、俯仰無愧之樂,藏道在身、無入而不自得之樂。
以孔顏師徒為典范的儒家“士人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乃是一個內部構成最為復雜的特殊群體,他們性情各異、志趣相左、品類不齊、或仕或隱、或窮或達,可謂千差萬別,即使是孔門弟子亦是如此。而就其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態度而言,如果我們可以把他們放到同一個光譜上來加以定位和分析的話,那么,躁進以干祿或唯權勢之嗜而不顧道義的功名利祿之徒便屬于這一政治光譜的一極,蔑視權勢而拒絕入仕的隱者則屬于另一極,在這兩極之間還有各種各樣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其中,孔顏師徒所代表的應該是政治立場和態度最為特殊的一個士人類別。對此,我們唯有從其所秉持的道德理想信念的角度,才能獲得一種更好的理解和體認。
如果說孔子儒家“以教為政”而“其目的在兼善天下,使人人皆有‘成人’之機會”或“以個人道德之發展為政治之最高理想”,①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40頁。又或者孔子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與唯一手段,不外將國民人格提高”,故“以目的言,則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則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②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12頁。那么,孔子終身所從事的講學立教或“以教導為人大道為職業”③錢穆:《孔子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2頁。的私學教育活動,在孔子儒家之“政治”的意義上,事實上也就是一項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政治活動。易詞言之,孔子雖未入仕為官,但卻是在從事一項真正意義的政治事業。因此,孔子雖然并不簡單地蔑視權力勢位而拒絕入仕為官,但亦決非屑屑于躁進干祿或單純地熱衷于入仕為官之徒,故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我們切不可誤解了孔子此言的意思,富貴利祿不可求而“從吾所好”者,非今人所謂業余愛好也,乃是指孔子所意欲從事的講學立教、“以教為政”的真正政治事業。據此而言,我們亦可以說,孔子在世俗的利祿仕途或純粹的權力政治領域之外或之上,實則開辟出了一個士人君子從事真正的道義性政治事業的公共空間與理想世界,而且,用行舍藏而并“不拘執于必仕必隱”的孔顏師徒以其堅忍不拔的高尚品格和超然獨立的大丈夫氣概自覺擔負起了這一道義性政治事業的衛道士和領路人角色。盡管他們僅憑自己一時的努力無法從根本上阻止乃至徹底扭轉現實權力政治日趨于暴力化和功利化的發展趨勢,但從長遠來看,他們卻奠立了這樣一種極富深遠意義的儒家“士人傳統”。誠如韋政通先生所言,“孔子是因堅持以道自任和‘士志于道’的理想,才使他無法被時君所用,才使他四處碰壁,甚至有時候連生活都過得很凄慘,但他并未因此而喪失熱情與自信。正因為他對自己理想的堅持,才為中國文化建立起一個用世不用世并不能決定人格價值及其歷史地位的新標準,因而開啟了一個人可以不用世,仍然可以有人生奮斗的目標,仍然可以有偉大的理想,仍然可以賦予人生以豐富的意義,仍然可以享有歷史崇高地位的士人傳統”。①韋政通:《如何研讀〈論語〉》,載自《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選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頁。
世俗之人常常誤解孔子師徒是“熱衷于仕途”,并將仕途與政治混為一談,且據此認為孔子一生在政治上是最失敗的。其實,與其說孔子熱衷于仕途,不如說他熱衷于關切和參與政治,而其目的在行道以救世,在亂世中難以實現其救世的理想固然是一種“失敗”,但這與仕途的挫折與失意卻是兩回事。前一種“失敗”在一定意義上更加彰顯了孔顏師徒在亂世中“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和矢志不渝、努力為理想而奮斗的可貴精神和獨立志節,這是一份最可貴的精神遺產。他們由此而樹立了一種新標準,讓人們明白這樣一種人生的道理,即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并不在于其是否用世即仕途遭遇的窮達順逆,不取決于其生活條件和身份地位的貧富貴賤,亦與一個人的壽命長短無關,而在于其志向之遠大抑或屑小、人格之高尚抑或卑下,亦即取決于一個人的德性修為如何;他們由此而開啟了一種影響深遠的“士人傳統”,一種“一個人可以不用世,仍然可以有人生奮斗的目標,仍然可以有偉大的理想,仍然可以賦予人生以豐富的意義,仍然可以享有歷史崇高地位的士人傳統”。正唯如此,孔顏師徒生前的“失敗”亦可以說恰恰成就了他們在后世的歷史崇高地位,至于仕途的窮達順逆卻是無關宏旨的,亦不是孔顏師徒所根本在意的,孔顏之為孔顏就在其用行舍藏而“弦歌不輟”“不改其樂”。
由孔、顏師徒所樹立和開啟的“新標準”與“士人傳統”在后世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在此,我們僅從“用行舍藏”和“孔顏之樂”兩個方面略論一二。
就“用行舍藏”一方面講,在經歷了秦皇的焚書坑儒和漢武的表章尊崇之后,儒生士人似乎在“用”的方面最終贏得了勝利,通經入仕和科舉取士制度的實行也為此提供了政治上的可靠保障,然而,問題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樣簡單,事實上他們卻不得不面對“儒之(仕)途通而道亡”(清方苞《望溪文集·又書儒林傳后》)或者欲“得君行道”而不能的困境,而且,在現實而世俗的仕途勢利場中,從來或唯一不缺少的就是那些曲學阿世、面諛以得親幸與富貴的權力順從者和功名利祿之徒。比較而言,只有那些身處無道之亂世或身在仕途勢利場中而仍然能夠恪守和堅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人生態度和立場的儒生士人,在其身上才真正體現出孔顏師徒“舍之則藏”的真精神、真血脈,只有他們能夠薪火相傳而將此真精神、真血脈維系于不墜而賡續不絕。
而就“孔顏之樂”一方面講,可以說至宋代理學思潮興起而得到了真正的發揚光大。如果說“理學本質的核心是一種信仰——自覺地獻身于某種信念,而不是哲學的陳述或不經明確表述的假設”②[美]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新加坡]王昌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71頁。的話,那么,理學思潮就是一種自覺地獻身于“學為圣人”這一人生信念與使命的思想運動,因為理學家將儒學看作是一種圣賢學問,而且,他們普遍相信士人君子可以通過“學”實現自我的轉化以成圣成賢。正如程伊川在《顏子所好何學論》一文中所言:“圣人可學而至與?曰:然。”而“圣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圣人之道也”。③程顥、程頤:《二程集(上冊)》,王孝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77頁。盡管程朱和陸王的理學思想存在諸多歧義,但不管怎樣,“學為圣人”或“圣人可學而至”作為一種人生信仰,卻構成了他們學術思想共同的核心議題或中心主題。那么,究竟應如何才能具體而切實地學以至圣人呢?他們的共同看法即是以顏子為榜樣或準的。如二程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圣人為近,有用力處。”“只學顏子不貳過。”“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為準的。”④程顥、程頤:《二程集(上、下冊)》,王孝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9、97、1184頁。陽明亦如是說:“見圣道之全者惟顏子。……顏子沒,而圣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圣學真血脈路。”①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2、97頁。顯然,宋明理學家以顏子為榜樣或準的主要是學習顏子的“不貳過”,目的是以顏子式改過遷善的篤實工夫作為最切近有用的入圣門徑,并將此視為是“圣學之正派”或“圣學真血脈路”。
而更加饒富意味的是,宋明理學家還特別提出了一個具有深刻而神秘之人生體驗意味的“孔顏之樂”命題,最初提出這一命題的是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周子不曾說破“孔顏之樂”乃至后人祕其事而謂不可言傳,無疑使“孔顏之樂”蒙上了一層神秘體驗的意味,至于孔顏所樂者究竟在仁在道,在我們看來卻并無實質性的差別,因為對孔顏師徒而言,仁即是道,道即是仁,仁與道是一非二。然而,如陳植所言,就孔顏師徒由“樂”而體現出的圣賢氣象而言,所謂的“孔顏之樂”,與其說其所樂在仁或在道即以仁或道為樂的具體對象,毋寧說體現了其為學成圣過程中的一種精神上的所得,即在立志于求仁行道或在追尋和踐行仁道的人生追求與生命歷程中而彰顯出的一種圣賢人格的精神氣象。換言之,如果我們理解不錯的話,我們大可不必將此圣賢人格的精神氣象“祕其事”而視作是一種神秘的人生體驗,事實上它體現的是一種以志于仁或志于道為精神動力,以“學以至圣人”為人生使命與目標,發自內心深處、真實而深刻的安寧、平和、喜悅和快樂的生命體驗與心靈狀態。陽明師徒亦曾討論“孔顏之樂”的問題,陽明將“樂”視為“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的“心之本體”,乃至認為是“雖則圣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者,②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4頁。這無疑將孔顏之“樂”本體化了,固然是一種別具意味的創見新解,但不管陽明這一見解的用意為何以及其良知學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意義,在我們看來,這其實亦將作為一種圣賢之“真樂”的“孔顏之樂”常人化了,即從本體論的意義上將圣賢與常人之間在人格品行與精神境界上的分際與差別輕易地拉平或消解掉了。事實上,我們仍然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何為圣賢別有之“真樂”?我們還能否對此有一種真實而深切的理解與體認,乃至在圣賢之“樂天知命”或“安貧樂道”與常人之消極地順從命運安排、無奈地過一種貧苦生活的實際際遇之間作出一種有意義的明辨區分?我們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而且認為二者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圣賢有著不同于常人的遠大志向、高尚品格、德性修養與人生目標追求。正是基于這樣的區別,我們認為韋政通先生對“孔顏之樂”的下述解說可以說深刻揭示了“孔顏之樂”作為圣賢之“真樂”的真實含義,即:宋代理學家有教人尋找孔顏樂處的,照“喜悅是美德”的話來了解,孔顏樂處,不必如程伊川所說是在所樂的對象上,而是因為對生命的熱愛所產生的喜悅,喜悅本身就代表一種道德的光輝。這種喜悅,不假借于名位,不托附于財富,它來自于健康的心靈,所以孔子可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顏子雖居陋巷,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依然能不失其內心的悅樂。③韋政通:《人文主義的力量》,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79-180頁。
依韋政通先生之見,只有從“因為對生命的熱愛所產生的喜悅”或“不假借于名位,不托附于財富”而純粹“來自于健康的心靈”的“內心的悅樂”的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和領會“孔顏之樂”的真實含義。而在我們看來,我們只有對此有了真實而深切的理解和體會,才能更好地來認識和看待孔顏師徒用行舍藏的人生信念對于宋明理學家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專制君權日益加強和科舉取士制度全面實行的時代,同樣面臨著道與勢、義與利、用與藏、學與仕、做官與從政的緊張與抉擇。為了化解由此而帶來的精神壓力,使自己能夠像孔顏師徒那樣篤定地恪守和堅持用行舍藏的立場,用則“致君堯舜”“得君行道”,舍則講學立教、“立言明道”,既“不假借于名位,不托附于財富”,而且尤其能夠不畏不懼于至尊君權的威勢而堅信道義的力量和天理的信仰終將戰勝一切、永恒不滅,并始終懷著一顆真摯樂觀的心態以孜孜追尋“孔顏之樂”,這是宋明理學家最值得我們同情和贊許的地方。沒有對“孔顏之樂”的真實而深切的精神修為與人生體驗,他們不可能像孔顏師徒那樣篤定地持守用行舍藏的立場,反之,沒有對用行舍藏立場的篤定持守,他們也不可能樂于追尋和體驗“孔顏之樂”的真義。正是他們通過“篤志圣學”的思想努力和“學為圣人”的人生實踐,使孔顏師徒成為士人學者普遍學習和效法的人生楷模,乃至使以孔顏師徒為人格典范、精神標桿和入圣準的的“士人傳統”在宋明時代得以真正地發揚光大而對士人學者產生了最廣泛、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結語
今日,我們再來重新審視和反思孔顏師徒用行舍藏的人生信念、內在心靈之“樂”的圣賢氣象以及由其精神人格所范型和塑造的“士人傳統”,究竟還能帶給我們一種什么樣的啟示和教益?
在當今社會,我們已很難想象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會像古代隱者那樣隱居山林湖澤,親自躬耕漁獵,時代條件讓這樣的生活幾近乎絕跡,而且現代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樣化的職業選擇與人生道路,也使他們不必再像傳統士人那樣必須也只能在仕與隱的兩條人生道路之間做選擇。盡管如此,如果說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環境中依然還存在著難以消解的德與位、道與勢、義與利、學與仕、窮與達之間的張力性生存困境并需要人們做出正確抉擇的話,那么,在我們看來,孔顏師徒用行舍藏、身處困境而“弦歌不輟”“不改其樂”的人生態度和由此而彰顯出的那種崇高的人文精神與道德政治理想,以及由他們所型塑、以他們為典范的儒家“士人傳統”,在今天就仍然是富有教益的,仍然對于個體生命的選擇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人生“第一等事”,究竟是“讀書登第”或入仕做官,還是“讀書學圣賢”或立志“做圣賢”,①王守仁:《王陽明集(下冊)》,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25頁。這是古代讀書人當捫心自問的一個人生大問題,亦同樣是現代讀書人當捫心自問的一個人生大問題。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做人就要做舜那樣的圣人,這不僅對古代讀書人有激勵作用,對現代讀書人亦同樣有激勵作用。
在學與仕的人生選擇中,究竟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還是“學而劣則仕,仕而劣則奔競鉆營”;在仕途之沉浮、官場之勢利的現實遭遇中,究竟是“用則以身行道,舍則藏道在身”,還是“用則嗜權貪利,舍則怨天尤人”。宋儒程顥有詩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②程顥、程頤:《二程集(上冊)》,王孝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82頁。唯有對此作深切反思而能度越前人,吾人斯乃可充滿信心地展望現代知識分子之未來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