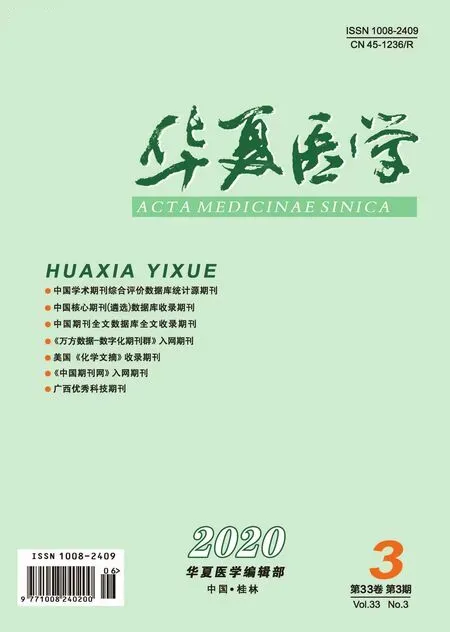外周化療性靜脈炎的發病機制及防治進展①
容桂榮,文瓊仙
(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廣西 桂林 541001)
靜脈給藥為化療最常用的給藥方式,但化療藥物對血管壁的局部刺激可引起靜脈炎。有資料顯示,化療藥物輸液性靜脈炎發生率可達50%~70%[1]。盡管臨床工作者進行了多種嘗試,如經外周靜脈的深靜脈置管(PICC)、鎖骨下靜脈置管等[2-3],但當這些置管有禁忌證時,靜脈炎的預防還需要依靠化療前、后血管保護藥物的應用、給藥部位冷、熱敷以及局部給予糖皮質激素、非甾體抗炎藥、抗組胺藥、局部麻醉藥、抗凝溶栓以及活血化瘀類等藥物外敷的措施[4]。即便如此,但由于缺乏相應基礎研究支持,使這些措施針對性不強,作用機制不確切,給藥劑量、方法及時機不明確,臨床效果不明顯,同時當出現靜脈炎后,種類繁多的處置會使患者治療成本進一步上升,因此臨床上有時為了避免其發生,甚至不得不減少輸液給藥而延誤治療。
1 外周化療性靜脈炎的定義
靜脈炎是指輸入高濃度、刺激性強的藥物或靜脈內長期放置刺激性較大的輸液導管而引起局部靜脈內膜的炎性反應,包括在輸液過程中護理人員操作不規范引起局部靜脈損傷與感染[5]。外周化療性靜脈炎是指在外周靜脈輸注化療藥物引起的靜脈炎。臨床表現為輸注藥物后輸液部位沿靜脈走向出現條索狀紅線、疼痛、觸痛、紅腫、血管外觀改變等兩種或兩種以上癥狀[6-8]。靜脈炎在病理學的表現[9]:通過HE染色,光鏡下可觀察到不同程度的血管內皮腫脹、血管周圍水腫、炎細胞浸潤、血管擴張、管壁增厚、管腔充血、周圍血管出血、纖維增生、血栓形成等表現。化療性靜脈炎發生的嚴重程度,主要與化療藥物的刺激性有關。化療藥物根據輸液外滲后對局部皮膚的損害程度,分為發泡劑、刺激劑和非刺激劑3類。如吡柔比星(THP)是常用的發泡劑類化療藥,屬蒽環類廣譜抗腫瘤藥,該藥對急性白血病、惡性淋巴瘤、頭頸癌、尿路上皮癌、乳腺癌、卵巢癌、子宮癌、胃癌等有較好的療效[10],但對血管刺激性大,外周靜脈注射一旦滲漏于血管外,可引起局部皮膚及軟組織的化學性損傷[11-12]。THP引起靜脈炎常見原因為[13]:藥物pH值為5.0~6.5,偏酸性,可干擾血管內皮細胞正常代謝和機能,藥物濃度高,輸入速度快,超過了血管緩沖應激能力,或在血管受損處堆積,均可使血管內膜受刺激導致靜脈炎的發生。此外,吉西他濱、順鉑、諾維本等發泡劑類化療藥靜脈注射時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靜脈炎[14]。
2 化療性靜脈炎的發病機制
Lu等[15-16]通過動物實驗方法發現化療性靜脈炎形成過程中炎癥發生是必然存在的,作為血管無菌性炎性反應,化療性靜脈炎發生涉及血管內皮細胞損傷,血管壁及周圍組織炎性細胞浸潤,周圍組織水腫甚至炎性反應,血管血栓形成等病理改變。雖然目前相關機制尚未完全清楚,但近年來對抗炎新靶點的深入研究為解決本問題帶來了很多啟發。Watanabe 等[17-18]發現,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白介素-1(IL-1)、白介素-6(IL-6)、內皮細胞表達細胞間黏附分子(ICAM-1)等是重要的早期炎癥因子,在促炎癥因子脂多糖的刺激下,心、肺、腎等組織TNF-α的mRNA表達顯著增加,血中極低濃度的TNF-α就可激活庫弗斯細胞、中性粒細胞、血管內皮細胞等造成肝和其他組織損傷。近期更有研究證實[19],TNF-α和IL-1均可以引起血管內皮細胞損傷。Takeda[20]在內毒素、免疫復合物和物理因子引起的炎癥反應研究中,通過上調內皮細胞黏附分子ICAM-1,促進嗜中性粒細胞表達CD11b/CD18,從而增強白細胞與內皮細胞的黏附,促進白細胞的滲出。
3 化療性靜脈炎的防治
Carbone等[21]通過研究發現,許多化學介質參與血管損傷修復過程,其中包括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黏附因子、一氧化氮(NO)等。VEGF是生長因子家族中最強的促血管內皮細胞有絲分裂原,可強烈而特異性地促使血管內皮細胞分裂增殖,促使血管新生,在創面愈合中起著重要作用,并認為它是局部血管通透性增加和新生血管形成的主要調節因子,與傷口部位肉芽組織形成有關。
葉麗紅[22]應用碘伏聯合馬應龍麝香痔瘡膏外敷治療外周輸液性靜脈炎,與50%硫酸鎂濕敷相比,總治愈率分別為75%和13%,其原理與馬應龍麝香痔瘡膏含人工麝香酮、人工牛黃、珍珠等藥理成分有關:麝香酮有活血通經、消腫止痛的作用,牛黃、珍珠等有不同程度活血化瘀的功效。與該研究相對應的基礎研究中,Liang等[23]就麝香酮在治療血管炎癥機制方面取得了進展,證實麝香酮可抑制大鼠IL-1β和TNF-α、COX-2、iNOS、NO等炎癥因子的產生,對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ERK1/2和c-Jun氮末端激酶JNK信號通路有明顯抑制作用;該實驗還表明,10 mg/kg的麝香酮可顯著降低大鼠TNF-a、IL-1β、前列腺素E2(PGE2)和6-酮前列素F(6-K-PGF1a)水平;此外麝香酮還能明顯抑制血管內皮細胞與中性粒細胞黏附及其表面ICAM-1和VCAM-1的表達,從而抑制中性粒細胞黏附血管內皮細胞,發揮抑制炎癥反應作用。王安素等[24]用喜療妥乳膏涂抹與50%硫酸鎂濕敷治療靜脈炎進行了Meta分析,納入2007~2014年的21個研究,共計1 669例靜脈炎患者,證實喜療妥總有效率和治愈率均高于硫酸鎂,分析喜遼妥為多磺酸基黏多糖類,具有很強的抗炎、抗凝血、抗血栓、抗滲出、促進傷口愈合及緩解疼痛的功效。潘春玲等[25]應用利百素涂抹的方法來預防外周化療性靜脈炎,與空白對照組比較,在化療第四療程結束后,靜脈炎發生率分別為18%和84%,認為其預防機制與藥物成分中的七葉皂苷和二乙胺水楊酸有關:七葉皂苷有抗炎、抗滲出、抗水腫、改善局部血液循環等作用,二乙胺水楊酸具有抑制前列腺素、白三烯等炎癥介質的作用。王硯麗等[26]使用水膠體和喜遼妥合用與單獨使用喜遼妥涂抹來預防PICC 化療性靜脈炎,結果在化療3個療程后,兩組靜脈炎發生率分別為31.7%和55%,認為與水膠體良好吸收性和自黏性輔助喜遼妥發揮作用有關,水膠體可刺激釋放巨噬細胞及白細胞介素,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從而減少疼痛和靜脈炎的發生,但其結論沒有得到基礎研究支持。諶永毅等[27]將216例肺癌初次行諾維本化療患者隨機分3組,在外周靜脈注射藥物后,分別使用康惠爾潰瘍貼、自制青黛、肝素鈉軟膏3 種不同藥物外敷,結果化療第一療程結束時靜脈炎發生率康惠爾潰瘍貼組為23.94%,青黛軟膏組為37.50%,肝素鈉軟膏組為32.88%,低于張超男等[28]同樣化療方案靜脈炎發生率(93.3%),說明3種方法均可降低靜脈炎的發生率,原理與所用材料和藥物都有不同程度改善局部組織微循環、活血化瘀、通經止痛等作用有關,然而該研究也未獲得基礎研究的支持。
綜上所述,外周靜脈輸注化療藥物可致靜脈炎的發生,其機制主要與藥物的pH值、濃度、輸液速度等因素有關。TNF-α、IL-1、IL-6和ICAM-1等是重要的早期炎癥因子,在外周化療性靜脈炎的發生機制中起重要作用。在臨床防治方面,主要開展了水膠體、中成藥、各類活血化瘀藥等局部外敷實驗并取得了一定療效。盡管目前化療性靜脈炎防治的臨床與基礎研究都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大多以獨立研究為主,鮮有臨床與基礎研究相結合的復合性研究,這導致其研究成果的推廣受到一定影響。未來在化療性靜脈炎防治研究中,應在臨床研究基礎上加強基礎實驗研究,進一步規范靜脈炎防治方法,減少因靜脈炎給患者帶來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