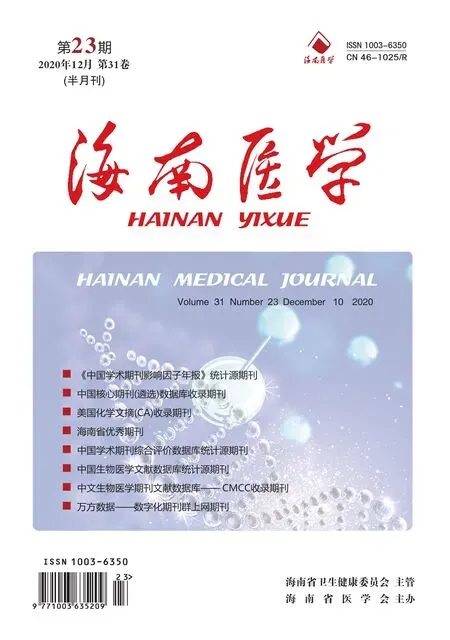卒中后抑郁發病機制及臨床表現的研究進展
呂易坤 綜述 劉安祥,張駿 審校
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神經內科,貴州 遵義563000
腦卒中是多種腦血管疾病的嚴重表現形式,具有高發病率、高致殘率和高死亡率的特點[1],是世界上第二位的致死病因,也是致殘率最高的疾病[2]。近年來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越來越多地受到關注。有研究證實首次腦梗死3個月后約41.1%的患者會發生PSD[3]。PSD 嚴重威脅著腦卒中患者的生命健康,相關數據顯示其致殘率和病死率高達70%~90%[4],同時也給腦卒中患者及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能夠早期識別PSD 并對其進行早期的診治對降低PSD患者的死亡率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進一步了解探尋PSD 的相關發病機制及臨床表現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將對PSD 相關的發病機制及臨床表現做一綜述,提高臨床對PSD 的認識,從而更好地指導PSD的防治。
1 發病機制
1.1 社會心理學機制 腦卒中患者的生活質量會有嚴重的下降,在發病過后會遺留的諸多問題在一定程度給患者造成了心理負擔,從而加速了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的發生與發展。如自理能力的下降、勞動能力的喪失、社交能力的受限、認知功能的下降、家庭負擔的增加、吞咽困難、言語不利及外貌的變化等問題。認知功能障礙、社會的支持度較低、個人收入的不樂觀以及既往腦卒中病史均是PSD發生的危險因素[5]。研究顯示發生抑郁后的患者軀體和社會功能明顯下降,患者的疾病復發率和死亡率上升,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神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進而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6]。腦卒中后容易導致PSD的發生,反過來PSD也會加重腦卒中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進而延緩患者腦卒中后的康復進程[7]。
1.2 多種因素共同影響機制 個人生活習慣、腦卒中病灶的大小及部位、環境的變化以及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等影響著PSD 的發生發展。研究發現抑郁史、近期負性生活事件、家庭不和諧、婦女、多發性腦卒中病變患者、合并復雜疾病、非妻子護理和前部病變等因素對腦卒中患者后期是否會出現抑郁現象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差異[8]。然而對于上訴諸多因素對于PSD 的發生是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排除這些因素是否可以影響PSD發生?現在的研究數據尚不足,需要進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因素在參與PSD的進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臨床存在上述PSD潛在危險因素的腦卒中患者要做到早發現、早診斷及早治療。
1.3 神經內分泌機制 目前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神經遞質假說是抑郁障礙的可能發生機制,PSD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抑郁狀態,其也存在著多種神經遞質的改變,無論是神經遞質傳導通路的破壞還是神經遞質釋放的增加或減少都可能是由于腦卒中病灶直接引起相應損害損失部位發生的神經遞質紊亂導致。
1.3.1 單胺類神經遞質 單胺類遞質的代謝與急性腦卒中的發生引起神經組織受損害程度有著密切關系,單胺類神經遞質的變化或相關系統功能障礙與抑郁癥的發生也有著密切的關系[9-12]。研究發現腦卒中后腦內的5-羥色胺(5-HT)、去甲腎上腺素(NE)和乙酰膽堿(Ach)神經遞質的異常變化與抑郁情緒的發生有關[12]。此外,SCHILDKRAUT等[13]與ANDERSEN等[14]早期也提出了一系列學說認為腦卒中后神經遞質的改變與抑郁發生密切相關。PSD 與腦卒中部位存在明確關系,在大腦左側半球、前部、皮層和多發病灶區域易發生PSD[15]。一項臨床研究發現抑郁的腦卒中患者的血漿及腦脊液中單胺類神經遞質低于非抑郁的腦卒中患者,左前病變患者的血漿和腦脊液中單胺類神經遞質的水平低于左前病變患者,前病變患者血漿和腦脊液中單胺類神經遞質的水平較低[16]。綜上,PSD發病率與腦卒中病灶有著密切的關系,腦卒中患者單胺類神經遞質降低的程度與腦卒中病灶定位有關,不同部位的損傷單胺類神經遞質的降低有著不同的變化。
1.3.2 神經營養因子 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是神經營養因子的一部分,是中風后神經元再生的關鍵因素。研究表明BDNF 與PSD 的發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17-18]。傅曉燕等[19]發現在PSD 大鼠模型的海馬中BDNF 的過度表達可以減輕PSD 的抑郁感,發揮出神經保護功能。對PSD 模型大鼠進行抗抑郁藥物干預后發現大鼠的抑郁癥狀減輕,并且檢測海馬中的BDNF 蛋白表達也明顯增加[20]。趙軻等[21]研究發現血清中的BDNF 表達水平與焦慮呈負相關,BDNF 在血清內的表達水平是抑郁癥的一項重要指標,可作為PSD早期發現和預防的重要血清生物標記物。綜上,BDNF 與PSD 存在密切聯系,是PSD 預后良好的一個重要指標,BDNF 的進一步研究可能成為PSD 患者的一個潛在治療靶點。
1.3.3 炎性因子 發生缺血性腦卒中后主要的血清炎癥因子會升高,且與病情的嚴重程度成正相關[22]。在腦卒中患者疾病進展過程中,炎性因子發揮著重要功能,PSD 作為腦卒中患者的常見并發癥之一,患者血清炎癥因子的變化是否與PSD 的預后有相關性?康笑等[23]通過研究發現PSD模型大鼠的血清中的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胞介素1β (IL-1β)含量明顯增加。PSD 患者血清部分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超敏C-反應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TNF-α水平顯著升高,并且在輕度、中度、重度抑郁患者血清中的水平依次升高,提示上述炎性因子可能參與PSD 的發生發展,并且水平不同的高低反映PSD 患者抑郁程度[24]。另外還有證實腦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清中白細胞介素10 (IL-10)明顯低于健康者,而hs-CRP、TNF-α、IL-1β、IL-6、IL-8均明顯高于健康者[25]。因此,上述研究提示炎癥因子的變化與PSD的發生發展相關,但各類炎性細胞因子在PSD 中怎么樣發揮作用以及各炎性細胞因子之間在PSD中的相互作用需要進一步研究。
2 臨床表現
PSD 臨床表現多樣,在認知功能方面曾有研究發現腦卒中后抑郁會加重患者認知功能障礙,患者抑郁狀況與認知功能呈負相關[26]。《卒中后抑郁臨床實踐的中國專家共識》[27]將腦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癥狀分為核心癥狀和非核心癥狀,其中核心癥狀一般表現為精力的減退、對事物或事情不再提起興趣、成天悶悶不樂、郁郁寡歡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等,而非核心癥狀則表現為體質量減輕、失眠多夢、焦慮及自責等其他表現。張瑛[28]選取了100多例臨床腦卒中患者作為觀察組且將其分為無抑郁、輕度抑郁、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4 個等級,再將這些患者按照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分為輕度功能缺損、中度功能缺損及重度功能缺損3 個等級,后將抑郁程度與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對應起來研究抑郁發生的嚴重程度與腦卒中損傷部位的關系,最后研究發現腦卒中患者缺損程度越嚴重,抑郁發生率也就越高。此外,吳祖舜等[29]在對299 例PSD 患者研究中按照臨床表現和Hamilton 抑郁量表評分將這些患者共分為輕、中、重度抑郁癥,觀察發現輕度抑郁癥患者主要表現為頭痛失眠、過度思慮、注意力不集中等;中度抑郁癥患者主要表現為言語減少且說話緩慢、內心情緒的不穩定、衣衫不整等;而重度抑郁癥患者則表現為內心極其絕望、不言不語、曾出現自殺的想法或者要求安樂死等。綜上,PSD患者在臨床表現上一定程度會受到神經功能缺損程度的影響,PSD的核心癥狀與非核心癥狀在不同患者中的表現比較相似,而對于其他非典型表現來說,由于體質及患病程度的不同,PSD患者在細微臨床癥狀上可存在不同的差異。
3 診斷
在臨床中對于PSD 的診斷大多都是結合卒中病史及抑郁的表現,加以相關量表的評分進行診斷。目前研究中主要涉及的量表包括自評量表和他評量表,其中自評量表包括Zung 抑郁自評量表(zung 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流調用抑郁自評量表(center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9項患者健康問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等;他評量表包括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蒙哥馬利抑郁量表(montgomery?asberg depression scale,MADRS)等[28,30]。在精神障礙的診斷和分類系統中,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PSD診斷和分類標準,國內外專家就PSD的診斷到目前尚未達成一致共識,一貫對于PSD的診斷都是套用抑郁癥的相關診斷標準或臨床量表,在實際臨床工作中,卒中患者功能往往受限,給臨床的評估造成了困難。由于PSD 診斷標準的不明確,部分臨床醫師不能及時、正確識別而耽誤患者治療,導致預后不好。因此,國內外統一PSD 診斷標準及標準化的臨床評估量表是目前臨床需要解決的問題。
4 結語
PSD 患者的臨床表現多種多樣,腦卒中不同病灶、不同程度抑郁均會造成不同的臨床癥狀。就PSD癥狀而言,有著個體差異性表現,而首發癥狀與診斷必要條件需要更合理的制定。
目前就PSD的發病機制并未有一個明確的共識,現在僅僅存在著可能的機制或學說。想要全面研究PSD 發病機制,需要從抑郁與腦卒中兩方面入手,并不僅僅是一個單獨的聯系,復雜且繁瑣,其生物學的異常及神經遞質間的相互聯系涉及到體內的多個系統,僅僅單一的從某個系統或者某一方面的發病機制入手不能得到完美的闡述,也不能進行完整的表達。PSD在神經生物學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但并未完全闡明其發病的本質,碎片式的研究沒有聯系在一起,終究不能形成一個體系。因此,探討神經細胞信號通路對神經遞質調控的影響,進而揭示它們在PSD 發生機制中的作用或將成為目前國內外研究的熱點。社會心理學機制的研究僅僅停留在表面,不同程度PSD 患者心理變化的不同與神經生物學機制是否有著某種特殊的聯系,更要依靠心理精神專業的把握,運用其更加全面的專業知識進行對PSD患者的心理介入,采用生化檢驗等技術檢驗不同層面的PSD生化指標,比較其差異與心理異同是否存在相關性。總之,PSD病因不清,發病機制復雜,研究出其本質可以更好的就臨床卒中患者預后提供良好的治療方案,降低PSD發病率及卒中患者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