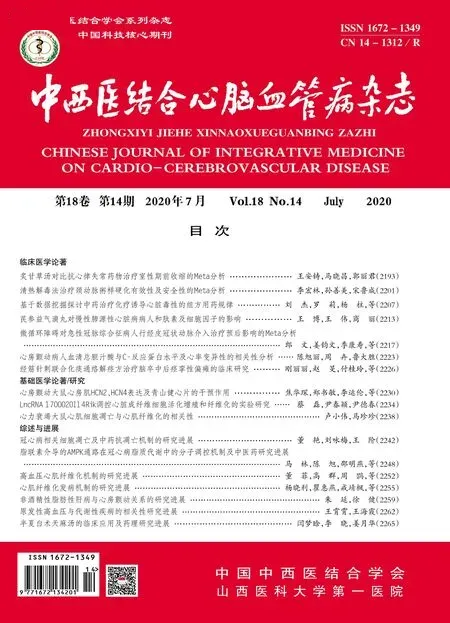顱內外動脈狹窄中醫研究進展
吳 俊,吳建萍,丁硯兵,陳 俊
顱內外動脈狹窄既是缺血性中風的重要病因,又是導致其高復發率的重要原因[1-3],現代醫學多采用基于指南的規范化西藥治療,或用血管內支架等手術聯合西藥治療,但其治療措施可能會出現胃腸道反應、消化道出血以及手術并發癥,尤其是支架后再狹窄發生率較高[4-6],嚴重影響其治療效果。中醫學雖無顱內外動脈狹窄這一病名,但根據其臨床癥狀可將其劃分為“中風”“中風先兆”“眩暈”等范疇。現綜述顱內外動脈狹窄的中醫證候證素、中醫體質、中醫藥干預等,以期為中醫藥干預顱內外動脈狹窄提供依據。
1 中醫證候及證素研究
王永生等[7]對25例頸動脈狹窄病人進行研究,發現頸動脈狹窄以中風病中的中經絡最常見,且與痰濁關系最為密切。孫韶剛[8-9]分析了150例頸動脈狹窄病人,認為其病機復雜,多屬虛實夾雜,且頸動脈不同狹窄程度的病人證型也有差別,狹窄程度越重則血瘀證越顯著。顏冬潤等[10]將頸動脈狹窄病人按基本證型和復合證型分為10種證型,結果表明以血瘀、痰濁、氣虛血瘀、痰瘀阻絡4種證型為主。朱羽佳等[11]將57例頸動脈狹窄病人分為氣血虧虛、痰濁中阻及肝陽上擾3種證型,研究表明前兩種證型病人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較肝陽上擾證病人高,Hcy水平可一定程度反映中醫證型差異。方慶霞等[12]將312例頸動脈狹窄病人分為氣虛型、陰虛型、痰濕型、痰火型,結果表明隨著狹窄程度的增加,痰濕證、痰火證的比例明顯增加。劉海琴等[13]對86例頸動脈支架置入術病人進行術前與術后中醫證型對比研究,結果顯示術前病人證型以血瘀證、痰濕證為主,兼風證,證型組合中以血瘀證+痰濕證+風證組合出現頻率最高;術后病人以血瘀證、氣虛證、痰濕證為主,氣虛證明顯增多,痰濕證較前下降,而血瘀證變化不明顯。
在頸動脈狹窄所致中風先兆方面,齊婧等[14]對680例伴有頸動脈狹窄的中風先兆病人進行分析,發現其證型以虛實夾雜為主,以實證居多。賈玉勤等[15]對300例伴頸動脈狹窄的中風先兆病人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與齊婧等[14]類似。在其他未明確劃分腦血管狹窄的中醫證候研究方面,姚計文等[16]將139例伴有顱內動脈狹窄的2型糖尿病病人分為氣陰兩虛、陰陽兩虛、陰虛熱盛、濕熱困脾4類證型,且前兩種證型病人更易發生顱內動脈狹窄。彭慧淵等[17]對247例伴有大腦中動脈狹窄或閉塞的急性缺血性中風病人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瘀證和痰證出現頻率均最高,且運用化痰通瘀法可有效改善病人臨床癥狀。張永全等[18-19]對急性缺血性中風病人進行辨證分析,發現腦動脈狹窄與肝陽暴亢證、陰虛風動證有關。王守運等[20]對172例缺血性中風病人進行中醫辨證分析,發現氣虛血瘀和風痰阻絡兩種證型與腦血管狹窄明顯相關。楊春霞等[21]在風痰阻絡證方面研究結果與王守運等[20]類似,但其氣滯血瘀證比例較高,且與腦血管病變的范圍和狹窄程度密切相關。
在中醫證候要素研究方面,姬少珍等[22]對納入的1 784例研究對象中259例顱外動脈狹窄病人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其證候要素以血瘀、痰、火、氣虛、陽虛、陰虛為主,且與非顱外動脈狹窄組病人無明顯差異。鄭碩等[23]對66例伴有頸動脈狹窄的缺血性中風病人進行分析發現,其證候要素以血瘀、痰、火、氣虛為主。
2 中醫體質研究
王琦教授[24-27]在中醫古籍文獻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將中醫體質分為9種,并制定了成熟的中醫體質辨識方法,使得中醫體質在臨床科研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現代學者也對顱內外動脈狹窄與中醫體質的相關性做了一定的研究。邱笑瓊等[28-30]對伴有腦血管狹窄的缺血性中風病人進行中醫體質分析發現,血瘀質與腦血管狹窄程度密切相關,而痰濕質與顱內、后循環等狹窄部位關系更為密切。張峰等[31]研究267例中風高危人群椎動脈情況與中醫體質的關系發現,椎動脈單側單發病變以陽虛質最多見,椎動脈單側多發病變以血瘀質最多見,雙側椎動脈病變以氣虛質最多見。邱朝陽等[32]研究207例急性后循環梗死病人的中醫體質,發現痰濕質相較于平和質較易出現椎動脈顱內段血管病變。黃任鋒等[33]研究了150例頸動脈狹窄病人與中醫體質的相關性,結果表明,血瘀質、痰濕質在頸動脈狹窄程度≥50%病人中所占比例最高,且痰濕質與頸動脈狹窄的發生呈正相關。蔣玉倩等[34]分析了174例腦血管狹窄病人與中醫體質的關系,結果表明,痰濕質、瘀血質、陰虛質與腦血管狹窄有關,但不同體質類型與血管狹窄的程度及分布無明顯關聯。
3 中醫藥干預研究
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報道運用益氣活血佐以養陰安神等治法治愈1例右頸總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及狹窄病人[35],顯示出中醫藥干預腦血管狹窄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目前支架植入術是癥狀性顱內外動脈狹窄的血管內主要治療措施之一[36],但其有一定的再狹窄率,對病人遠期預后有影響,有學者從中醫角度探討了支架植入后發生再狹窄的中醫證候因素及中醫藥防治。林浩等[37]對30例行支架植入術的顱內外狹窄病人進行中醫辨證分析,結果表明,術前多表現為痰證、血瘀證、風證,術后以痰證、氣虛證為主,可能與支架術后再狹窄有關。童晨光[38]對93例行椎動脈起始部支架植入術后病人進行6個月隨訪,結果發現血瘀證和氣虛證與術后再狹窄密切相關,氣虛血瘀證可能為病人術后支架再狹窄的重要影響因素;基于此,童晨光等[39]將植入椎動脈起始部支架且符合氣虛證和血瘀證的96例病人隨機分為兩組,兩組均給予常規西藥治療,試驗組同時給予益氣活血中藥治療,對照組同時給予安慰劑口服,隨訪6個月,結果表明,試驗組支架再狹窄發生率低,并可改善病人氣虛、血瘀狀態。張良芝等[40]將60例頸動脈狹窄支架植入術后病人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對照組單純常規給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口服中風防治靈膠囊,兩組均治療180 d,結果顯示,中風防治靈膠囊聯合西藥防治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有較好療效,同時可降低近期出血并發癥的發生率。胡玉英等[41]將無癥狀性頸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病人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對照組予常規西藥口服,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予中藥抵當通脈方口服,治療3個月后,結果顯示,抵當通脈方聯合西藥治療無明顯不良反應,能有效減少斑塊,并能顯著降低頸動脈狹窄程度。
王立新等[42]認為對于行顱內外動脈狹窄血管成形術的病人,其術后瘀血痰濁被支架局部強行祛除,類似于中醫破血化瘀療法,故易在化瘀時耗傷氣血而導致出血、倦怠等證,主張在術中數小時內加用補益元氣的中藥靜脈注射劑以增強機體對手術的應激能力,減少術中、術后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張新春等[43]認為在頸動脈狹窄支架植入時,術前針對痰濁、血瘀、氣虛治療,并佐以疏肝理氣緩解病人情志緊張,術中以預防血管痙攣為重,宜理氣活血,術后缺血再灌注損傷宜鎮肝熄風、化痰開竅,術后再狹窄應注意氣虛這一病機,宜補氣益氣兼活血化痰。
4 小 結
目前顱內外動脈狹窄發病率越來越高,且與缺血性腦卒中、認知功能障礙等疾病發生均有密切關系[44-45],中醫對其理論及臨床研究也越來越多,在理論方面多認為其病理性質多為虛實夾雜,與虛、痰、瘀有關,體質以痰濕質、血瘀質為主,以益氣活血為主要治則的中醫藥干預手段基本達成共識。隨著對顱內外動脈狹窄病因病機的深入認識、中醫證型的不斷統一、體質關聯性的深入探討,將有利于發揮中醫藥“治未病”“治已病”的巨大作用,但在中醫相關研究中仍存在一定的問題與缺陷:①目前,以頸動脈狹窄研究較多,對其他病變血管往往未明確劃分;②對顱內外動脈狹窄的病因病機認識不一致,證型劃分紊亂;③體質研究中病例均較少,缺乏不同地域之間的比較研究;④對于中醫藥干預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病人多為中短期臨床觀察,缺乏長期隨訪跟蹤報道等。希望在今后能進一步深入研究,在證型劃分中達成共識,擴大樣本量,完善設計方案,為中醫藥干預顱內外動脈狹窄提供更多更有力的證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