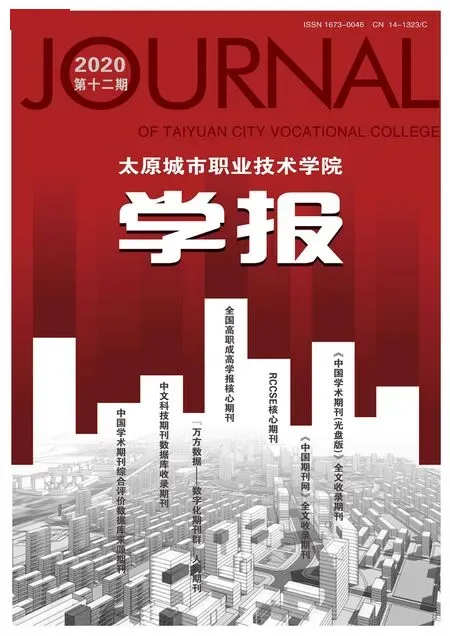略論張庚先生的戲劇理論
——以“舊劇(戲曲)現代化”為例
■王傲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1399)
戲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有不同的審美形態和社會功能。如今抗疫戲劇承擔著引導大眾、“紀錄”歷史的責任和義務。而20世紀初的話劇和戲曲(舊劇),也肩負著啟發民智和促進民權的歷史使命。但令人遺憾的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戲曲已經式微,其發展與時代脫節嚴重,難以承擔社會所需要的個性解放重任。而話劇這一新興藝術,則逐漸成為改良者首選的藝術形式。于是,一場言辭激烈和觀點偏激的新舊劇論爭就此開始。隨著論爭的落幕,學成歸國的余上沅等人面對戲曲與話劇不能適應時代發展形勢的現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國劇運動”,開始使知識界人士對于新舊劇的態度逐步回歸“平穩”,思考也愈加全面。1939年,張庚先生提出了“話劇民族化與舊劇現代化”的著名論斷,開啟了戲曲現代化的初步探索。到新中國成立后,關于戲曲未來發展方向的探討更成為戲劇界研究的熱門話題。也就是說,探討“戲曲現代化”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關系到戲曲的未來發展戰略,關系到戲曲在時代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明確,戲曲的“現代化”不是一個單純的“題材”概念,甚至不是“形態”概念,而是要表現“現代精神”。可以說,現在戲曲面臨的社會環境較之過去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但探討“戲曲現代化”卻仍未過時,其原因就在于戲曲的“現代化”始終是一個現實問題和發展問題,關乎戲曲藝術的興衰。
一、序幕:“五四”文化論爭與新舊劇爭論
早在20世紀初,對于“戲曲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就已初現端倪。當然,這場“討論”最初是在文化批判的基礎上進行的。率先舉起批判戲曲大旗的是錢玄同,錢玄同與胡適等人以“新文學”的標準去看待戲曲,以致激烈地批評戲曲“一無是處”,觀點不可謂不偏激。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場論爭有著深厚的時代背景。當時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竊取,并掀起尊孔思潮。胡適等文化界的啟蒙者認為,要想中國壯大,必先推翻中國傳統文化。此后,《新青年》成為新舊劇爭論者的陣地,戲曲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實際上,若不論胡適等知識分子對于戲曲的批判,而導致的知識界對于本民族文化認同上的“自卑感”,那么這種爭論其實也是一種有“動力”的“壓力”。近代的戲曲雖然一直在改變,但改變的速度緩慢,需要一定的外力刺激。錢玄同等人固然沒有真正認清戲曲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所在,也離間了知識分子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文藝的認同。但是,從時代與藝術發展的角度講,如此大的外力刺激,也只有在那個時代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循序漸進的變革可能會導致“舊劇界”依舊“自吹自擂”,也不會催生出張厚載等人對于“舊劇”審美價值的維護,以及歐陽予倩、周信芳、梅蘭芳等戲曲界先驅者的思考。
此外,雖然“五四”戲劇論爭在知識分子內部掀起巨大影響,但對京劇等演出的實際影響并不大。這說明舊劇在中國的根基之牢固,不是一時所能撼動的。而胡適等人秉持的“文學進化觀”,進而將中國的舊劇認為是“野蠻”的,而西方的新劇是“文明”的這一觀點,則很明顯帶有西方優越論的色彩,不能全面地、辯證地看待中西方文化和藝術的優缺點。同時,張厚載等人為舊劇的辯護,也具有機械性。舊劇的維護者在爭論時也有“意氣”之爭,他們認為“中國戲何須給外國人看”[1],此論就很明顯與新劇支持者的部分說法如出一轍,帶有偏激性。而張厚載等人在辯論時,也機械地套用西方的戲劇理論來牽強附會地解釋中國戲曲的審美特征,亦具有片面性。此后,兩派的爭論雖然看似逐步趨于“調和”,但還是針鋒相對。而在這時,戲劇界的歐陽予倩、宋春舫、梅蘭芳、周信芳等人的觀點就較為公允,他們真切地意識到改革舊劇的必要性,促進了戲曲舞臺藝術的革新與發展。其后,到了20世紀20年代,學成歸國的余上沅等人掀起的“國劇運動”,以及歐陽予倩等人開展的“南國戲劇”運動都對新舊劇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并逐漸使知識界人士對于新舊劇的態度回歸“平穩”,思考也愈加全面,揭開了探索中國戲劇民族化與現代化建設的序幕。
二、“現代題材”:戲曲現代化的初步探索
面對當時劇界對于今后“劇運方向”的“困惑”,以及抗日戰爭的實際需要,張庚先生的第一步就是“話劇民族化”。作為當時舶來品的藝術形式,話劇雖然在“五四”以來發展迅速,并出現很多劇作家和名作,但抗日戰爭的社會環境亦使話劇藝術的實踐和人民群眾的接受之間出現了較大的隔膜。話劇的作用并不像“西化”人士所希望的那樣,只有它才能夠迅速傳達時代精神,振奮國人,反而經歷了不少坎坷,一度脫離群眾。戲曲雖然被激進派所否定,但并沒有就此“消亡”,反而在梅蘭芳等人的傳播推動下,一度引起很大反響。面對這種情況,張庚較早地注意到了話劇藝術必須著重學習和借鑒戲曲這種民族藝術形式的問題,并提出了“話劇民族化”的想法,即合理地運用戲曲的“舊形式”,將其創造性地應用到話劇藝術中去,豐富其表現手段,使話劇大眾化,適應中國人民幾千年來養成的審美習慣,這樣才能扎根于人民群眾。張庚看到了話劇演員在舞臺演劇中的弊病,比如機械地運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驗理論,演員只是照搬日常生活等。正是基于這種情況,張庚提出了話劇的民族化必須與繼承傳統相結合,強調了“話劇大眾化在今天必須是民族化,主要的是要它把過去的方向轉變到接受中國舊劇和民間遺產這點上面來”[2]。這種從話劇的角度提出重視本民族文化遺產的思想,打開了劇界人士正確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天窗”。此后,張庚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又逐步注意到秧歌劇等民間戲劇形式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新的戲劇工作付諸實踐,這為他以后進一步探究“舊劇的現代化”提供了契機。
張庚的“舊劇現代化”在一開始只是重新賦予和表現戲曲新的現代題材。“舊劇現代化的中心,是去掉舊劇中根深蒂固的毒素,要完全保存舊劇的幾千年來最優美的東西,同時要把舊劇中用成了濫調的手法,重新給予新的意義,成為活的。這些工作的進行,首先一定要工作者具有一個進步的戲劇以至藝術的觀念”[2]。張庚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戲曲現代化思想,已經開始強調戲劇工作者的觀念問題,這在今天看來具有長遠意義。從根本上講,戲曲如何實現現代化,不僅是一個題材的問題,也是戲劇觀念的問題。如果戲劇工作者不轉變創作觀念,現代化只能是“紙上談兵”,不能付諸于實踐。如今戲曲面臨著“老舊”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戲曲界對于“現代化”的認識不夠,這還需戲曲從業者在戲曲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上做長時間的探索和準備。此后,張庚不斷深化對“戲曲現代化”這一問題的研究,去探索它“是什么、為什么、如何做”,并通過實踐和理論上的總結和概括,使它更為清晰,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在張庚眼中,“戲曲現代化”不是徹底地改變中國戲曲,而是吸收和借鑒、協調和發展、傳承和創新,要去表現現代精神。到新中國成立后,張庚在經歷了幾次全國大規模的戲曲演出后,對戲曲現代化的理解更為深入。也就是說,面對中國傳統戲曲,必須在保持戲曲藝術本體特征的同時,對戲曲舊的內容和形式進行甄別和改造,而不是一刀切、一鍋煮,違反戲曲的藝術規律。此外,張庚提出的“戲曲現代化”意義又不僅限于此。在長期的理論與實踐中,張庚對于戲曲藝術精神的理解更為深入,并逐步提煉出以“劇詩”為核心的戲曲理論觀,以滿足戲曲改革的需要,指導戲曲文學創作和舞臺實踐。
三、“現代精神”:張庚戲曲現代化的理論內核
隨著20世紀50年代“戲改”成為中國戲曲事業發展的主線,注重戲曲的推陳出新和探討現代戲的創作成為劇界工作重心。從對待“戲曲現代化”的問題上來看,當時很多文藝工作者都主張用西方寫實話劇的特點來改造戲曲,但在創作中出現了概念化的傾向,以至于戲曲產生“去戲曲化”的舞臺詬病。為此,張庚在民族美學的高度積極審視戲曲藝術的發展實際,以“物感說”為“劇詩說”的理論支撐,在強調戲曲具有詩性品格的同時,重視戲曲如何同新時代、新題材、新觀眾相結合,從而探討現代戲曲如何表現現代生活“靈魂”的問題。同時,在張庚看來,現代題材的戲曲劇目是戲曲現代化的最佳載體,而這首先需要做到戲曲藝術表現內容的現代化。為此,張庚高度重視戲曲現代題材的劇目建設,提倡創作出一批表現現代生活的戲曲劇目,以加強戲曲的現代戲建設。而值得注意的是,要認識張庚對于戲曲現代戲的探討不能只囿于他提倡戲曲現代題材建設的方面,而不考慮張庚對于戲曲劇目要表現現代精神的方面。現代精神的表達,是戲曲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道路,也是張庚戲曲現代化理論的核心。戲曲藝術有千百年的發展歷史,大量傳統劇目生長于民間。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傳統劇目中存在的有害因素,如封建色彩、宿命論等,也要認識到傳統劇目里蘊含的人民性和現代性,即優秀的傳統劇目依舊能表現現代精神。為此,張庚面對很多文藝工作者不理解傳統劇目的現狀,“駁斥了那種所謂‘只有表現了現代生活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說法,闡述了表現歷史生活的傳統劇目在社會主義藝術家手中,完全有可能具備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意義”[3],從而對戲曲的現代化問題作出了新的解釋,即戲曲藝術要做到表現現代題材與現代精神相結合的美學高度,這樣才能促進戲曲走向現代化。
此外,中國的時代和實踐發展也讓張庚看到“兩條腿走路”是不足以實現戲曲現代化的,這就要求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去創作“新編歷史劇”,要融入現代人的審美趣味和時代精神,實現“傳統戲、現代戲、新編歷史劇”的“三并舉”,而這又從實踐上反推了張庚對于“戲曲現代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從“五四”時期的初步探索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三改”方針;從“以現代劇目為綱”到“三并舉”方針,隨著“戲曲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深入,戲曲藝術雖然一度經歷了“樣板戲”時期的“一枝獨秀”,但新時期后的戲曲發展卻更加明確地堅定了只有走向“現代化”才是戲曲實現自身振興的唯一道路。同時,隨著更多自覺遵循戲曲藝術創作規律的優秀劇作不斷涌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也愈加緊密,“資料-志-史-論-評”五位一體的戲曲學科框架也漸為完善。由此可見,張庚先生對于中國戲曲現代化的建設具有不容忽視的歷史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