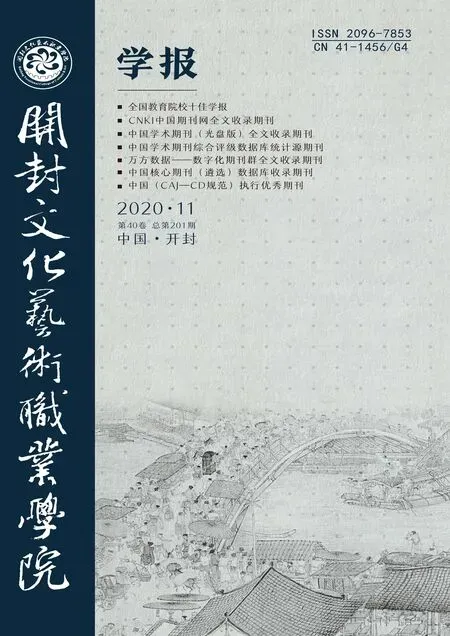龍榆生與夏承燾交游考
汪海洋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龍榆生是 “民國四大詞人”[1]173之一。關于龍榆生與夏承燾的交游研究,李劍亮的《夏承燾詞學與〈詞學季刊〉》[2]從夏承燾與《詞學季刊》這一方面進行了論述;蕭莎的《夏承燾交游詞研究》[3]從夏承燾與龍榆生的交游詞方面進行了論證。這些論文為研究龍榆生詞學交游提供了依據與基礎。然而,相關論述均有待進一步深入,如1949 年前后龍榆生與夏承燾關系的變化。龍榆生生平交游是其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龍榆生與夏承燾在詞學道路上相互幫助,相互影響,使得二人的詞學觀點互為補充。二人的交游既幫助了夏承燾,又對龍榆生的詞學觀產生了影響。本文將以龍榆生就職于汪偽政府為分界點,對龍榆生與夏承燾的交游進行研究,以此對龍榆生的詞學活動進行梳理,為深入理解龍榆生的詞學觀提供參考。
一、 1940 年前龍榆生與夏承燾的交游
龍榆生與夏承燾相識于1929 年,他們的相識得益于李雁晴。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記錄道:“得李雁晴廈門大學五月三十日函,謂暨南大學教授龍君榆生,名沐勛,江西人,黃侃弟子,近專治宋詞,有所論述。雁晴囑與通函討論。”[4]99夏承燾從李雁晴處得知龍榆生專于治詞,主動尋求龍榆生的幫助。這時,龍榆生已經是大學老師了,其在詞學上的影響力要高于夏承燾。夏承燾此時正在編撰《唐宋詞人年譜》,編纂年譜是一件耗時耗力的工作,需要逐一考證詞人生平。然而,當時的夏承燾并不具備這些條件,他既“無師友之助”又“聞見不廣”,因此,急需他人在詞學研究上給予幫助,而龍榆生正是這個能給予其幫助的人。于是,夏承燾開始主動給龍榆生寫信,剛開始在信中以學生自居。夏承燾這個時候住在嚴州,因為嚴州的 “學問空氣太稀薄”[3],而龍榆生住在上海,在暨南大學任教,兼之周圍有許多師友,所以夏承燾渴望得到龍榆生的幫助,正如信中所言 “如得先生上下其議論,共學之樂,乃無藝矣”[3]。龍榆生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當即回信愿意與夏承燾結交,并進一步提出與夏承燾合編詞人年譜,“與予締交,問《詞有襯字考》。又謂有意為詞人年譜,欲與予分工合作”[3]。夏承燾則非常高興,隨即 “燈下作一書復之”[3]。
此后,二人交往日益密切,夏承燾常將著作寄給龍榆生指正。夏承燾要寫《張子野年譜》,就委托龍榆生 “查子野入蜀年代”,在龍榆生的幫助下,夏承燾完成了《張子野年譜》,并刊登在龍榆生創辦的《詞學季刊》上。同時,夏承燾也在龍榆生治詞的道路上給予了其幫助。龍榆生治詞標舉蘇、辛,在一次寫信中,他告訴夏承燾,“《稼軒年譜》已成,發愿為蘇、辛詞合箋”[3]。龍榆生想要為蘇軾和辛棄疾著合箋,夏承燾長于詞人的考證,“瞿禪專為詞人做年譜,翻檢群書,校核事跡,積歲月而成《唐宋詞人年譜》十種十二家,開創詞人年譜之先例”[5]。于是,夏承燾在給龍榆生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蘇、辛詞使事較多,尊著于冷僻者一一注出,亦極便讀者。”[3]夏承燾認為,蘇軾和辛棄疾的詞作多運用典故,對于簡單的典故不必一一標出,龍榆生在做箋注時只需把其中生僻的、不常見的典故標注出來。龍榆生的《東坡樂府箋》完成以后,夏承燾“為榆生閱東坡詞箋”,并“刪其繁處”,幫龍榆生校正《東坡樂府箋》,而且告訴龍榆生 “東坡詞宋人有顧禧景繁補注,見《西塘集耆舊續聞》,共四、五事”[6]。夏承燾看了龍榆生的“補訂辛梅臣辛稼軒年譜” 后,評價甚高,說其作 “甚詳贍翔實”[3]。龍榆生寫完《清季四大詞家》以后,夏承燾指出《清季四大詞家》中的4 點錯誤,龍榆生虛心接受并改正,最后刊登在《暨南大學學報》上。
夏承燾治白石詞,二人在通信中多次交流觀點。夏承燾寫有《與龍榆生論陳譯白石〈 暗香譜〉 書》《與龍榆生論白石詞譜非琴曲書》《再與榆生論白石詞譜書》等文章,后來都被刊登在《詞學季刊》上。在《與龍榆生論陳譯白石〈 暗香譜〉 書》一文中,夏承燾說其曾見陳東塾譯白石《暗香》一書,認為 “其用《通考》舊法,而不免疏牾”,龍榆生看后 “定白石詞譜為琴聲”。夏承燾對于此說 “不敢盡信”,于是,又寫了《與龍榆生論白石詞譜非琴曲書》,“于旁譜辨中舉數證獻疑”。龍榆生回復:“茍宋詞亦一字數音,可以由樂工自由增減,何以《漁歌子》曲度不傳。蘇黃以《浣溪沙》《鷓鴣天》歌之,必依譜改定其句度。” 夏承燾又寫了《再與榆生論白石詞譜書》,解釋道:“雖一字一律,而纏聲赴拍,并非毫無緩急。”[7]1107這些觀點的交流加深了二人對于白石詞的理解,并為以后夏承燾研究白石詞打下了基礎。
不僅如此,在二人的交往過程中,龍榆生還不斷為夏承燾提供相關的書籍。龍榆生曾把 “蛻庵先生賡言” 的《蛻庵詩集》送給夏承燾。夏承燾研究姜夔詞,龍榆生盡可能把自己所藏的相關書籍借給夏承燾。因為龍榆生受學于朱祖謀與黃侃,二人都曾點評過《夢窗詞》,當夏承燾寫《夢窗詞集后箋》時,龍榆生就把朱祖謀與黃侃點評的《夢窗詞》借給夏承燾,并且幫夏承燾把《夢窗詞集后箋》發表在《詞學季刊》上。因為夏承燾要編撰詞人年譜,龍榆生就送給夏承燾 “《詞莂》《菌閣瑣談》及陳慈首《稼軒年譜》”;因為夏承燾研究辛棄疾缺少書籍,龍榆生就幫夏承燾買《詞話叢抄》;因為夏承燾研究姜夔,龍榆生就幫夏承燾 “向上海各詞人問白石事”。二人還經常討論《姜考》的體制。夏承燾研究宋元詞,龍榆生就送給夏承燾《宋元三十一家詞》《散原精舍詩別集》。另外,夏承燾還從龍榆生處見到了許多珍貴的書籍,如“大鶴山人詩稿、張爾田《詞莂》未刊本”[5]。這些書籍均有益于夏承燾日后從事詞人年譜研究。
龍榆生不僅為夏承燾提供書籍,還把周圍的師友介紹給夏承燾。龍榆生是朱祖謀與黃侃的學生,而且交友廣泛。夏承燾對龍榆生直言“足下見聞較廣,當有以教我”,并希望龍榆生把自己引薦給朱祖謀,于是,龍榆生就充當了朱祖謀與夏承燾之間交流的橋梁。夏承燾認為朱祖謀所考吳文英的生年有誤,與自己所考相差三十多年,遂請龍榆生把這一發現告知朱祖謀。龍榆生在信中說道,朱祖謀 “自承夢窗生卒為未定之說”,并且 “盼予速寄示”,隨后夏承燾就通過龍榆生把《夢窗生卒考》寄給朱祖謀,朱祖謀看后評價道 “夢窗系屬八百年未發之疑,自我兄而昭析”。在龍榆生的幫助下,夏承燾與朱祖謀開始有書信上的往來,并經常談論詞學。此后,二人的關系進一步加深,龍榆生邀請夏承燾共同編纂《清詞鈔》,并且答應與其 “共訪彊村”[3]。因為龍榆生的緣故,夏承燾于1930 年與仰慕已久的朱祖謀見面,“四月,赴滬,初與龍榆生把晤,初謁朱彊村”“七月,返溫度暑假,經滬,第二次晤榆生,第二次詣彊村”“九月,經滬,訪榆生、詣彊村”[8]226。
龍榆生于1933 年創辦了《詞學季刊》,期間共發表了夏承燾11 篇論文:《張子野年譜》、《夢窗詞集后箋》、《賀方回年譜》、《韋端己年譜》、《晏同叔年譜》(上)、《晏同叔年譜》(下)、《馮正中年譜》、《南唐二主年譜》(一)、《南唐二主年譜》(二)、《南唐二主年譜》(三)、《南唐二主年譜》(四)。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夏承燾在詞學上的影響力。這些論文幾乎全為詞人年譜,夏承燾長于考證的特點也在此時顯露出來。對于龍榆生和夏承燾在詞學上的成就,夏承燾曾評價道:“榆生長于推論,予則用力于考證。”[5]這個評價非常中肯。
這些舉措無疑擴大了夏承燾的交往面。因此,龍榆生對夏承燾的詞學研究給予了很大幫助,后來夏承燾回憶道:“閱嚴州日記,念僻居山邑,如不交榆生,學問恐不致有今日。”[3]
二、1940 年后龍榆生與夏承燾的交游
1940 年,龍榆生投靠汪精衛并在汪偽政府任職,二人的關系逐漸發生變化。夏承燾在日記中寫道:“聞口口將離滬,為之大訝,為家累過重耶,抑羨高爵耶。枕上不得安睡。他日相見,不知何以勸慰也。”[3]此后,龍榆生為士人所不齒,夏承燾遂用“口口”代指龍榆生。夏承燾經常寫信勸誡他,“三月一日,夏承燾發先生函:‘勸榆生及時蓄積為退步計’”[4]125。
作為朋友,夏承燾還經常寫詞勸龍榆生回頭,“夏承燾感先生事,為賦《水龍吟》‘皂泡’、《木蘭花慢》‘題嫁杏圖’、《虞美人》‘感事’、《鷓鴣天》‘萬事兵戈有是非’、《臨江仙》‘古津席上,名山翁示詩云:明歲春風二三月,吾曹猶及看花否?作此為報’、《虞美人》‘自杭州避寇過釣臺’等詞”[4]124。雖然此時夏承燾與龍榆生仍有往來,但夏承燾立場堅定,汪偽政府為龍榆生創辦了《同聲月刊》,夏承燾沒有在上面發表過一篇論文。
此后,汪偽政府倒臺,1945 年11 月8 日,“國民黨教育部以了解學潮為由請走龍榆生,囚禁于老虎橋監獄”。夏承燾 “以萬元托仲連買蔬肴饋之”[4]124,并且委托其在法院工作的學生琦君幫助龍榆生,1945 年12 月9 日:“發希真蘇州高等法院一函,由心叔轉,懇其相機照料榆生。”12月16日:“得希真復,謂榆生保釋事,俟鄭院長回蘇時即可設法,似不甚難。”龍榆生在獄中時還經常與夏承燾通信,1945年7 月12 日:“得榆生蘇州函,囑畫扇面,并囑時時通書,以慰寂寞。”[4]124龍榆生得以提前出獄,夏承燾功不可沒。龍榆生出獄以后與夏承燾繼續通信并談論詞藝,《天風閣學詞日記》1948 年12 月20日云:“昨榆生寄來新《忍寒詞》一冊,燈下閱數首,予曩勸其應刪各篇己盡刪矣。”[4]137-138
1949 年以后,龍榆生因為歷史舊嫌,生活艱苦。1951 年,龍榆生經歷了“鎮壓反革命運動”。1953年,夏承燾拜訪龍榆生,二人曾有過唱和,“晨九時與朱、沈二君冒雨往上海博物館訪榆生,一別十馀年,已兩鬢繁霜如老翁矣。謂蕙風先生為劉翰怡所抄之《詞林考鑒》,積稿可三四尺。劉尚健在,此稿不知何在。(榆生所鈔僅七八本耳。)又謂《彊村叢書》版已無可蹤跡,《彊村遺書》稿則已捐與博物館或文史館。榆生導觀博物館,匆匆行十馀室,多見所未見”。龍榆生詩曰:“最難風雨故人來,佳節匆匆罷舉杯。九死艱虞留我在,十年懷抱為君開。照人肝膽情如昨,顧影芳華去不迴。今夕霸王臺下過,倘從云外一低徊。” 龍榆生在詩的自注中表達了對夏承燾的感謝:“予曩歲陷虜中,數來往彭城、燕京、金陵間,欲效辛幼安之所為。奇謀未就,終遭縲紲。微瞿禪及女弟子龔家珠后先營救,幾早瘐死獄中矣。”[4]133
1954 年,為解決龍榆生生活上的困難,友人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劉大杰等主持為上海公營新文藝出版社編印古典文學叢刊,約顧頡剛、容庚、詹安泰、朱東潤、游國恩、王季思等分任編纂。其中詞選一種,特請先生與夏承燾合作,藉讓先生獲薄酬開銷”[4]133。龍榆生與夏承燾受邀合作編選《詞選》,夏承燾剛開始答應與龍榆生合作,但1954 年8 月,夏承燾給龍榆生寫信道,“備課忙,無暇及《詞選》”,退出了詞選的編撰工作。關于夏承燾為什么退出編纂工作,《天風閣學詞日記》中曾有記載,1954 年8 月11 日云:“微昭(陸維釗)來,謂上海友人頗以予與榆生合編詞選為言,榆生歷史舊嫌,至今不恕于人口。” 8 月18 日:“夕心叔(任銘善)、天五(吳鷺山)來,談與榆生編詞選事。心叔恐予過忙,謂可讓榆生一手為之。” 19 日:“發榆生函,寄還唐五代北宋選目,并告事忙課忙,選詞事不能兼顧,請榆生一手了之。”[4]139
龍榆生于 “1958 年5 月被劃為右派”,1961 年才得以“脫帽”[9]907,此時龍榆生已經60歲。脫帽后,龍榆生與夏承燾仍有往來,并經常與其談論這段經歷:“午后榆生來,數年不見,發白八九分矣。談此次脫帽經過,謂以八字自勉:戒驕戒躁,又紅又專。又談徐州事,予多不解。勸予早晨散步,最能安泰心身,談兩三小時云。”[4]351
1965 年,龍榆生64 歲,仍經常與夏承燾寫信論詞調詞樂:“談詞學革命化研究計劃,謂此一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之偉業,盼以熱情毅力不斷努力,促其實現。”[4]189可見,龍榆生在晚年仍然為推進詞學事業的發展作貢獻,這種精神讓人敬佩。1966年,龍榆生卒于上海,至此,二人的交往告一段落。
結語
龍榆生與夏承燾相識于1929 年,他們的友誼持續了30 多年,30 多年來,二人在詞學的道路上互幫互助,砥礪前行。在二人初識之時,龍榆生用自己在詞學上的影響力積極地幫助夏承燾,為夏承燾介紹師友,提供詞學書籍,拓寬其治學的道路;在后來龍榆生被人們非議的時候,夏承燾并沒有因為龍榆生一時的錯誤而與其斷絕往來,仍然不遺余力地幫助龍榆生。這30 多年,二人書信往來,談論詞學,交流詞學觀點,共同推進了現代詞學的進步,而他們的友誼也成為詞壇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