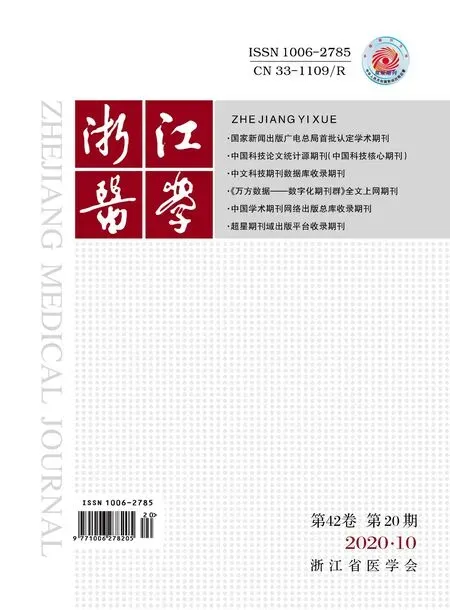氧化應激狀態對慢性腎臟病的影響研究進展
石承乾 張冰冰 魯科達 夏虹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ease,CKD)具有患病率高、知曉率低、預后差及醫療費用高等特點,已成為世界各國所面臨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我國CKD患病率達10.8%[1]。CKD患者往往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壓、血脂異常等,可引發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而氧化應激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3]。當多種原因引起線粒體負荷過重,導致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增多,細胞抗氧化能力下降,生理性防御機制破壞,這是是氧化應激發生的關鍵。體內的ROS積聚過多,損害機體內多種正常的蛋白質、脂質、核酸等物質,加劇炎癥反應并加速腎損傷進展。因此,臨床可通過檢測CKD患者相關生物標志物來評估機體氧化應激狀態。本文就氧化應激狀態對CKD的影響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腎臟ROS來源
紫外光、電離輻射、藥物等是體內非酶方式誘導ROS形成的主要原因,在細胞內,大量ROS由線粒體電子傳遞鏈生成,而細胞色素P450家族、黃嘌呤氧化還原酶(xanthine oxidoreductase,XOR)、還原型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氧化酶(NOX)等催化酶會極大影響 ROS 生成[4]。NOX 家族中 NOX1、NOX2、NOX4被證實在腎皮質中表達,其中NOX4為最常見的亞型,當處于CKD等病理情況,或受到血管緊張素Ⅱ(AngⅡ)、葡萄糖、生長因子及炎癥介質等刺激時,NOX4在腎臟高表達且為腎臟ROS主要來源,是腎臟氧化應激和腎損傷的關鍵[5-6]。
2 CKD患者氧化應激狀態
氧化應激是體內ROS增加而抗氧化物下降引起的結果。機體中存在生理性防御機制,氧化代謝失衡可多方面影響腎臟,包括血管反應性、腎血流動力學、腎小球濾過率以及所有腎單位的腎小管重吸收與分泌功能,引起腎損傷[7]。通過檢測蛋白質、脂質、核酸氧化產物等相關生物標志物可評估CKD患者機體內氧化應激狀態及抗氧化能力。
2.1 CKD患者氧化系統變化 評估CKD患者氧化應激狀態是探索新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的一步,而氧化應激損傷蛋白質、脂質、核酸等引起的產物具有較長半衰期,因而可作為評估氧化應激狀態的生物標志物。晚期氧化應激蛋白產物(advanced oxidation protein products,AOPP)和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是蛋白質氧化應激的生物標志物。研究提示AOPP可引起細胞內炎癥,引起腎臟機構及功能異常,引起腎小球肥大及蛋白尿等,并指出AOPP與肌酐清除率存在負相關[3],可反映CKD患者腎功能狀態。
脂類分子的結構使其易受氧化,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丙烯醛、4-羥基壬烯酸(4-hydroxynonenal,HNE)及硫代巴比妥酸反應物質(thiobarbituric acid reactive substances,TBARS)等在脂質氧化過程中產生。研究發現在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患者的血漿MDA明顯高于腎臟微小病變患者及正常對照患者,提示氧化應激在腎小球硬化的病理性進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在沒有腎活檢情況下對鑒別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與腎臟微小病變有一定價值[8];但因MDA的水溶性,可在血液透析過程被清除,因此在評估血液透析患者氧化應激時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證實,CKD患者血清MDA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患者,并且終末期腎臟病患者MDA水平高于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患者[3,9]。F2-isoprostane是花生四烯酸非酶氧化形成的一種在細胞膜磷脂上的不飽和脂肪酸,可在血清及尿液中檢測出[10],隨著疾病進展,CKD 3~5期患者血清游離F2-isoprostane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患者[11]。
8-羥基脫氧鳥苷為白細胞DNA損傷的標志物,在氧化化合物和核酸的相互影響下增加,在腎衰竭進展中逐漸上升,并是透析患者全因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12-13]。CKD 患者 AOPP、MDA、F2-isoprostane、8-羥基脫氧鳥苷等氧化指標明顯升高,提示CKD患者機體內同時存在蛋白質、脂質、核酸等多種氧化應激損傷,一方面可作為氧化應激的生物標志物,評估氧化應激狀態;另一方面隨著腎功能下降,AOPP、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等氧化產物在體內蓄積成為了尿毒癥毒素,損傷細胞、組織、器官,引發炎癥和免疫功能紊亂等全身性反應,加速了CKD進展。
2.2 CKD患者抗氧化系統變化 內源性酶與非酶抗氧化機制與氧化應激產物引起的破壞性效果相關,其中脂溶性抗氧化劑包括維生素E、β-胡蘿卜素及輔酶Q;水溶性抗氧化劑包括維生素C、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過氧化氫酶(catalase,CAT)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等;而鐵蛋白、轉鐵蛋白和白蛋白通過螯合金屬離子躍遷發揮非酶抗氧化作用。
SOD是重要的內源性抗氧化酶,其3種亞型(SOD1、SOD2、SOD3)存在于腎組織線粒體、細胞質及細胞外空間[3]。SOD活性受抑制則增強腎臟ROS活性,從而降低腎臟血流、腎小球濾過,成為大鼠高血壓的潛在因素[14]。有臨床研究證實CKD患者血清SOD明顯下降[9],但在未進行透析治療的CKD5期患者中SOD2反而升高,并且對患者生存沒有獲益[15]。
CAT存在于所有的需氧細胞中,并在腎組織表達升高,在減少ROS及抑制脂質過氧化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指出,脂多糖(LPS)誘導的CAT失活會明顯加重內毒素血癥大鼠腎臟損傷[16]。但在臨床研究發現,CAT活性在眾多CKD臨床研究結果中表現不一致,作為CKD患者的氧化應激指標值得商榷,但對糖尿病患者是一個可信賴的氧化應激指標[17]。
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是機體 H2O2、羥自由基(OH-)及含氯氧化劑的清除劑;GSH-Px則以GSH作為供氫體,將H2O2及其他有機過氧化物轉化H2O及O2,達到抗氧化作用[3]。而GSH-Px可分為細胞內GSH-Px以及存在于血漿的細胞外GSH-Px(eGSH-Px)。CKD患者 eGSH-Px 活性及 GSH 含量較健康者明顯降低[9,13,18],腎臟替代治療對eGSH-Px活性具有消極影響,血液透析患者透析后eGSH-Px活性明顯低于CKD3~5期非血液透析患者[18]。
對氧磷酶-1(paraoxonase-1,PON1)是人 PON1 基因產物,具有催化水解磷酸酯鍵作用,并具有過氧化物酶活性[19]。研究發現,CKD患者PON1活性低于控制對照組,其活性與血清MDA等水平相關,并且CKD患者PON1血清水平與受損的主動脈功能顯著相關[20-21]。
此外,非酶類抗氧化物系統在機體內也起到重要的抗氧化作用,其重要組成之一維生素C廣泛分布于細胞內液及細胞外液中,在清除ROS以減少氧化應激帶來的損害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水溶性抗氧化劑作用。而維生素E可保護細胞膜不受脂質過氧化影響,并且可形成低反應性的維生素阻斷自由基級聯反應[3]。
CKD患者SOD、GSH-Px及PON1等抗氧化指標明顯降低,提示CKD患者抗氧化能力下降,氧化/還原失衡,更易受到氧化應激損傷,促進CKD進展。
2.3 氧化應激狀態與CKD的關系 研究發現,CKD患者ROS活性明顯高于健康對照患者[22-23]。而ROS過多積聚于體內產生多種氧化應激產物。CKD患者機體游離 F2-isoprostane、AOPP、MDA[3,8-9,11-12,17]等氧化激指標明顯高于健康對照患者,并且這些指標與腎小球濾過率存在負相關[17,24]。與此同時,CKD 患者 SOD、GSH-Px、PON1等抗氧化酶活性較健康對照患者下降,維生素C、維生素 E 等非酶類抗氧化物水平降低[3,9,13,18,20-21,25]。并有研究報道AOPP水平與血清MDA水平呈正相關,而GSH-Px與其呈負相關[21]。CKD患者普遍存在氧化應激狀態,氧化應激的增加和抗氧化能力的下降與腎功能減退相關,氧化/還原平衡遭到破壞是氧化應激發生的關鍵。
3 氧化應激與CKD危險因素的關系
3.1 氧化應激與高血壓 高血壓在CKD患者早期即可出現,并會增加CKD患者心血管疾病發生率和病死率,控制血壓是CKD管理預防核心要素[2]。高血壓患者腎臟是氧化應激的重要部位,腎臟氧化應激在高血壓引起腎臟血管收縮、腎組織損害中具有重要作用,是腎臟內皮功能、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及腎小管離子通道表達的關鍵調節因素,可引起腎血管病理性改變,最終導致慢性高血壓的發生[26-27]。使用抗氧化劑、超氧化物歧化酶模擬物及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阻滯劑等可減少ROS釋放,減弱或延緩高血壓發病,保護腎臟結構和功能[28]。
3.2 氧化應激與糖尿病 糖尿病是老年CKD患者非常普遍的危險因素,高血糖促進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 2(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SGLT-2)驅動腎小管鈉的重吸收,隨后抑制球管平衡并激活致密斑中RAS,引起入球動脈擴張并收縮出球動脈[2,29],在早期可表現為一側或雙側腎臟腎小球濾過率升高;但持續高血糖狀態刺激線粒體過度釋放ROS,通過轉錄因子NF-κB、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等途徑,增強腎臟炎癥、破壞血管內皮功能,促進動脈粥樣硬化及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沉積,引起腎纖維化逐步加重,最終導致腎小球濾過率逐漸下降而進入終末期腎臟病[30]。
3.3 氧化應激與脂質代謝異常 CKD患者常伴有脂質代謝異常及尿毒癥毒素相關的脂質顆粒修飾,致動脈粥樣硬化因子低密度脂蛋白(LDL)被過度釋放的ROS氧化形成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DL,OX-LDL),促進內皮細胞分泌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誘導單核細胞與巨噬細胞在血管中浸潤,浸潤的巨噬細胞通過清道夫受體吞噬OXLDL后形成泡沫細胞并停留在血管壁,促進炎癥反應并引起內皮功能障礙,導致動脈粥樣硬化[2]。而OX-LDL可通過植物血凝素樣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受體(lectin-like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LOX-1) 刺激ROS生成,形成ROS-LDL-OX-LDL-ROS惡性循環,最終導致腎臟缺血、炎癥及纖維化[31]。
3.4 氧化應激與炎癥反應 持續存在的低度炎癥已成為CKD重要組成部分,在CKD病理進展中具有獨特作用,造成蛋白質-能量消耗(protein-energy wasting,PEW)狀態,并增加CVD及全因死亡率風險[32]。當過度產生的自由基介導腎損傷發生后,通過多種促炎癥反應信號通路引起中性粒細胞等炎癥細胞浸潤于損傷的腎組織,而炎癥反應則可通過NOX系統促進超氧化物產生,持續性造成腎臟損傷或充當信使分子,進一步加重局部炎癥反應,長期氧化應激及慢性炎癥引起的腎損害最終導致腎單位缺失,加速CKD的進展[33]。氧化應激與炎癥反應則形成了一個自我循環,修復自由基損傷的炎癥過程成為額外自由基的來源,因此控制氧化應激及炎癥反應是CKD長期管理重要的舉措。
3.5 其他 社會人口老齡化必將增加CKD絕對數量,而糖尿病、肥胖的流行最終可能成為CKD主要病因[2]。老齡化引起的相關功能損傷歸咎于氧化應激對脂質、蛋白質、DNA等大分子氧化產物積累[34],而肥胖患者相關并發癥由炎癥/氧化信號通路,激活RAS、NF-κB等系統,導致內皮功能紊亂,引起CKD的發生、發展[35]。
4 氧化應激與腎纖維化
腎纖維化是CKD進展到終末期腎臟病的共同途徑,而ROS則可通過多種通路引起腎損傷,在腎纖維化進展中起到重要作用。TGF-β/Smads通路被認為是纖維化疾病中的關鍵機制,其中關鍵因子TGF-β1通過NF-κB、p38MAPK、JNK、ERK1/2 等通路促進腎纖維化進展[14]。ROS產生增多及氧化應激的增強與TGF-β1生成與激活密切相關[36]。研究發現,TGF-β1可增強NOX活性及NOX2、NOX4表達,誘導ROS產生,而干擾NOX4表達可減少TGF-β介導的超氧化物形成[37-38]。Das等[39]進一步研究發現干擾Smad2或Smad3的表達可減少由于TGF-β1激活所引起的NOX4表達增加、ROS代謝及線粒體膜電位喪失等,而其機制可能與Smad-ERK1/2-mTORC1軸相關[40],提示TGF-β/Smad2/3通路激活上調NOX4,誘導ROS生成,在腎纖維化進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
氧化應激敏感性轉錄因子核因子NF-E2相關因子2(nuclear factor E2 related factor 2,Nrf2)對體內酶-非酶抗氧化系統具有調節作用,可改善氧化應激狀態,在腎纖維化進展中起關鍵作用。促纖維化因子TGF-β1通過激活多種信號級聯導致活化成纖維細胞形成,促進ECM合成,激活轉錄因子Nrf2,誘導抗氧化/細胞保護基因表達。Tan等[41]發現在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及單側輸尿管梗阻(UUO)小鼠模型中,Nrf2靶基因表達明顯上升。Chung等[42]T型鈣離子通道阻滯劑可通過激活Nrf2,促進CAT、SOD1等抗氧化酶表達,延緩UUO模型小鼠腎間質纖維化進展。ROS過量釋放會加速腎纖維化進展,激活Nrf2則可起到與TGF-β1相反的作用,減弱氧化應激狀態而延緩腎纖維化進展[43]。
5 小結
CKD患者普遍存在氧化應激狀態。過多ROS積聚損害腎臟結構,加重腎損害,并且與心血管疾病、貧血等并發癥發生率及病死率的增加有關。及早評估CKD患者氧化應激狀態并進行積極的干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