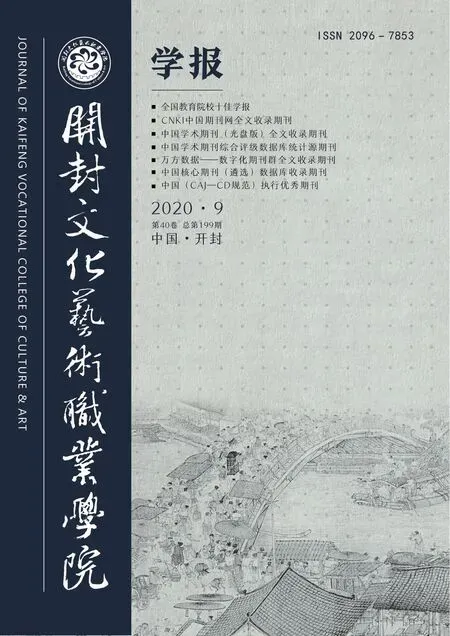現實與荒誕之間
——探析班克斯的涂鴉藝術價值
韓 昀 黃 雁
(云南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人類最早意義上的涂鴉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以西班牙的阿爾塔米拉和法國的拉斯科洞穴壁畫最為盛名,這在當時是以敘事體的方式記錄人類的生產勞作。涂鴉藝術真正成為概念上的藝術潮流則是出現于20 世紀70 年代的美國紐約,著名的涂鴉藝術家有巴斯奎特、凱斯·哈林等。涂鴉藝術憑借其年輕化、反叛性的特點迅速蔓延整個歐美國家,地下涂鴉者們將油漆噴涂在街道墻壁、地鐵站和車廂等一些公共場所最顯眼的地方,以字母或者圖像作為個人符號來詮釋他們的個性或者懷疑和反思。
一、城市街頭中的涂鴉藝術
涂鴉藝術因其反傳統、反主流的特征長久以來不被權威機構所認可而處于一種邊緣的狀態,這反而更激發了它頑強的生命力。涂鴉藝術的表達手法多樣而且有著極強的自由性,因而受到年輕人的追捧,它經由涂鴉藝術家或者涂鴉團體自發在城市的墻壁甚至廢棄的場地進行創作,達到了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它消解了以往形式上的藝術品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邊界,在視覺上傳遞著涂鴉藝術家們的個人見解。
班克斯于1974 年出生在英國的布里斯托爾,班克斯并非他的真名,而是涂鴉完成后簽名用的匿名。班克斯是當今藝術界炙手可熱的超級明星,可他卻以神秘感示人,沒有人見過他的真實相貌,因為他拒絕一切商業性的采訪和活動。同大多數涂鴉藝術家一樣,班克斯在其作品中表達著自己的訴求。因為涂鴉藝術對公共環境有“破壞”的嫌疑而未得到官方的認可,在街道墻壁上、地下通道等公共場所隨心所欲地噴涂是城市管理者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觸及政治的敏感話題。這就決定了班克斯只能在夜間進行涂鴉,而他將自己的面部裹得嚴嚴實實,只露出兩只眼睛,沒有人能看清他長什么樣子。班克斯創作的《氣球與女孩》《投擲鮮花的人》等涂鴉作品讓當地的百姓驚喜于這種看上去充滿諷刺意味卻又風趣十足的涂鴉作品,起初當地的政府抹去涂鴉的做法遭到了居民們的反對,最終經由議會決定而保留了下來。班克斯通過涂鴉的方式表達他所處社會中的問題,他被視作城市街頭的“游俠”受到當地人的推崇,他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紐約、洛杉磯甚至難民營和以色列隔離墻都留下了他的涂鴉作品,他通過涂鴉這種藝術行為質疑西方的精致文明,他常在作品中表達反對種族歧視、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等一些當代尖銳的話題。
二、班克斯的涂鴉藝術特點
(一)構圖中的留白
構圖是繪畫作品中最根本的結構框架,它是對整體畫面中的節奏、空間、形象、秩序感的安排,是揭示形象和表現思想的手段,體現著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和畫面的形式美感。班克斯的涂鴉作品在構圖上不同于其他涂鴉藝術家以畫面飽滿為主要手段,他有意在作品的構圖上留有空白以此凸顯畫面的視覺中心,如同中國傳統書畫藝術中的留白手法。例如:在墻壁的邊角進行畫面形象的安排或者是對畫面背景不做處理保持原有的墻面。構圖中留白的獨到之處不僅在于能夠將畫面主體形象通過正負形的對比進行強化,而且這種方式給予了觀者更多自由想象的空間。
(二)獨特的涂鴉形式
班克斯的涂鴉采用的是紙模噴涂的形式,這是一種近似模板印刷的方式,紙模具有價格低廉、便于攜帶、可重復使用的特點。班克斯將噴涂的形象事先用模板制作好,然后固定在墻面上用噴灌進行噴涂,作品完成后明暗對比鮮明,線條邊緣硬朗,具有質感,有著強烈的視覺效果。紙模涂鴉成為班克斯獨特的藝術標志,當然這樣做更有利于神秘的他快速完成作品。
(三)象征性的藝術符號
兒童的形象在班克斯涂鴉作品中出現的頻率極高,在涂鴉中他們被賦予了一種特定的意味。涂鴉最初作為人類表達情緒的方式,多是信手拈來,具有無意識的特點,如同兒童玩游戲。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兒童在潛意識里就有涂鴉的本能。班克斯作為一名和平主義者,一直關注著貧困和戰亂中的兒童,他的作品或是對兒童的天真、坦率特征的表現,或是對他們不幸遭遇的同情。老鼠、猩猩、和平鴿等動物形象在班克斯的作品中也極為常見,他通過擬人化的手法,為動物穿上衣服、舉著牌子或者拎著行李箱,他們有的神情慌張,有的抬頭張望,并在旁邊附上黑色幽默的獨白,好像動物在替人類鳴不平,看似好笑卻達到了反諷的藝術效果。
(四)戲擬拼貼的手法
班克斯善于將經典的形象挪用之后進行再創作。例如:他將塔倫蒂諾導演的電影《低俗小說》鏡頭中的手槍換成了沃霍爾作品中的香蕉形象,塔倫蒂諾導演的電影充滿著黑色幽默,而沃霍爾作為波普藝術的領軍人物主張藝術的大眾化,班克斯將它們重新組合并賦予新的內涵。他也善于將公眾人物的形象與特定的場所進行融合。例如:2015 年他在法國加萊“叢林”難民營繪制了一幅喬布斯背著行囊的難民形象,這種創作并不是肆意改造,而是有根據的,因為喬布斯是敘利亞的移民后裔。班克斯在涂鴉中采用戲擬拼貼的創作手法豐富了涂鴉藝術語言,更展現了他極高的藝術才華和想象力。
三、班克斯涂鴉藝術中的荒誕感
“荒誕”在語義上是不合邏輯的,在存在主義哲學中用以形容無意義、矛盾的狀態。“荒誕感”的產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固有的理性與信仰的情結在現代文化語境下的變異,即理性變為非理性,信仰陷入危機的結果[1]。法國作家加繆通過《局外人》這部小說揭示了世界中存在的不合理性、荒謬性,荒誕感的產生源自現代人信仰的缺失,人們常表現出一種焦慮、無力感甚至是冷漠。而“荒誕”并非理論常態上的非理性,在存在主義哲學中它是指具有清醒自我意識的局外人,是感性體驗和理性認知的統一。“荒誕”在審美形態上是反傳統、反形式、反美學的,這與班克斯在涂鴉創作中對抗主流、消解精英文化和揭示現實中的荒誕感是相吻合的。
觀看班克斯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其作品的主題對現實生活的反轉,他的作品整體呈現出一種詼諧幽默、荒誕諷刺感,這種荒誕源于現實,介于真實與荒誕之間。班克斯的作品更多不是將事件說完整而是留給觀者更多的思考空間,這是視覺藝術的特點所致,也是視覺藝術的魅力。一如尤奈斯庫所說:“藝術就是表達一種不可表達的真實,有時竟也表達了。這就是它的似是而非之處,是它的真理的所在。”[1]188班克斯的涂鴉在構圖上不拘泥于傳統涂鴉的滿,在色彩的使用上有所克制,有時近似黑白的單色畫,運用紙膜噴涂的形式營造出簡約的畫面感,他會根據要表達的情緒而加以醒目的顏色形成一種視覺上的反差。他將現實中的不合理性通過涂鴉作品進行反駁,運用視覺形象轉化文學語義上的荒誕概念,使得觀者經過視覺感官上的反應從而產生哲學上的思考。
種族歧視、難民問題和霸權主義……只要是這個世界上的尖銳話題,都會成為班克斯所表達的主題,正是由于這些荒誕的、不合理的問題的存在給了班克斯涂鴉創作的動力。班克斯是一位熱愛和平、具有社會意識的當代藝術家,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在巴以邊境的隔離墻上留下多幅作品,如有牽著氣球試圖穿越隔離墻的女孩、兩個兒童在隔離墻上挖洞透著遠處美好風景的畫面,班克斯借此表達他對以色列建立隔離墻這一荒謬行為的批評和諷刺。班克斯運用錯視畫法將富有象征意義的圖像安排在特定的場所里,他有意識地選擇使得這種反差產生了強烈的戲劇效果。
結語
當今的世界是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科技的進步、經濟全球化的快速進程使得人類的視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寬闊,互聯網縮短了人們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藝術史的進程不同于以往的線性發展,當代藝術呈現出多變的局面。產生于20 世紀70 年代的涂鴉藝術作為非主流、反傳統的標識自然有著其天生的弊端,但不得不承認它的出現改變了人們以往的視覺體驗,消解了大眾與藝術之間的距離感,拓展了藝術作品的呈現方式,在其自身不斷整合完善的過程中改變著城市的景觀,在此過程中大眾也逐漸認識到涂鴉藝術的價值。
藝術家的創作往往會受到時代的制約,但同時也反映著他所生活的時代。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班克斯通過他的涂鴉作品對世界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進行著沉默的批判,他那富有荒誕哲理的涂鴉作品不斷地喚醒著人們的社會意識,在復雜的當代社會環境中具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正如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的:“藝術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藝術形象的形式去顯現真實……”[3]68班克斯的藝術創作不為商業功利所動,他的涂鴉作品是發自內心的需要,是藝術家對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體現,源于現實的荒誕畫面訴之于人的感官,觸動著人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