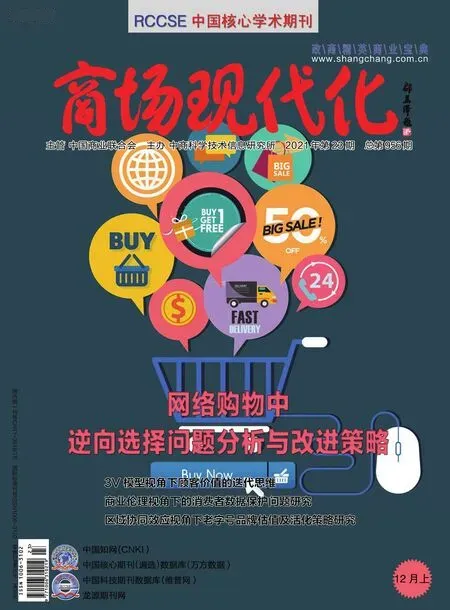淺談FCC、UGC在社交媒體下對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的影響
謝文君
摘 要:在這個時代,社交媒體平臺被整合到了營銷策略中。這項新技術提出了新的機制和溝通工具,公司可以依賴這些機制和工具與實際和潛在的客戶進行互動和接觸。本研究旨在探討以社交媒體為載體,進行的FCC、UGC對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的影響。本文從社交媒體的機會與挑戰,口碑營銷在社交媒體的應用,FCC、UGC在社交媒體的傳播三個方面,分析FCC、UGC在社交媒體下對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的影響。
關鍵詞:社交媒體;FCC;UGC;口碑;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
一、社交媒體的機遇與挑戰
1.社交媒體的概念
Mangold&Faulds(2009)將社交媒體定義為“消費者生成的媒體”,它導致了策略和通訊設備的重大變化,而它引領了營銷領域的一個新興現象——“線上消費者”。同時,根據Castronovo&Huang(2012)所述,社交媒體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平臺,營銷推廣工作可以通過社交媒體連接到一個易于訪問,也易于集成的、虛擬的、數據可搜集的消費者聚集場所。
2.社交媒體的機會
Constantinides和Fountain(2008)指出,Web2.0為營銷人員和公司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企業的主要機會是,通過web2.0的應用,管理者希望傳播的營銷信息可以更容易、更快、更具成本效益地傳遞給一群受眾或相關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企業還可以通過與市場和消費者保持聯系,有效地獲得更多關于消費者需求和相關選擇的信息,以及通過直接或個性化的一對一溝通和通常的一對多溝通與他們進行雙向溝通的互動,從而從中受益。
企業通過對希望溝通的消費者提供平臺,吸引更多消費者和利益相關者,鼓勵他們參與在線社區,將粉絲、追隨者和品牌傳道者聯系在一起,并允許他們與其他消費者互動,以及滿足消費者和企業之間的溝通需要。有了這樣的在線品牌社區,企業可以方便而有效地擴展自己的網絡,并通過為自己的品牌或產品創造積極的口碑來擴大自己的影響范圍,從而刺激消費者分享自己的網絡。
3.社交媒體的挑戰
企業面臨的挑戰可以歸因于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即眾多研究者聲稱的從企業到消費者的權力轉移。包括所有相關應用程序在內的社交媒體的出現,通過前所未有的授權給消費者,導致了“范式轉變”(Meadows Klue,2007)。因此,營銷人員應該學習新的溝通方式,并與這些強大的消費者互動,他們永遠不會輕易被老式的溝通方式打動,并在營銷過程中變得平等(Constantinides&Fountain,2007)。
盡管社交媒體降低了營銷人員通過傳統營銷傳播渠道影響消費者的能力,但社交網絡和在線口碑為組織提供了其他新渠道(Duan,2008)。此外,Mangold&Faulds(2009)提出由于權力從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企業失去了對信息的“內容、時間和頻率”的控制,而這些信息的組成部分在傳統的營銷渠道又控制了企業和品牌。同時,其他挑戰如負面反饋,可能會損害企業的聲譽,消費者對營銷人員信息的關注度較低,對預期信息的扭曲和修改,以及衡量社交媒體投資回報率的困難等,正是組織所面臨的。
二、社交媒體口碑(Word of Mouth)
即使企業和產品或服務信息的來源非常有效和可靠,點對點的溝通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同行的建議或意見可以極大地影響一個人的購買決策(Castronovo&Huang,2012)。對于這一現象,由于消費者傾向于高度信任其他個人的建議或決策,特別是當決策包含財務或心理風險時,口碑信息成為營銷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口碑不僅可以比其他傳統的廣告工具更有效地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而且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現有的消費者。
互聯網的出現使消費者有更多的機會從其他消費者那里收集有關特定品牌或產品的中立信息,并允許他們通過參與電子口碑(e-WOM)來提供自己的體驗或意見(Hennig-Thurau,2004)。Hennig-Thurau(2004)將電子口碑傳播(WOM)描述為“潛在的、實際的或以前的客戶對一個產品或公司所作的任何正面或負面的陳述,通過互聯網提供給其他人和機構,并指出電子口碑傳播(e-WOM)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如論壇和基于網絡的意見平臺。
Castronovo&Huang(2012)認為,由于消費者與其他消費者的人際聯系能力不斷增強,營銷人員應創造或提供一種強大的手段或有效的工具,以刺激企業和產品信息的迅速傳播。因此,口碑策略被視為整個在線傳播策略的關鍵組成部分,在線整合營銷傳播的目標是通過強調營銷人員希望與消費者溝通并在消費者之間共享的信息,為品牌或企業創造并保持積極的口碑消費者。
三、FCC、UGC在社交媒體的傳播
1.社交媒體的兩種作用
由于社交媒體被解釋為“促銷組合的混合元素”,Mangold&Faulds(2009)進一步解釋說,根據寶潔公司使用社交媒體的示范,社交媒體有兩個相關的促銷角色。
一方面,社交媒體允許組織與目標消費者溝通,這也是傳統IMC渠道的作用,但可以通過博客、facebook、微博、微信等平臺,這些平臺可以是公司贊助的,也可以是其他組織或個人贊助的。(Castronovo&Huang,2012)社交媒體的典型特征是其世界性的廣泛傳播,以及它能夠瞬間聯系或接觸到大量的人。因此,在WOM戰略中,社交媒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要使社交媒體成為一個有效的平臺,發揮組織的預期作用,社交媒體的存在就必須從企業的官方網站中滲透進來。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使消費者能夠實時地與無限多的其他消費者交談,而不是與過去效率低下的極少數人交談。Mangold&Faulds(2009)描述了社交媒體作為消費者之間溝通工具的第二個作用,并舉例說明文森特·法拉利發布了一段錄音來記錄他在客戶服務方面的體驗,然后被成千上萬的其他博客和網站點擊,這被認為是“病毒性的傳播”,最后以主流媒體之一的身份引起了《約克郵報》的關注。
此外,Mangold&Faulds(2009)聲稱,社交媒體的第二個作用可以看作是傳統口碑傳播的延伸。然而,e-WOM通信不同于傳統的WOM通信,因為它可以瞬間將一個客戶與數百萬人連接起來,而公司無法直接控制他們傳輸的信息。根據社交媒體的兩種角色,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的溝通一般可以分為用戶生成的溝通(User-generated Communication,UGC)和企業創建的(Firm- created Communication,FCC)社交媒體溝通,這也是基于信息的來源。
2.企業創造(FCC)和用戶創造(UGC)社交媒體傳播
根據Bruhn(2012),企業創造和用戶創造的社交媒體傳播都是輸入因素,這兩種傳播的區別體現了到了一個社交媒體下營銷的事實,即個人客戶和生產者都是基于品牌的信息發送者,甚至是創造者。
(1)UGC的特征
Kaplan&Haenlein(2010)指出,用戶生成內容(UGC)可以解釋為“人們能夠使用的社交媒體的所有方式的集合,該術語通常涉及由最終用戶創建并公開提供的各種形式的媒體內容”。因此,UGC有三項基本特征:第一,訊息或內容應是在公眾網站上公布的、可供特定目標人士使用的訊息或內容;第二,需要創造性的努力或想法;第三,訊息最好是在沒有專業營銷的途徑和操作的情況下創作。
(2)FCC、UGC在企業控制與運用上的不同
Bruhn(2012)強調了由于公司對社交媒體上的用戶生成內容(UGC獨立于公司控制)和企業創建的社交媒體上的通信(FCC受控于公司控制)的控制程度不同,這兩種社交媒體上的通信在社交媒體戰略中都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Bruhn表示,企業創造的傳播和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創造的內容的不同主要表現與信息來源可靠性的不同與消費者對品牌形象維度的意識的不同。
企業在社交媒體上創建的傳播(FCC),可以相當程度地促進消費者功能性品牌形象的提升,而社交媒體上用戶生成的內容(UGC)可以積極影響享樂品牌形象。然而,Bruhn(2012)指出,雖然企業不應利用社交媒體上的企業創造傳播(FCC)來提高享樂品牌形象,但它們可以用來影響消費者對消費者的傳播(UGC)。
(3)UGC的負面影響
然而,Constantinides&Fountain(2007)證明,UGC可能對既定的企業文化造成“危險”。這種危險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匿名業余視頻和音樂混剪發布到公共網站”,如YouTube、優酷、嗶哩嗶哩等混剪視頻,導致觀眾混淆廣告、小說和現實;二是催生了專業化娛樂業產生的“知識產權濫用”。
四、品牌價值
Aaker(1996)將品牌價值定義為:“與品牌名稱和符號相關聯的資產(和負債),增加(或減去)產品或服務為公司和/或公司客戶提供的價值”。品牌價值可以解釋為“基于企業提供的基本價值和功能價值而產生的產品或服務的額外價值”。
Campbell(2002)指出,建立一個成功的品牌,或在消費者與品牌之間建立牢固關系的關鍵因素是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和信任,這兩個因素也會影響品牌價值和品牌發展。
通過不斷的努力,品牌價值的形成可以通過成功地將符號或事物與品牌結合來實現。然后,品牌知識可以通過品牌價值來提供,品牌價值對基于消費者的品牌價值(客戶對品牌的反應)和與企業相關的品牌價值(與公司在市場上為品牌所做的努力有關)具有不同的影響(Aaker1996;Keller1993;Shamma & Hassan,2011)。
1.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
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可以理解為品牌知識對消費者對品牌的反應具有差異性效應(Keller,1993),因此應強調三個要素:品牌知識、差異效應和消費者反應。此外,品牌知識包括品牌意識和品牌聯想兩個方面。品牌意識是指消費者對品牌的回憶或認可程度在消費者心目中的記憶。品牌聯想是指顧客的品牌形象,可進一步分為功能性品牌形象和享樂性品牌形象(Bruhn,2012)。
此外,Bruhn(2012)指出,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是企業創造的品牌傳播(FCC)和用戶創造的品牌內容(UGC)或對其他顧客在社交媒體上的品牌活動作出反應的結果,而不是他們對同等價值但未品牌化的產品的反應。顧客的品牌態度可以代表對一個品牌的總體評價、品牌價值的多元構成與品牌相關的屬性或利益,品牌態度會受到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的影響(Bruhn,2012)。
2.社交媒體下的品牌價值鏈模型
在21世紀,消費者的社會信息已經從無形的信息傳播到現實的信息傳播。Bruhn(2012)指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影響客戶各個方面的關鍵因素,包括“意識、信息獲取、意見、態度、購買行為以及購買后的溝通和評估”。
因此,Bruhn(2012)基于Keller&Lehmann(2003)的理論構建了品牌價值鏈模型,Keller&Lehmann(2003)的品牌價值模型考慮了由于營銷組合產生的不同影響,而Bruhn考慮到客戶信息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廣泛交換的顯著影響,修改了該模型,以適應社交媒體上企業創造的傳播和用戶生成的內容,而不是傳統的品牌價值鏈,因為后者僅限于由公司直接控制的營銷傳播。
根據Bruhn(2012)的模型,品牌價值鏈的結構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品牌內容的發送者(包括作為傳統渠道或社交媒體傳播者的企業和作為內容創造者的消費者);第二,消費者的品牌態度,包括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第三,顧客行為作為口碑或購買意圖的反映;第四,企業的財務業績。
3.社交媒體下的FCC、UGC對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的影響
此外,Bruhn(2012)指出,第二和第三層次構成了基于顧客的品牌價值。根據Weinberg&Pehlivan(2011),傳統營銷傳播的目標可以歸納為與客戶品牌價值相對一致的“認知、知識、召回、購買”,而社交媒體的傳播目標則表現為“對話、分享、協作、參與、傳播”。
因此,企業創造和用戶生成的社交媒體傳播(兩個信息發送者)與基于客戶的品牌價值(也被稱為傳統目標品牌意識和品牌形象)之間的關系清楚地顯示為品牌價值的前三個層次(Bruhn,2012)。
根據Bruhn(2012)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企業創造的傳播(FCC)和用戶在社交上生成的內容(UGC)都會提高品牌知名度。企業在社交媒體上創造的傳播會影響功能性品牌形象,而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產生的內容會影響享樂品牌形象。進一步驗證了品牌意識、品牌形象與品牌態度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五、總結
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給企業營銷同時帶來了機遇與挑戰,電子口碑傳播在社交媒體營銷下凸顯了重要作用,通過網絡激勵的消費者內容生成雖然相較企業創造的傳播難以被企業所控制,同時UGC存在著一定的負面風險。但是,根據新的社交媒體下的品牌價值鏈模型可以知道FCC、UGC與基于客戶的品牌價值之間的關系清楚地顯示為品牌價值的前三個層次,具體表現為FCC、UGC都會提高品牌知名度,而FCC在社交媒體上更多影響功能性品牌形象,UGC在社交媒體上會影響享樂品牌形象。
參考文獻:
[1]Bruhn, M., Schoenmueller, V., &
[2]Castronovo, C., & Huang, L., 2012. Social media in an alternativ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odel. Journal of Marketing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6(1),pp.117-134.
[3]Constantinides, E., & Fountain, S. J., 2008. Web 2.0: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marketing issues. Journal of Direct, Data and Digital Marketing Practice,9(3),pp.231-244.
[4]Duan, W., Gu, B., & Whinston, A. B., 2008a. Do online reviews matter?—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anel dat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45(4),pp.1007-1016.
[5]Keller, K. L., 2009. Building strong brands in a modern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15(2-3),pp.139-155.
[6]Mangold, W. G., & Faulds, D. J., 2009. Social media: The new hybrid element of the promotion mix. Business horizons,52(4),pp.357-365.
[7]Pickton, D., & Broderick, A.,2005.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Harlow:FT Prentice Hall. Financial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