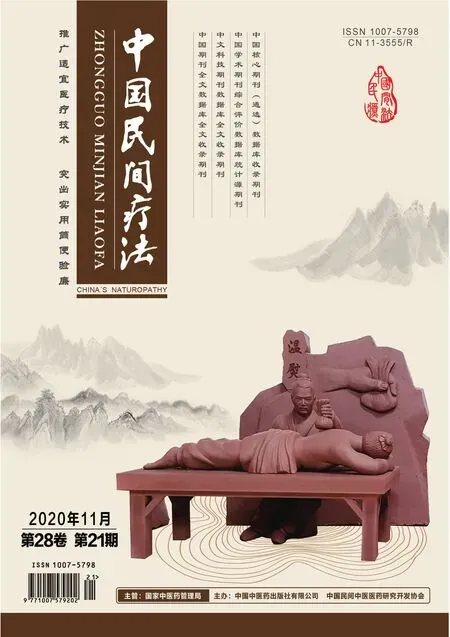賈躍進應用四妙散驗案舉隅※
劉 毅,何曉瑜,王瑞敏,張譯心,賈躍進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晉中030619;2.山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西 太原030024)
四妙散是在《丹溪心法》二妙散的基礎上,加牛膝、薏苡仁而成,出自《成方便讀》。方中黃柏為君,苦寒清熱燥濕;蒼術為臣,芳香燥濕健脾,使水濕祛而不易生;牛膝補肝腎、強筋骨,引藥下行使藥達病所;佐薏苡仁淡滲甘緩,利濕熱而舒筋絡。全方藥簡力專,攻補兼施,常治療濕熱下注類疾病。
賈躍進老中醫是第6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碩士研究生導師,有30余年的臨證經驗,擅于應用中醫藥治療神經內科疾病及多種臨床常見病。賈師應用四妙散時不拘于濕熱下注類疾病,而是以“濕性趨下”的特性為出發點,靈活運用此方化裁治療多種濕熱類疾病,本文以5個驗案以窺賈師治療濕熱之經驗。
1 玫瑰糠疹
患者,女,46歲,以“遍身皮疹1年余”為主訴于2019年8月27日初診。患者2018年5月無明顯誘因出現右下肢膿包,后經太鋼醫院切開引流后痊愈,2018年9月周身遍發皮疹,太原市中心醫院診斷為 “玫瑰糠疹”,服藥及光療治療后無效。后經山西中醫研究所分院治療后好轉。2019年3月復發加重,5月服藥減輕,7月又嚴重。刻下癥:全身紅色皮疹,水皰,瘙癢,色素沉著,乏力,身熱,易出汗,納可,大便秘結,小便正常,睡眠不佳,易驚醒,醒后不可再眠,舌胖苔黃膩,脈數。西醫診斷:玫瑰糠疹。中醫診斷:風熱瘡;辨證:濕熱釀毒。治以清熱燥濕解毒。處方:蒼術18 g,黃柏15 g,炒薏苡仁45 g,土茯苓30 g,茵陳30 g,苦參10 g,白鮮皮15 g,浮萍15 g,合歡皮20 g,金銀花20 g,枳實12 g,炒萊菔子20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2019年9月3日二診:大腿根紅疹,癢甚,灼熱,納可,失眠,二便調,雙手水皰減少,舌胖,脈沉。上方加赤小豆30 g,服法同前。2019年9月16日三診:全身癢明顯好,未再發疹,遂不更方,隨癥加減再服7劑。
按語:玫瑰糠疹(ptyriasis rosea,PR)是臨床皮膚科常見病,發病原因尚不明確,特征皮損為覆蓋糠狀鱗屑的紅斑丘疹,相當于中醫“風熱瘡”。清·陳士鐸言:“風熱瘡,多生于四肢胸脅,初起如疙瘩,癢而難忍。”[1]根據該患者皮損特點診斷為水皰型PR。該患者纏綿難愈、反復發作、乏力,乃濕邪為患之象,加之身熱、大便秘結、汗出、舌脈等,提示熱象較著,故可從濕熱入手。賈師認為“聚而不散謂之毒”,此病乃濕熱搏結于皮膚聚而不散而成疹瘡,故診為濕熱釀毒。以四妙散化裁,投以大劑量蒼術、黃柏、薏苡仁清熱燥濕;重用土茯苓、茵陳、白鮮皮、金銀花等清熱解毒,強化清利濕熱之功,解其疹瘡;“諸癢皆屬于風”,故加浮萍等疏解風熱,解其瘙癢;合歡皮解郁安神,安其失眠;枳實、炒萊菔子利其便秘,通腑以調暢全身氣機,亦可給邪以出路。全方主次兼顧,分別從內、外、下三路祛邪解毒且兼以健脾、安眠。“諸痛癢瘡,皆屬于心”,二診投以赤小豆,色赤入心,同時清濕熱;久病多瘀,兼見色素沉著,赤小豆亦有散血之效,故三診諸癥悉除,邪祛正安。
2 汗證
患者,男,49歲,以“汗多2年”為主訴于2019年7月15日初診。刻下癥:飽食時汗甚,頭汗,時夜汗,五心煩熱,納可,口干,口苦,眠差,大便正常,小便黃,舌胖,齒痕,苔膩,脈數。中醫診斷:汗證;辨證:濕熱上蒸,中焦郁滯。治以清熱燥濕,健脾退熱。處方:蒼術15 g,黃柏15 g,炒薏苡仁30 g,黃芩片10 g,土茯苓30 g,滑石15 g(先煎),牡丹皮15 g,地骨皮15 g,茯苓20 g,川牛膝12 g,豬苓30 g,生麥芽30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2019年7月22日二診:汗多好轉,小便黃,納可,眠輾轉不寧,未打鼾,大便正常,面油膩,舌胖,脈沉,上方加地骨皮20 g,澤瀉12 g,服法同前。2019年7月29日三診:汗多、面油膩好轉,余皆正常,效守上方,服法同前。
按語:汗證指由于陰陽失調,腠理不固,而致汗液外泄失常的病證[2]。《素問·陰陽別論》認為:“陽加于陰謂之汗。”[3]該患者主要表現為飽食汗甚,頭汗,《脈因證治》載:“胃熱上熏,頭汗。”[4]《雜病廣要》亦述:“食湯飯酒面,使熱蒸于上,則頭面汗出,淋漓疏泄,故謂之頭汗,此陰虛不能以附陽也。”[5]認為汗證是濕熱上蒸、陽明有熱所致。飲食不節,傷及脾胃,釀為濕盛,久而郁熱,濕熱熏蒸,循經而上,迫津外泄,頭汗乃出。濕熱纏綿,病程較長,中焦郁熱,胃不和則臥不安,故其眠差;另其口干、苦,小便黃,舌脈俱是濕熱癥狀;久汗傷陰,故有夜汗、五心煩熱等陰虛癥狀。賈師觀其脈證,以四妙散加減濟之,并加黃芩、土茯苓益清濕熱之力;牡丹皮、地骨皮解陰虛之熱;滑石清熱利尿,使邪從下而祛,并減其溺黃;豬苓、茯苓利水滲濕,茯苓寧心安神可緩解眠差;麥芽稟春生之氣,顧護脾胃。諸藥共奏清濕熱、退虛熱、健脾胃之功,方證相應,故二診好轉,三診得康。
3 痛風
按語:痛風是由尿酸排泄減少或嘌呤代謝紊亂導致的一種晶體性關節炎[6],屬于中醫“歷節”“痹證”等范疇。《景岳全書》云:“蓋痹者閉也,以血氣為邪所閉,不得通行而病也。”[7]其中濕熱痹阻是痛風發病的主因[8],吳鞠通言:“寒濕固有,熱濕尤多。”本案因患者素體氣血不足,勞累加重,且食用海鮮,損傷脾胃,釀生濕熱,濕熱之邪下襲陰位,循脾經閉阻足趾氣血,故急性發作,紅腫熱痛,下午加重,行動不利。此濕熱下注、血行不暢之痹證當以四妙散方投之,清利下部濕熱,土茯苓為治療痛風要藥,清熱除濕,利關節;豬苓、車前子清利濕熱,利小便;延胡索、乳香、莪術活血行氣,消腫止痛;生麥芽行氣健脾。諸藥相合,清利濕熱,活血止痛,調節氣機,急則治標不傷正,控制活動期的濕熱痹。二診好轉后加麩炒白術健脾利水,木瓜舒筋活絡、和胃化濕。此階段治以健運脾胃,杜絕生濕,生化氣血,扶正祛邪。三診進入緩解期,加行氣祛風止痛之僵蠶、川楝子,疏通全身氣血,防止反復發作。賈師臨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分階段對癥治療,重視調氣血,兼顧脾胃,是故方隨法出,藥到病除。
4 痤瘡
患者,女,36歲,以“面紅疹伴小白頭10年,再發2個月”為主訴于2019年8月5日初診。刻下癥:面紅疹件小白頭,按之覺痛,下頜多,經前多發,或腰困,月經有血塊,納可,口中異味,大便2~3日一行,質黏,小便黃,乏力,頭油膩,齒痕,苔膩,脈弦。西醫診斷:痤瘡。中醫診斷:粉刺;辨證:濕熱釀毒。治以清熱燥濕,解毒透疹。處方:蒼術15 g,黃柏15 g,炒薏苡仁30 g,土茯苓30 g,金銀花20 g,連翹20 g,赤芍15 g,川楝子10 g,黃芩片10 g,豬苓15 g,枳實15 g,炒萊菔子20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2019年8月15日二診:藥后紅疹明顯減輕,僅額頭一個紅疹,口異味好轉,納可,口干,睡眠6~7 h,遇事則眠淺,大便不成形,質黏好轉,2 d一行,小便黃減輕,舌胖,脈弦。上方加芡實30 g,服法同前。
按語:痤瘡是臨床發病率較高的一種損容性毛囊皮脂腺疾病,好發于身體富含皮脂腺的部位[9]。《素問·生氣通天論》載:“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為皶,郁乃痤。”[10]說明濕邪郁而化熱釀毒是其發病的重要病機。體質學研究亦表明,痤瘡的形成與濕熱有關[11]。賈師臨證尤善將病、證、體結合以綜合分析診治,本案患者面紅疹、白頭,可辨病為粉刺;口干苦,大便黏而不暢,小便黃,頭油膩,舌齒痕,苔膩,乃濕熱之象;濕熱蘊于肌膚釀毒而生粉刺,濕熱傷脾,故下頜多見;女子素體以肝為先天、以血為本,易肝氣郁滯,氣血失調而化熱,濕熱搏結,纏綿難治,經前陰液下注,陽熱上犯,濕熱熏蒸面部而痤瘡加重。故方選四妙散化裁以清利濕熱,解毒透疹;土茯苓、銀翹清熱解毒,祛衛表之濕熱蘊毒;久病多瘀,加赤芍、黃芩清熱涼血散瘀;川楝子活血行氣;豬苓清熱利濕,利小便;枳實、萊菔子通腑泄濁,給邪以出路。全方表里兼顧,主次皆具,服方癥減;二診守原方,佐芡實除濕止瀉,諸癥乃解。
5 痿證
患者,女,53歲,以“雙下肢無力7個月余”為主訴于2019年6月10日初診。患者7個月前因感冒出現雙腿疼痛,與冷熱無關,10 d后疼痛消失但出現雙下肢無力,不能行走,多方診治,效果欠佳。曾就診于山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診斷為“脊髓炎”。刻下癥:雙膝怕冷,雙腿腫脹,汗多,素怕冷,納差,多食胃脹不適,情緒平穩,眠可,大便10余日一行,小便黃,有熱感,口干喜涼飲。既往史:2012年心臟瓣膜置換術,口服華法林。查其舌胖,中心黃膩,脈數。中醫診斷:痿證;辨證:濕熱阻滯,經絡閉阻。治以清熱燥濕,通利經脈。處方:蒼術20 g,黃柏20 g,炒薏苡仁45 g,牛膝30 g,木瓜12 g,知母15 g,僵蠶10 g,火麻仁30 g,車前子20 g,枳實15 g,炒萊菔子20 g,厚樸15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2019年6月17日二診:小便不暢好轉,大便7 d一行,不思飲食,飯后胃脹,眠可,攙扶勉強步行,項部紅疹,舌胖齒痕,脈弦。上方加麩炒白術30 g,金銀花15 g,大黃6 g,服法同前。2019年6月24日三診:用大黃后大便可通,小便不暢好轉,納可,雙下肢乏力好轉,苔黃,脈沉弦。上方加莪術10 g,服法如前。2019年7月8日四診:右下肢沉重好轉,雙膝冷好轉,大便兩日一行,小便正常,汗出如流好轉,項部紅疹明顯好轉,齒痕,脈弦。上方加黃芪45 g,服法同前。
按語:痿證指肢體筋脈弛緩,軟弱無力,不能隨意運動,或伴有肌肉萎縮的一種病證[12]。《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10]可見濕熱是痿證的重要病因。本案患者雙下肢無力、腫脹,行走不得,病屬“痿證”;便秘、溲黃,渴喜涼飲,結合舌、脈象,提示濕熱阻滯;久病易虛,并見脾胃虛弱之征。處方以四妙散加減以清利濕熱,通利經脈;“治痿獨取陽明”,薏苡仁入陽明;懷牛膝長于補肝腎、強筋骨;入木瓜舒筋活絡,和胃化濕;知母清熱生津,解其口干;僵蠶通其經絡;火麻仁、枳實、萊菔子解其便秘,通其腑氣;“濕者當利小便”,佐以車前子通其小便,利其濕熱;厚樸理氣化濕。全方藥簡力宏,治療主癥的同時,兼顧兼癥,故二診好轉。濕熱漸祛后又以黃芪、麩炒白術補氣健脾,益其正氣;大黃通大便,瀉其腑氣;久病多瘀,莪術破氣行血,標本兼治,下肢復康。
6 小結
賈師治療濕熱為病時以“濕性趨下”為出發點,從而靈活應用四妙散化裁,以法系方,異病同治;在清利濕熱過程中治病求本,標本兼顧;與此同時還注重調理氣機和后天之本,強調給邪以出路,在長期臨證中效驗甚眾。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四妙散具有抗菌抗炎、解熱鎮痛、鎮靜、降低血尿酸水平、增強代謝水平等作用[13-15],故可治療和緩解以上與炎癥反應、免疫反應、感染及與尿酸水平、代謝水平相關的疾病。賈師應用四妙散之法治療濕熱為患,科學安全有效,應用廣泛,應進一步思考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