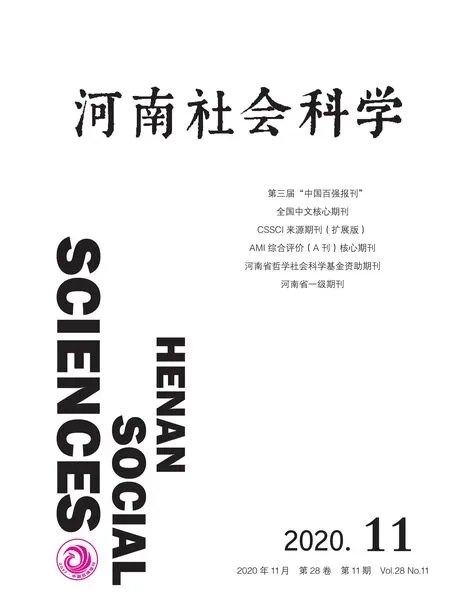墨家邏輯與科學思維
楊武金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中華民族具有優(yōu)秀的科學思維傳統(tǒng),比如歷史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等。墨家學派所創(chuàng)立的墨家邏輯對這種科學思維傳統(tǒng)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墨家邏輯是由中國先秦時代的墨子及其弟子所創(chuàng)立起來的系統(tǒng)邏輯學說。墨家邏輯通常也稱為“三物邏輯”。三物者,故、理、類也。《墨子·大取》說:“三物必具,然后(辭)足以生。……(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推理論證要得出可靠結論,必須故、理、類三者全都具備。沈有鼎說:“‘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十個字替邏輯學原理作了經(jīng)典性的總結。”[1]336科學思維首先是合乎邏輯的思維,墨家的故、理、類“三物邏輯”思想,是墨家科學思維的核心部分,對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科學思維傳統(tǒng)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求故思維
通常說,事出有因。荀子說:“辭之有故。”(《荀子·非十二子》)尋故、探故是中國思維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傳統(tǒng)應該是從墨家開始的。墨家說:“(辭)以故生。”(《墨子·大取》)墨家非常重視對“故”的探討,強調(diào)“故”在推理論證中的根本性作用。“故”可以是事物現(xiàn)象發(fā)生的原因或者本質(zhì),同時也可以是推理或論證的理由或根據(jù)。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哲學上主張“四因說”,強調(diào)對萬事萬物存在的四種原因,即質(zhì)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動力因的探討,是對事物本體論的探討,是對人們關于事物存在性的反思。他說:“既然我們的事業(yè)是為了獲得知識,而在發(fā)現(xiàn)第一事物的為什么,即把握其最初的原因之前,是不應該認為自己已經(jīng)認識了每一事物,那么顯然,我們應該研究生成和毀滅以及一切的自然變化,并引向對它們本原的認識,以便解決我們的每一個問題。”[2]把握事物的原因是獲取知識的前提。中國先秦時代的墨家學派認為,“故”是萬事萬物呈現(xiàn)的各種原因,同時也是推理或論證的理由或前提。
首先,墨家把“故”看成推理或論證的理由或者根據(jù)。在墨家看來,推理論證活動是人們非常重要的認知活動,是人們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從而也是科學思維中非常核心的部分。《墨子·經(jīng)上》說:“故,所得而后成也。”理由就是有了它就能推出結論的東西。《墨子·經(jīng)說上》說:“故:有之必然。”有了理由或前提就一定能夠得出結論。《墨子·小取》說:“以說出故。”通過推理論證可以將結論推導出來。墨子在論辯活動中,經(jīng)常針鋒相對地指出對方“未明其故”(《墨子·非攻下》),即對方不明白、不清楚己方說話的理由。墨子認為,在辯論過程中,“無故”即缺乏理由的一方要服從“有故”即有理由的一方。
其次,墨家把“故”看成事物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可以作為類比的對象來說明理由或前提的。墨家把“故”區(qū)分為大故和小故。其中“小故”是“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墨子·經(jīng)說上》),有前提不一定就能夠得到結論,但沒有前提卻一定不會得到結論,小故是推出結論的必要條件。“大故”則是“有之必然”(《墨子·經(jīng)說上》),有了前提就一定能夠得出結論,大故是得出結論的充分條件。關于什么是“小故”,墨家就舉“若(尺)有端”(《墨子·經(jīng)說上》)來說明,就像有點不一定有線,但沒有點一定沒有線那樣,有點是有線的必要條件。關于什么是“大故”,墨家就舉“若見之成見也”(《墨子·經(jīng)說上》),即人們之所以能夠看見物體,是因為有良好的視力、足夠的光線、適當?shù)木嚯x等條件都具備了的原因[1]333。在墨家看來,事物的“故”也就是事物的“所以然”,《墨子·小取》說“摹略萬物之然”,即探索萬事萬物的所以然之故,強調(diào)對事物原因的認識。
在墨家看來,事物存在的客觀上的因,決定了人們認知活動中的理由或者“故”,當然這種“因”和“故”之間不一定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墨子·經(jīng)下》說:“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墨子·經(jīng)說下》說:“或傷之,然也。見之,知也。告之,使知也。”事物何以是這樣的,與我們何以知道事物是這樣的,與我們何以使得別人也知道事物是這樣的,不一定相同,可以用生病的情況來進行說明。有人受到傷害,這是他生病的原因;看見有人被傷害,是知道他被傷害的理由;將他被傷害的事情告訴別人,則是使得別人也知道事情的真相。
事實上,墨家在實際的思維論證中經(jīng)常通過結果來探求事物的原因,這說明墨家是非常重視對事物因果關系的認識的。比如,墨子為了論證兼愛的重要性,首先就追問天下之所以亂的原因是什么,《墨子·兼愛上》說:“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天下之所以亂的原因就在于人與人之間不相互關愛,臣不孝君、子不愛父、弟不愛兄,同時,父不愛子、兄不愛弟、君不愛臣,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不能互相關愛,這是天下之所以大亂的根本原因。這里,墨家論證了“兼愛”是天下大治的“小故”即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兼愛天下就會亂,只有實行兼愛才能實現(xiàn)天下大治。同時,墨家還進一步論證了兼愛也是實現(xiàn)天下大治的“大故”即充分條件。《墨子·兼愛上》說:“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所以,兼相愛則天下大治、家庭和睦,人們就能夠生活在幸福之中。所以,墨子最后得出結論說:“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墨子·兼愛上》)總之,兼愛是實現(xiàn)天下大治,實現(xiàn)社會和諧、世界和諧和家庭和睦,以及個人生活幸福的既充分又必要的條件。
類似的,墨子為了論證節(jié)用的重要性,也是追問古代圣王為何沒有發(fā)動戰(zhàn)爭、沒有過度役使人民、沒有向老百姓征收重稅,但也能夠實現(xiàn)國家財富倍增,根本原因就是他們能夠節(jié)約用度。《墨子·節(jié)用上》說:“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圣王為政,其發(fā)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去其無用之費是圣人之所以既沒有發(fā)動戰(zhàn)爭,也沒有過度役使人民、沒有向老百姓征收重稅,卻能夠實現(xiàn)國家財富倍增的根本原因。
二、立法思維
法治精神一直是中國人的思維傳統(tǒng)。法治思維在中國古代就已經(jīng)形成,其中墨家的“法”思想對于中國古代的法治思維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作用。
墨家“三物邏輯”(故、理、類)認為,“法”是推理論證能夠得出合理結論的基本依據(jù)。墨家也稱法為“理”或“道”。《墨子·大取》說:“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人們沒有道路就無法行走,雖然有強健的四肢,如果不明白路在哪里,那困難立刻就會到來。也就是說,推理論證如果沒有法,就失去了依據(jù),自然也就容易陷入困境。
當然,墨家的“法”也是判斷言辭的真假、是非的標準。《墨子·小取》說:“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判斷言論的是還是非,即正確還是錯誤,必須根據(jù)“法”來進行。符合“法”則為是,不符合“法”則為非。墨子專門提出“三表”作為判斷言論是非的根據(jù)。《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將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實、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作為衡量言論是非的三個重要標準。《墨子·非命上》說:“子墨子言曰:‘(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fā))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言論沒有衡量標準,就好比在制陶輪盤之上,放立一個測量時間的儀器,是非利害之分是不可能弄明白的。“三表”是衡量是非利害的三個根本性標準。其中,第一表是“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是要尋找歷史證據(jù),溯源到古時候圣王的歷史事跡,體現(xiàn)出墨家具有歷史思維的特點。《墨子·非命中》說:“然胡不嘗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fā)憲布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fā)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古代圣王選拔孝子,鼓勵他侍奉雙親、尊敬賢良,鼓勵他做善事,頒布法令以教誨人民,嚴明賞罰以獎善止惡。如果能夠這樣做,則混亂就可以治理,危險就可以轉化為安寧。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人民還是那樣的人民。安危治亂,這與命沒有什么關系,關鍵在于統(tǒng)治者能否根據(jù)實情制定法律法令加以執(zhí)行。
墨家也在法律、法令或者法規(guī)的意義上來使用“法”這個概念。《墨子·辭過》說:“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圣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奸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這里的法令是“法”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刑罰”則是刑律上的懲罰措施。《墨子·經(jīng)上》說:“罪,犯禁也。”罪是做了違反法律、法令所禁止做的事情。《墨子·經(jīng)說上》說:“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高亨的解釋是:“人之有罪,只限于犯禁;設其所為,不在法禁,雖害于人,亦無罪。”即如果行為不在法律禁止的范圍內(nèi),即使有害的行為也是無罪的。高亨將“殆姑”校勘為“若詒”,就像欺負人那樣,雖然有害于人,但不在法律禁止的范圍之內(nèi),所以這種行為屬于無罪。
從墨子的“三表”法來看,墨子能夠將之作為法的東西,其本身也一定是可靠的、經(jīng)得住考驗的事實或正確理論。《墨子·經(jīng)上》說:“法,所若而然也。”法就是遵循它就可以成就結果的東西。《墨子·經(jīng)說上》說:“意、規(guī)、圓三也,俱可以為法。”即圓這個詞的含義、圓規(guī)和圓形三種東西,都可以作為制作圓的標準或者方法。《墨子·法儀》篇論證百工從事都重視依法從事,所以統(tǒng)治者治理國家不可以無法無天,墨家把“法”看成一種政治制度。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這個故事說的就是社會生活是復雜的,人也是復雜的。因此,無論國家治理還是社會治理,都必須依法行事,也就是按理行事、依法行政,才能實現(xiàn)社會安定、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墨子·當染》說:“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當。”成功的統(tǒng)治者行政的根本方法或道理就是按理行事、依法行政。
那么,實現(xiàn)社會治理的根本法或理又是什么呢?在墨子看來,尚賢就是政治正確的理論。《墨子·尚賢上》說:“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yè)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志),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尊重賢才、尚賢,起用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是國家政治的根本。《墨子·尚賢上》說:“故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nóng)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德行和能力是衡量一個人才的根本性標準,也是任用人才的根本理法。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清華簡·治邦之道》中的“尚賢”思想與《墨子·尚賢上》中的尚賢思想非常類似。其中說道:“故禍福不遠,盡自身出。故昔之明者早知此患而遠之,是以不殆,是以不辨貴賤,唯道之所在。貴賤之位,豈或在它?貴之則貴,賤之則賤,何寵于貴,何羞于賤?雖貧以賤,而信有道,可以馭眾、治政、臨事、長官。”[3]在國家治理之中,絕對不能分富貴貧賤,而是應該大力使用有道之人,對于有能力、有德行的人,要大膽使用,敢于使用,及時使用,對無能力或者缺德的人要及時罷免,不然后患無窮,災難就會接踵而至。因此,在墨家看來,實現(xiàn)社會治理的根本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事。《墨子·尚同上》說:“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網(wǎng)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古代圣王設立五種刑罰,用來治理人民,就像絲線有紀(總繩)、網(wǎng)有綱一樣,是用來控制天下那些不向上統(tǒng)一于上級的老百姓的。
從《墨子》的《法儀》篇和《天志》篇來看,能夠作為法的東西,其實也就是要符合“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或標準。墨子提出“非命”“尚力”的主張,主要就是基于人可以通過制定法律法規(guī),從而來更好地行政。在墨家看來,在國家政務中實踐“兼相愛”“交相利”并不難,關鍵在于領導者能夠將之作為法來推廣和宣傳。墨子指出,像攻城野戰(zhàn),殺身為名,這樣的事情才是人們最難做的,但是只要統(tǒng)治者愿意做,老百姓都能跟從著去做。而且“兼相愛”“交相利”與攻城野戰(zhàn)、殺身為名這樣的事情完全不同。《墨子·兼愛中》說:“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兼愛是非常容易實踐的事情。墨子還舉大禹治水、周文王治理西岐、周武王拯救夏商百姓等,都是兼愛精神的體現(xiàn),都能說明兼愛是完全可以實踐的,關鍵在于領導者將它作為法儀來進行宣傳和推廣。
三、明類思維
中國向來擅長類比推理和類比思維,韓非子通過楚國“矛和盾”的故事,來類推“不相容之事不能兩立”的道理,公輸般(魯班)從被茅草劃破手指頭,開始觀察一葉茅草兩邊細小而鋒利的鋸齒之后,發(fā)明了對木匠來說非常有用的鋸子,類比思維是一種創(chuàng)新思維。
在中國人邏輯思維和中國邏輯史的發(fā)展歷史進程中,類概念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類概念在邏輯科學中是一個最基本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范疇,或者說它是邏輯科學——關于人類思維的形式和規(guī)律的科學——借以產(chǎn)生的基礎。在中國最古老的歷史文獻《易經(jīng)》等著作中,還無“類”字出現(xiàn),但是,在《尚書》《周禮》《詩經(jīng)》《左傳》《國語》等著作中,“類”字出現(xiàn)得越來越多,含義也不盡相同,有表示祭名的,有表示善意的,有表示族類的,也有表示物類、事類的,也有表示類似的意思。《論語》中出現(xiàn)“有教無類”的表述,其中的“類”當為族類的意思。在《墨子》一書中,“類”字大量出現(xiàn),同時具有類比、類推、推理的含義。事實上,墨家的言論大多不是通過直敘而是通過類比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類概念在墨家的思想體系中已經(jīng)作為一個邏輯的范疇得到呈現(xiàn)。
墨子非常重視類比和推理的作用。《墨子·魯問》篇記載,墨子的弟子彭生子對墨子說:“往者可知,但來者不可知。”這時,墨子問他:“假設你在百里之外的親人得了重病,你如果能夠及時到達則親人就能得救,如果不能及時到達則親人就會不在人世。現(xiàn)有兩輛馬車,一輛好車,能夠及時到達,另一輛破車,要很久才能到達。請問你到底希望乘哪一輛車呢?”彭生子回答說:“當然是乘快的那一輛了。”墨子于是說:“看來未來的事情也是可以知道的啊!”即推理是有巨大作用的。墨子在與彭生子的對話中,也使用了類比推理來進行論證[4]。不過,墨家所考慮的類比推理比我們一般所說的類比要深刻得多,因為它把演繹和歸納都包括在其中了。沈有鼎說:“古代中國人對于類比推論的要求比較高,這是因為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類比推論有著極廣泛的應用。”[1]336
墨家認為,在推理論證過程中,明確類同類異,是進行正確推理的必要前提。墨家認為,在證明和反駁中都必須根據(jù)類的原則來進行。墨子在論證的過程中,經(jīng)常批評對方“未明吾言之類”(《墨子·非攻下》),即“不明白我所說話的類別”。《墨子·經(jīng)上》說:“立辭而不明于其類,則必困矣。”不明白事物的類別必然會陷入困境,從而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墨家因而提出“同類相推”“異類不比”的基本推論原則。即在推論過程中必須區(qū)分類同還是類異。墨家區(qū)分了各種不同的“同”和不同的“異”。《墨子·小取》說:“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無論證明還是反駁都必須根據(jù)類的要求來進行。如果在同類的范圍之內(nèi),則可以根據(jù)同法的原則來進行推論,同類則同法。《墨子·經(jīng)上》說:“法同則觀其同。”比如,統(tǒng)治者既然在宰殺牛羊這樣的小事情上都知道要尚賢,而管理國家和宰殺牛羊屬于同類而且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更應該知道尚賢。但統(tǒng)治者在管理國家大事上并不知道尚賢,由此說明統(tǒng)治者是“知小不知大”“明小不明大”“不知類”。墨子在《公輸》中曾經(jīng)嚴厲地批評公輸般一邊主張“吾義固不殺人”(講仁義不殺一個人),但同時又為楚國制造云梯以攻打宋國,指出這種“義不殺少而殺眾”(講仁義不殺一個人但事實上卻在從事著殺許多人的勾當)的做法是“不可謂知類”(不可以說是會類比的人)。墨子在《非攻下》中多次批評論敵“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也”,指出對方?jīng)]有能夠認識到他所說話的類別不同,也不清楚他所說話的理由或者原因。墨子所批評的對象,從邏輯上看就是自相矛盾,統(tǒng)治者缺乏理性思考。墨家認為,反駁應該根據(jù)“類”的原則來進行,理由在于“同類”可以相推。《墨子·經(jīng)下》說:“止,類以行人(之),說在同。”
《墨子·經(jīng)說下》說:“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對方通過指出這一類事物情況都是這樣,必然性地推導出某一個具體事物情況是這樣,這時我方就可以通過指出這一類事物情況不是這樣,從而懷疑對方的結論。
墨子經(jīng)常應用矛盾律和反證法來進行論證,揭露對方思維中存在的矛盾。《墨子·貴義》說,墨子曾經(jīng)從魯國出發(fā)到齊國去,在路上碰到一個日者即算命先生告訴他,“今天上帝在北方殺黑龍,您長得黑,所以您如果到北方去不吉利”。墨子根本不聽算命先生的警告,繼續(xù)向北走,結果遇到了河水暴漲,于是只好返回來,這時算命先生見他后非常得意地說:“您看,不信我的話吧,我說過先生不能往北方去的嘛。”墨子對此反駁說:“南方人不能往北方,北方人不能往南方,人的臉色有黑色有白色,為什么都不能前往呢?況且上帝在甲乙日殺青龍于東方,在丙丁日殺赤龍于南方,庚辛日殺白龍于西方,壬癸日殺黑龍于北方。如果都按照你的說法,那整個天下的人都不能走路了。你這完全是在束縛人的思想而使得天下虛無人跡,你的話是不能聽的啊!”墨子在這里運用歸謬法對命定論進行了徹底的駁斥,充分肯定了理性和邏輯思考的重要作用[5]。
如果屬于異類的事物對象,則不能根據(jù)同法的原則來推理。《墨子·經(jīng)上》說:“法異則觀其宜。”比如,《墨子·經(jīng)說下》說:“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虭與瑟孰瑟?”木頭與夜晚哪一個更長?木頭的長短和夜晚的長短怎么能比較?智慧與糧食哪一個更多?爵位、親屬、價格、品行其中哪一個更高貴怎么能比較?在地上奔跑的動物如麋鹿和在天上飛行的動物如鶴,哪一個更高,怎么比較?蚯蚓的叫聲與琴瑟的和聲,哪一個的聲音更好聽?再比如自然之美和人為之美,哪一個更美?這個很難說。所以,《墨子·經(jīng)下》說:“異類不比,說在量。”量度上不同的事物之間就不能進行推論。所以,如果非要在不可比的事物之間進行比較,就會出現(xiàn)錯誤。異類的事物通常所立法異,則需要根據(jù)不同的邏輯來進行思考。《墨子·經(jīng)說上》:“法異則觀其宜。”根據(jù)實際具體情況來考慮推論的方式。
四、結語
墨家邏輯中“故”“理”“類”三個范疇概念,是墨家思想中的求故思維、立法思維和明類思維的基本總結。墨家邏輯對后世的影響,雖然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得到重視和發(fā)展,但卻是沿著這三種思維方式和方法來進行的。比如,荀子就非常重視墨家的“故”和“法”,強調(diào)思想論證中必須“辭之有故”,必須“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孟子則發(fā)展了墨家的明類思維,強調(diào)通過列舉同類事例來進行推論。如果從墨家的求故思維、立法思維和明類思維出發(fā),開展更深入的分析,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墨家的思想中也蘊含著辯證思維、歷史思維和創(chuàng)新思維等多種思維方式。就辯證思維來說,關于類同類異原則的“同”,《墨子·經(jīng)說上》說:“同,異而俱于之一也。”“同”是不同事物共同具有的方面,“同”是異中之同,其中包含“異中見同”的思維方法。同樣,墨家也強調(diào)“同中見異”的思維方法。再說歷史思維,墨家在思想論證中十分重視歷史思維,墨子“三表”法中的第一表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強調(diào)從正反對比的歷史的觀點來看問題,墨子在關于其核心思想的論證中,經(jīng)常運用歷史思維。墨家也特別強調(diào)思維創(chuàng)新,反對儒家的君子必須說古代人的話穿古代人的衣服等錯誤觀點,強調(diào)思維實踐和實際,因為對古代人來說創(chuàng)新是必然的。總之,墨家邏輯建立于科學思維方法的基礎之上,同時又反過來為科學思維服務,在墨家的思想里,正好體現(xiàn)了邏輯和思維的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