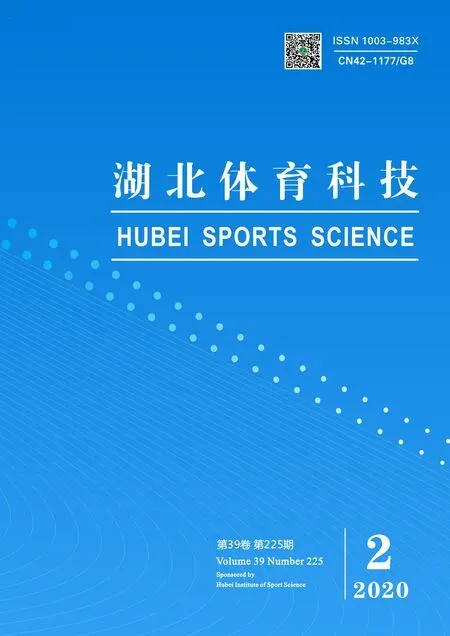文化模式視域下武術文化的建構與整合
冉海波
(成都體育學院 研究生院,四川 成都 610041)
社會中所存在的每一種族群落,大多具有與之相適應的且為之群體人員共同尊崇的民族特性,這種由其社會成員共同遵守和認同的規則或制度,便是這一民族的意志在適用范疇內凝練的具體文化模式。民族團體并非完全等同于由血緣關系鏈接而成的家庭模式,要形成能夠長久繁衍的群落,往往需要多個不具備同系族源的家庭共同構建。誠然,促使其磨合并最終熔為一體的因素不勝枚舉,或是擁有共同的行為習性,或是具備相似的準則觀念,亦或是具有相同的價值追求。但不可否認的是身處這一社會結構中的個體自誕生便接受著族群中特有文化模式的規訓,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當一種文化群體中的人漸漸長大,參與到文化活動中時,群體的習慣便成為他的習慣,群體的信仰也會成為他的信仰,群體的約束也會成為他的約束。”[1]繼而通過文化模式的理論建構起了人類群族行為與群族文化之間的聯系,也闡釋了民族群體文化形成的社會學原理。
武術本是中華民族的身體行為方式之一,在歷史的流變中卻逐漸演進成為了民族標識性的身份符號,被整合到傳統文化范疇之中。這其中的曲坎坷折,我們往往會通過史實的原因,或武術功能地位演變的維度進行探究與詮釋,然而對于部分行為特異性的武術文化現象,傳統的解釋似乎有捉襟見肘之處。因而亟需尋求一種新的文化角度,對武術文化的建構加以補充,于是,以群族構成的文化模式視域為研究視角,似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傳統武術文化予以更為恰當的闡釋。
1 溯源與探驪:文化模式概念的源起
基于工業革命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以帕森斯、莫頓等社會學家為代表的機構功能主義主張,從社會各子系統和社會角色入手,利用實證的方法尋求出有效的解決途徑,他們所探討的文化結構之間的有機整體性風靡一時。然則,由于在實證的過程中過于注重對社會角色的靜態分析,固守其客觀性,進而導致了對人類主觀能動性的忽視,認為任何文化中人的本性與欲望都是一樣的,最終隨著二戰的持續,結構功能主義的弊端日益顯現。露絲·本尼迪克特在對人類學和社會學深入研究后,開始意識到結構功能主義觀點的缺陷,“從而立意探索文化的深層結構與價值觀念,把文化的制度和習俗當作人們主觀態度的表現來看待。”[2]通過對祖尼人、烏塔姆人、科奇蒂人等群族的實地調查,提出了自己關于社會學中文化的見解,并于1934年出版《文化模式》一書,“在此書出版以后,文化模式理論自成一派,而本尼迪克特也被認為是文化模式理論的創始人。 ”[3]
本尼迪克特以文化模式的結合形式對人類的各種行為方式加以詮釋,“指出在任一社會中,人類可能產生的行為范疇,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或受到重視。從而表示贊成文化相對論,贊成根據文化發生的來龍去脈來評價文化現象。”[4]文化模式中主要凸顯了本尼迪克特對于人類文化研究的三重理論,一是文化的心理學類型思想,以某種心理主導的人各類型闡釋某一族群的文化形式,以及不同文化模式之間的差異性。再則是文化整合論思想,在民族文化發展的進程之中,以族群的共同意志主導某系文化元素并逐步制度化,繼而形成文化的整體性。此外還有文化相對主義,認為每一種文化模式皆是由民族特點盤合而來,不同文化模式有著或多或少的差異性,但彼此之間并無高低有了之分。文化模式理論的提出,承認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又為不同民族文化的建構模式提供了一種可溯之源,進而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探析族群文化的產生緣由,也為當前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工程建構了一種可行的措施。
2 文化與人格:心理學構圖的武術傳統
人類與生俱來便存有好動的心理,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不同方域內的人群通常會選擇一種較為適宜的方式來滿足身體運動的需要。而同一族群往往又會因趨同心理因素,對同一種運動行為產生興趣,于是就形成了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間傳統體育運動。武術傳統中的每一個體對其所屬文化均有獨到的認同歸宿感,而“認同是與意識相關的,即它與對一個無意識的自我認知所進行的反思相關。”[5]由此,似乎能較容易理解中華武術的產生與華夏民族獨特的心理活動息息相關。
2.1 人格類型差異性催生多元武術
武術文化所體現出來的文化模式具有鮮明的民族特性,是中華民族人格特質在身體行為上的具體呈現,文化模式似乎可以通過某種人格的心理特征來構畫某種文化存在的理想形式。本尼迪克特提出“一種文化就如一個人,是一種或多或少一貫的思想和行為的模式。”[6]其文化模式是由或多或少與之相關聯的文化叢,在一定的范疇內經過有序排列整合而來的整體形式。在傳統武術構建之初,文化叢因子頗為豐富,且每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叢又隱含著較多的文化元素,因而對傳統武術文化的形成產生了較多影響。拋去器物層次文化和符號元素所形成的實質性的影響外,還有一個較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個體心理因素,也即是通常所說的人格因素。習武者是武術的衍生與傳承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影響因子,而武者的社會心理活動則更多的表現在其身體行為之上,進而凸顯為人格之間的差異。武術文化模式中人格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個體與群體2個方面,其中個體是其模式形成的文化元素,而群體則是相關的文化叢。個體人格對于武術文化的作用主要是由武術拳種流派中突出的精英人物來完成,如某一武術的創始人或后世集大成者,這一類武術家的心理活動與思想的頓悟往往會對本門武學的發展趨向產生引導作用。精英武術家的行為以及思想逐漸形成武術中的小傳統,“這種‘小傳統’所體現的是個人對武術的價值的感知認識,或者說是習武者理解練習武術對自身個體的作用的一種方式。”[7]從弗洛伊德代表的精神分析派看,武術家人格的特征則會以精神意志的形式留存于武術文化之中,具體表現則為宗族門派的門規,或祖訓,亦或師訓。群體人格的差異性構成了武術文化模式中的文化叢,每一群體都具有特殊的人格特征,這是由其生活的環境及習俗的共同作用導致的。群體為追求本族群利益的同時,由于價值觀念的趨同性逐漸產生了約定俗成的傳統意識,這種意識往往會基于對自身存在以及民族發展乃至社會進步的考量,對自身武術技法與文化采取保守態勢,也由此催生了中華武術文化的多樣性。
2.2 民族心理聚合性演化同一特性
中華民族是由多個原始群族經過長時間磨合而最終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體,這得益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衍生于民族實踐之中的任一文化,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相互之間文化遷移的影響。武術文化模式在各種文化的交流與切磋中得以定型,發展至今儼然已具有共同點文化特性,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的特殊心理行為,以東方哲學形式指導著每一個武術個體的行為與習性。武術作為民族一個具有獨特標識性的身體文化符號,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指導著族群的社會行為,由此所建構的傳統體育文化模式如今已然“是一個民族、社會、國家文化模式的具體層面之一,是構成體育實踐活動最為深層的思想文化基礎、對體育實踐活動具有主導影響的、決定體育實踐活動指向的一種文化形態。”[8]文化模式語境中,文化被認為是某一特定范圍內的人格,彰顯在典章上的擴大化,而武術文化正好對應的是中華民族,這與本族群的人格類型特征不無關系。
民族的人格心理特征與社會所處發展階段有著緊密聯系,不同時段的社會形態對于當時的社會成員心理會形成一定的聚合力,以至民族心理特征表現出較強的統一性。阿爾伯特·謝夫勒在《社會的構造與生命》一書中“將社會心理社會形態與社會生理并列,用以解釋社會性質。”[9]中華武術的演變經歷了多個社會性質的變革,而習武者個體本身均具有不同的社會屬性,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性,亦是武者有異于普通大眾的特點。習武群體所共有的人格性質驅使其相互之間結合成社會關系上的共同體,使之生活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構成相應的武術文化模式,以求在其關系模式的庇佑下,發揮自身武術技法的價值作用,以及提升其文化影響力。在習武界的“武林”與“江湖”之中,不同武術門派多以求同存異的心境,參與武術的交流與切磋,由此武術文化模式表現出較強的聚合力,通過民族心理特性的趨同性建構起中華武術文化體系。
3 程式與記憶:整合論建構的武術文化
民族文化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高度凝練,對于常規的普通文化具有較強的導向作用,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族群特定的行為要素,甚至可能抑制或排斥外來因素的影響,對限制域內成員的行動起到協調作用,表現出文化模式的整合功能,“文化整合,就是指構成文化的諸文化要素、子系統與層次之間相互適應相互綜合變為整體或完全的過程。”[10]文化模式視閾下,武術文化的建構就是通過整合不同方域中的地域武術,協調他們之間成員的社會行動而形成的。
3.1 武術統一性調和社會成員行為
中華民族是一個較具自律性的民族,傳統文化中以儒家為代表的規范思想,千百年來一直約束著人們的社會行為活動,“與其他文化模式截然不同,中國傳統文化模式屬于道德主導型的文化模式。”[11]在這種文化體系的引導下,武術文化也隨之引申了其中了內涵蘊意,逐漸內化為其存在的群族意志,并加以改進形成自己的管理體制。在武術組織形式上采用宗族體系,每一個體均有其所屬部門,受到相應族制門規的管束,以師承關系模擬宗族的血緣建制,從而建構起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網絡。在管理形式上形成師門文化,制定相應的道德規范要求,門內習武成員的社會行為受到族訓的教導,承擔著各自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在傳統武術文化中,武德占據著武者意識形態領域的支配權力,個體行為中的長幼尊卑與綱常倫理是不容觸犯的。對于武者種種行為的管束體制,統一和調和了習武者的社會行為,如此層層包裹,最終武者個體或門派在一定范圍之內達成了共識,建構起武術體系中的文化模式。
誠然,武術文化模式的整合功能是將原本零散的各種民間武術以特定的結構模式進行匯總,進而加以規范社會成員之間的行為活動,但這種形式上的統一性并非純粹的耦合,因為“社會群體中不同成員都是獨特的行動者,他們基于自己的需要、根據對情境的判斷和理解采取自己的行動。”[12]習武群體行動的價值意義在滿足自身行動的程度上,還會在更高的高度上謀求與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的共識與合作,在每一次民族危亡之際,習武者成員的意識與行動都會形成高度的統一。春秋戰國時期,百家興起,習武之人便成為縱橫聯合之術中的重要媒介,當家國同構思想在習武群體中主導民族意志時,武術文化中所傳遞的民族價值觀念,更是成為了統一社會行動的指向標志。明朝時,全國武者為抗拒倭患,匯聚于東南沿海,到清末民國時期,又以武者的民族意識結社成大大小小的武術團體,為強國保種而反抗外族入侵,可以看到武術文化以及武者的價值高度。盡管,由于不同武術門派在傳統文化的陶染下,具有較大的保守性和封閉性,甚至存有內斗性,但是在民族認同的高度上,武術文化往往能夠起到協調社會成員的具體行動,以此表現出文化模式對民族行動的整合作用。
3.2 武術普適性盤合民族內部文化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人類文化模式過程中認為每一種人類文化的產生與形成,都會有一項驅動因素和主導動機。武術文化中講究中庸之道與陰陽互換理論,追求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境界,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習武主導動機,并依據這一動機選擇與之有利的行為要素,繼而抑制其它干擾因素的產生。而這些合乎習武者價值追求的行為或方法,被最終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來,成為了某種由特定形式架構在一起的文化符號體系。盡然“武術文化是一種民族性和地域性特點很強的文化”[13],但都統屬于中華文化之中,從族群發展的角度論究,武術文化的整合則是以社會整體為考慮對象,盤合各種武術的共通之處,從而形成具有較大包容性的文化模式。由于武術文化多是取材于傳統的大眾文化之中,因而具有較大的普適性,同時武術文化又對民族文化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在此環境下誕生的個體首先便是適應群眾中世世代代流傳而來的生活模式,而武術文化也在無形中塑造了其成員的經驗與行為。武術文化模式的形成整合了局部地域武術的小傳統文化形式,通過整合協調社會中的習武群體的情感與動機,使之在民族的意志下構建出統一的文化價值目標,同時也超過了個體武術文化特質的總和。
武術文化的整合是以有機的文化觀念進行組合的,泰勒曾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指出“文化或文明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習慣。”[14]武術文化即為古代華夏民族所共同特有的一種行為習慣,無論是巫術起源說,還是宗教起源說,亦或其它起源說法,無一例外的都與民族的風俗習性相關聯。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提出文化產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某種社會欲求,并將這種欲求分為“生物欲求、作為手段的欲求和整合的欲求”[15]。文化模式語境中的武術文化幾乎涵蓋了這3種基本類型,而其中整合的欲求則表現在,習武群體極力尋求一種能夠被共同認可的文化結構,并以此構畫出價值觀與世界觀上的共同特點,進而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武術文化通過傳統武術這一身體技法的普適性,建構起了武者雙方在基本價值觀念上的共識,實現了對民族文化的整合,成為了群族之間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并對今天習武群體的社會行動產生著深遠影響。
4 結語
武術文化模式是由諸多行為個體因子在一定時段內所共同表現出來的文化特性,不同的宗族門派通過文化的整合功能,進行有條理的排序,在一定層面上表現出共有的模式類型,進而在一個較大的民族共同體內發揮著更大的功能作用,成為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一束頗具影響力的文化叢。當前武術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已然受到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與之相關的研究亦是與日俱增,在此環境下分析其建構模式,或許可以從其細微的組成元素上尋覓到較為適宜的保護措施。武術作為東方民族獨具魅力的身體行為方式,是中華民族對于社會特有的認知方式,因而從每一個習武族群的生活形態角度,剖析武術文化模式在不同時空下構成元素的變化,以及影響因子的異動,或許能夠使我們更好的理解當前武術變化的緣由。從文化模式視域理解文化功能的意義,繼而探尋新時代文化模式對武術文化的導向作用,對武術文化加以合乎時代特征的改進,引入時代文化元素,并借以文化的傳續功能,構建新的武術文化模式以及傳承模式,存續華夏先祖的知識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