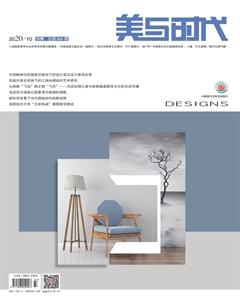實踐價值論視角下的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研究


摘? 要:江南先民留下的絲綢染織藝術是我國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不應僅僅將其作為一門傳統技藝看待,更應當將其藝術特征與當代創作需求緊密結合。在多元化的社會文化實踐中,江南絲綢逐漸具備了雅俗共賞的藝術價值。其當代價值主要體現為師從造化的創作理念,運用視覺符號合理表現人們美好生活愿景的創作方法,以及工匠精神的物化詮釋。
關鍵詞:絲綢;染織藝術;江南;當代價值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社科應用研究精品工程“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數字化傳承研究”(17SYC-101)階段性成果。
自古絲綢之路開辟至今,絲綢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符號代表。中國蠶桑絲織技藝于2009年9月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其重要的文化價值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認同。江南絲綢具有悠久的歷史。南宋以后,江南地區的紡織業逐步得到發展。明清時期,江南絲織業已譽滿全國。如今,江南地區的杭羅、云錦、宋錦、緙絲、甌繡、蘇繡已成為中國蠶桑絲織技藝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江南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珍貴的藝術價值。該領域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國傳統文化體系的梳理,還可以通過借鑒先民的意匠智慧,推動我國當代藝術創作和藝術教育實踐的發展。
為了深入地分析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價值,本文以實踐價值論為理論基礎進行研究。實踐價值論的主要思想包含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實踐是價值的起點,也是價值動態生成的過程[1];其二,實踐并不只是個體勞動,還包括了社會系統性行為[2];其三,價值不是純粹的客體屬性,還是主體的主觀臆想。在人類的實踐過程中,當客體的特征可以滿足主體的需求時,價值便產生了[3]。運用上述理論可以系統性地揭示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價值形成、價值特征和當代價值。
一、經濟因素和技術創新對藝術價值形成的推動
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價值創造的源泉。江南絲綢染織藝術價值的產生也來源于人們多維度的社會實踐。在這些社會實踐中,經濟與技術是影響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它們對于江南絲綢染織藝術價值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經濟因素:貿易為藝術價值的提升注入了動力
在化纖技術市場化之前,絲綢是我國重要的貿易出口商品。在宋代,我國絲綢便已銷往朝鮮、日本和南洋諸國。現在,日本還保存著道元緞子和大燈金瀾,這些都是南宋時期的絲織品[4]52。明清時期,江南絲綢的經濟價值突顯,成為國家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貿易為國家創造了豐厚的經濟收益,同時也促進了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發展。這是因為不同地域的貴族和富裕階層對于絲綢的品種、色彩、圖案等有著不同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需求還在發生著變化。康熙四十年,哈薩克等族對絲綢的需求新增了官綠、深玉、藕色等色彩;在嘉慶初年,又新增了玫瑰紫、蔥心綠等色彩[4]324。正是這些源自貿易的需求,促使江南先民們不斷通過實踐豐富絲綢的色彩及圖案,最終形成了藝術創新和發展。可以說,我國的絲綢貿易不僅帶來了江南地區的經濟繁榮,也推動了絲綢染織藝術價值的不斷提升。
(二)技術創新:循環再利用的造物方式提高了創作效率和藝術的豐富性
江南絲綢染織藝術并不是完全通過純手工工藝完成的,江南地域的先民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改進工藝,提高生產效率。循環再利用的造物思想便是工藝上的重要創新。具體體現為江南絲綢染織工藝中“花本”的制作和實踐應用。“花本”的實質是用線事先存儲好編織的程序,猶如在計算機程序中給一組數據賦值,然后再根據這組數據的內容進行生產。與計算機程序相比,其不同點在于預先制作程序的過程需要更加精細入微的把握。若有細小的偏差,則可能對其后的生產造成明顯的影響。因此,制作“花本”通常需要花費較高的時間成本。一旦成功地制作出“花本”,便可以反復利用。從長遠來看,節約了制作時間和人力成本。在“花本”制作工藝的應用過程中,藝術創作的精密性得到了提高,藝術作品顯得更為細膩且精致。隨著“花本”工藝與織機技術的共同變革,大花樓“花本”的上機工藝是允許自由更換“花本”的,而不是織完一個固定的圖案循環后才可更換“花本”。這使得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豐富性得到了提高。
二、文化實踐對藝術價值特征產生的影響
創造價值的行為并不局限于個體勞動,還包含社會性的實踐行為。這種社會性的實踐行為不僅包含造物實踐,還包含了文化實踐。江南先民的審美及文化實踐雖沒有直接作用于絲綢織物,卻通過理學思想和吉祥文化的傳播,對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價值特征產生了深刻影響。該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理學思想:“格物”精神推動寫實特征的形成
江南絲綢染織藝術中蘊藏著樸實而生動的寫實表現手法,這與當時理學思想的文化實踐有著緊密的聯系。宋代理學奠基人程顥、程頤將“格物”精神理解為“格物致知”。這種關于“格物”精神的文化實踐首先影響到宋代的繪畫,形成了宋代繪畫寫實和嚴謹的風格[5]。隨著南宋文人及畫家的南遷,這種藝術風格逐漸影響到了江南染織藝術。很多江南染織藝術作品就是根據自然的田園風景或花鳥形態進行寫實創作而成的。如蘇州絲綢博物館館藏精品《緙絲人物》(如圖1),其作品并沒有刻意追求富麗、華貴,而是在畫面主體采用了較為寫實的表現手法,體現了樸素而溫馨的生活場景。再如江蘇金壇周禹墓出土的絲綢文物,其枝葉走勢生動,花卉形態自然,體現了創作者對于生活細致的觀察和潛心的吸收。
(二)吉祥文化:象征著美好生活的吉祥紋飾
中國吉祥文化的審美內驅力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6]。江南先民們同樣期待著幸福、美滿的生活,這樣的文化思維推動了吉祥文化的社會實踐,最終形成了一套吉祥紋樣的審美和造物體系。在江南絲綢染織藝術中,主要使用的吉祥紋樣有兩大類。1.來自神話傳說的神物寶器。如八吉祥紋樣等,明清江南絲綢中的麒麟也屬于這種類型的吉祥紋樣,該紋樣具有“送子”的寓意,有著仁愛的內涵。江南絲綢染織藝術充分而大膽地利用這些較為成熟的文化符號,向受眾人群傳達著吉祥康樂的信息,使人們能夠在生活中較為快捷地感受到豐富而美好的心理撫慰;2.具有諧音象征的吉祥紋樣。如妝化織物“吉慶雙魚”,其主體為較為寫實的魚型,同時巧妙地運用了磬作為裝飾,取其諧音“慶”,魚的背景采用了盤長結,取其諧音“吉”。上述兩種吉祥紋樣的共同特點是在當時社會中的符號指向性較為鮮明,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階層所理解和廣泛接受。
在多元化的社會文化實踐中,江南絲綢染織藝術最終兼具理學思想的寫實性和吉祥文化的象征性。二者細膩、有機的結合,形成了江南絲綢雅俗共賞的藝術特征。
三、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當代價值
客體的內涵及特征只是形成價值的條件之一。只有當主體需要這些內涵和特征時,價值才會產生。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當代價值是其藝術特征與當代需求的契合。具體而言,其當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于自然元素的深入體驗與生動表達
在當代設計藝術中,往往忽視了對于自然的體驗和表達。一方面,國際主義設計風格對于我國當代設計產生了一定影響。尤其是在工業設計和數字媒體設計領域中,很多作品的裝飾性設計語言幾乎被完全抹去,使其逐漸喪失了多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在染織設計、服裝設計和包裝設計等領域,裝飾性元素雖然基本被保留,但隨著設計產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縮短設計時間,裝飾性元素的取材并非來自生活或自然,而是通過互聯網搜索的資料。這些資料往往只是客觀世界的一個數字化切片。與通過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去全面地感受自然產生的多維度體驗相比,網絡資料給創作者帶來的審美體驗顯得過于單一化。在這些單一而片面體驗的基礎上形成的設計作品,其蘊藏的藝術感染力自然也會較小。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創作素材大多來源于日常生活中能夠見到的自然景物,如牡丹、菊花、芙蓉、玉蘭花、茶花、翠竹、松樹、梅花等植物元素,以及鴛鴦、鯉魚、飛雁、蝴蝶等動物元素。這些創作素材客觀存在于江南地域,創作者可以深入而全面地進行審美體驗。正因如此,江南絲綢染織藝術中自然元素往往被表現得栩栩如生(如圖2)。生動的自然造型與細膩的織、繡等工藝有機結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作品。這正是當代藝術設計領域需要重視并吸收的創作理念。
(二)表現當下民眾美好生活愿景的藝術符號
如今在高校和政府的文化部門中,已經重視傳統藝術的當代活化工作。基于傳統藝術的當代設計實踐成果較為豐富。然而,依然存在著忽視審美主體的創作誤區。僅僅因為某種藝術形式或形態具有悠久的歷史,便將其造型與現代技術進行生硬的嫁接,而不是深入思考該藝術盛行時期,其藝術特征與當時民眾需求的關系。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設計資源除自然景物以外,還有一部分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藝術符號。如麒麟、辟邪、夔龍、鸞鳳以及象征著吉祥的“八寶”和“八吉祥”等圖案。這些傳統文化元素符號已經為中國百姓所熟知,并且有著較為吉祥的寓意。使用這些符號進行設計的作品契合了當時百姓的美好生活意愿,所以得到民眾的廣泛接受和喜愛。當代設計藝術可以吸取并發揚這樣的創作方式,積極提煉當下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愿景,并結合我國傳統文化將其概括為恰當的藝術符號。此外,江南絲綢藝術中的吉祥符號往往并不是孤立呈現的,而是與其他類型的裝飾紋樣有機融合在一起。如江蘇蘇州曹氏墓出土的《鳳穿牡丹紋花絹裙》(如圖3),該作品在傳統吉祥符號——鳳的周圍配以纏枝花卉造型,且鳳與花卉的比例控制合理,使吉祥寓意之中平添了勃勃生機。當代設計藝術在運用文化符號時也可以采用符號與自然圖形和生活畫面相結合的方式,從而使其形式更為完善,內涵更加豐富。
(三)工匠精神的物化詮釋
工匠精神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工匠精神是當代社會各行各業都應繼承和發揚的文化品質和造物態度。在藝術設計領域,人們也應當努力挖掘和繼承先人的工匠精神,并基于工匠精神凝練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創作理念。江南絲綢染織藝術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蘇繡、緙絲等工藝往往需要學習十余年甚至數十年才可能創作出精品。在作品的意匠和制作過程中,需要高度的專注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在經線和緯線的使用中,稍有偏差,便可能導致整件作品的失敗。可以說工匠精神貫穿了江南絲綢染織藝術學習和創作的始終。不僅如此,如今傳世的江南絲綢染織藝術作品還體現了巧妙的構思、細膩的做工和精湛的技藝,這些都是江南先民工匠精神的物化詮釋。與語言的教化相比,工匠精神的這種物化詮釋更直觀且深刻地被人們接受。當代藝術設計可以重視并運用這一設計效應,積極創作并推廣體現當代工匠精神的設計作品,使受眾在欣賞藝術設計作品的同時,理解并認同具有工匠精神的造物理念。
四、結語
綜上所述,以實踐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系統性地從經濟、技術和文化維度對江南絲綢染織藝術進行剖析,可以發現:其藝術價值的形成受益于實踐過程中的貿易推動,其循環再利用的造物理念不僅至今仍值得提倡,并且提升了藝術的豐富性;理學思想及南宋文化中心的南遷促成了其寫實特征的形成。吉祥寓意的視覺展現是其能夠被民間廣泛接受的重要因素。
江南先民留下的絲綢染織藝術是我國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不應僅僅將其作為一門傳統技藝看待,更應當將其藝術特征與當代創作需求緊密結合。學習江南先民深入體驗自然與生活的創作過程,將“師從造化”運用到當代設計藝術實踐之中;學習運用視覺符號合理表達當代民眾的美好生活意愿;認知物化詮釋工匠精神的當代傳播作用,并積極將工匠精神運用到設計實踐之中,使江南絲綢染織藝術的文化內涵成為推動當代設計藝術發展的重要動力。
參考文獻:
[1]陳金美,付國輝.實踐價值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4):24-27.
[2]李鐵強.從勞動價值論到實踐價值論——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路徑[J].江漢論壇,2013(2):87-91.
[3]朱榮英.馬克思主義基本范疇及其學科體系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143.
[4]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M].北京:農業出版社, 1993.
[5]李碧紅.意象視域下的宋徽宗繪畫風格研究[J].藝術百家,2015(2):201-203.
[6]胡燕,嚴昊,朱志平.中國吉祥文化審美略論[J].學習與實踐,2016(12):121-127.
作者簡介:吳小勉,博士,蘇州科技大學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