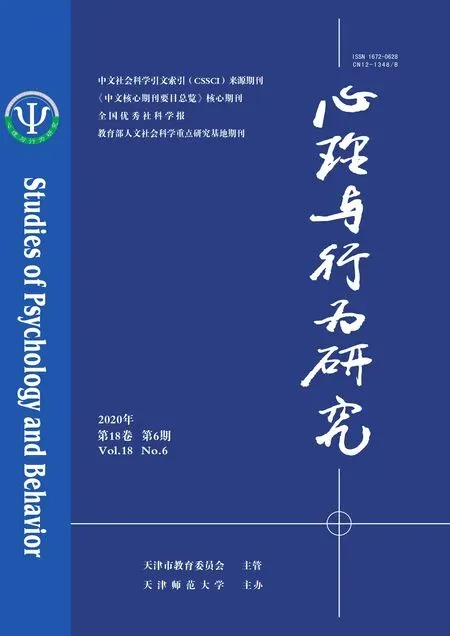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對震后青少年自殺意念的影響:安全感的調節(jié)作用 *
原 昊 王文超 伍新春 田雨馨 陳秋燕
(1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應用實驗心理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心理學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2 西南民族大學教育學與心理學學院,成都 610041)
1 問題提出
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地震、洪災或颶風等重大自然災難的幸存者最常見的消極心理反應之一。而地震后幸存的青少年由于其心智發(fā)展尚不成熟,自身的情緒調節(jié)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有限,往往缺乏足夠的經驗和應對策略來處理這一重大危機(Tang et al., 2018),因此是PTSD 的高發(fā)群體。例如,Hsu,Chong,Yang 和Yen(2002)對1999 年臺灣南投地震后幸存的321 名12~14 歲的初高中生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在地震發(fā)生6 周后這一群體PTSD癥狀的檢出率為21.3%;Tang 等人在雅安地震3年后對寶興、蘆山和天泉縣的6132 名中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發(fā)現,PTSD 癥狀的檢出率為9.9%;伍新春、王文超、周宵、陳秋燕和林崇德(2018)在汶川地震8.5 年后對災區(qū)2291 名青少年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表明,有4.75%的青少年出現了PTSD 癥狀。
相關研究表明,青少年的PTSD 癥狀會導致其產生自殺意念。自殺意念是指個體產生了殺死自己的想法或念頭,但并不會采取威脅自身生命安全的實質性行為(杜睿, 江光榮, 2015),而自殺意念同時也是個體實施自殺行為和完成自殺的有力預測因子(Klonsky, May, & Saffer, 2016)。Ying 等人(2015)在汶川地震1 年后對災區(qū)2298 名中學生開展的調查表明,中學生的PTSD 癥狀對自殺意念具有正向預測作用。Mazza(2000)調查了106名在郊區(qū)就讀的美國高中生,結果發(fā)現,在控制了性別、年齡以及抑郁癥狀后,這一群體的PTSD癥狀仍可以正向預測自殺意念。除了將PTSD 作為一個整體探討其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之外,也有很多研究者按照DSM-IV 的分類標準,將PTSD 分成侵入性癥狀、回避/情感麻木性癥狀以及警覺性增高癥狀三個不同的癥狀簇,分別考察各個癥狀簇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例如,Guerra 和Calhoun(2011)對393 名參加過戰(zhàn)爭的士兵進行了調查,結果發(fā)現,這一群體的PTSD 癥狀能顯著正向預測自殺意念,但在PTSD 的各個癥狀簇中,僅有情感麻木性癥狀對自殺的預測作用是顯著的。Bell 和Nye(2007)調查了50 名患有PTSD 的越戰(zhàn)老兵發(fā)現,僅有侵入性癥狀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而Briere,Godbout 和Dias(2015)對357 名有過創(chuàng)傷經歷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發(fā)現,僅有警覺性增高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是顯著的,侵入性癥狀以及回避/情感麻木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都不顯著。
以上研究表明,PTSD 的不同癥狀簇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不同。那么,為何PTSD 的同一癥狀簇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也會不同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這其中存在某些調節(jié)變量,而安全感可能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調節(jié)變量。安全感作為一種基本的心理需要,是個體對可能出現的危及自身心理和身體穩(wěn)態(tài)的危機事件的預感,包括人際安全感和確定控制感兩個維度(叢中, 安莉娟, 2004)。安全感較低的個體往往不信任他人,常常會感到自己不被接納,容易產生焦慮情緒,表現出神經質傾向;而安全感較高的個體對自身則更加接納,同時也更加信任他人,能夠體驗到更多歸屬感和控制感,不會認為自己是他人的累贅(吳茜玲, 羅嬌, 白紀云, 侯木蘭, 李霞, 2019)。而歸屬感受挫和累贅感恰恰是個體產生自殺意念的重要原因:歸屬感受挫主要表現為孤獨感,即缺乏同外界的積極聯系;累贅感主要表現為不勝任感和無能感,認為自己缺乏對外界的控制(Joiner, 2005)。而震后安全感水平較高的青少年,通常能夠與他人維持穩(wěn)定的、積極的親密關系,較少體驗到被世界孤立和拋棄的感覺,同時也較少體驗到無能感和不勝任感(吳茜玲等, 2019),這可能會緩沖PTSD對自殺意念的消極影響。而安全感較低的青少年在面對地震帶來的巨大創(chuàng)傷時,往往認為自己不值得被無條件接納,易陷入被拋棄的感覺中,進而產生強烈的孤獨感;同時這部分青少年在面對自己無法掌控的創(chuàng)傷事件時,更可能喪失對生活基本的確定感和控制感,從而加劇PTSD 對自殺意念的消極影響。
因此,本研究擬將安全感作為調節(jié)變量,考察其在PTSD 及各個癥狀簇對自殺意念影響過程中的調節(jié)作用。一方面,以往研究大都是以經歷過人為創(chuàng)傷事件的成年人為被試。與人為創(chuàng)傷相比,自然災難具有突發(fā)性、破壞性強和影響范圍廣等特點。而青少年群體由于自身的心智發(fā)展并不成熟,更容易在自然災難后產生PTSD 和自殺意念等消極心理反應(Tang et al., 2018);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大都是按照DSM-IV 的標準將PTSD 分為侵入性癥狀、回避/情感麻木性癥狀、警覺性增高癥狀三個癥狀簇探討其對自殺意念的影響(Bell &Nye, 2007; Briere et al., 2015; Guerra & Calhoun,2011)。但在最新的DSM-5 中,PTSD 又新增了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這一癥狀簇是否會對震后青少年的自殺意念產生影響,安全感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為解答這一問題,本研究以汶川地震8.5 年后的在校初高中生為被試。考慮到震后青少年的年齡、性別、抑郁癥狀和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往往是自殺意念的有力預測因子(Mazza, 2000;Ying et al., 2015),因此在控制了上述變量后,采用DSM-5 的分類標準探討PTSD 及其各個癥狀簇對震后青少年自殺意念的影響,并考察安全感在其中的調節(jié)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在汶川地震8.5 年后開展,調查了汶川縣和都江堰市的1136 名學生。其中男生511 名(45.0%),女生621 名(54.7%),4 名被試未報告性別(0.3%);年齡范圍在10~19 歲之間,平均年齡14.76 歲(SD=1.51 歲),8 名被試未報告年齡。
2.2 研究工具
2.2.1 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問卷
選取伍新春、張宇迪、林崇德和臧偉偉(2013)修訂自Wu,Hung 和Chen(2002)編制的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問卷,測查被試的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包括自己是否被困、目睹或事后得知親友被困/受傷/死亡三個部分,無此情況記1 分,事后得知計2分,親眼目睹計3 分,共18 道題目。所有項目得分相加即為被試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的總分,總分越高代表其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7。
2.2.2 流調中心抑郁量表兒童版
采用William,Chung 和Ho(2010)修訂的,Fendrich,Weissman 和Warner(1990)編制的流調中心抑郁量表兒童版(CES-DC),從情緒、認知和行為三個方面測查青少年過去一周內的抑郁程度。該量表包含20 道題目,采用0~3 的4 點計分方式,0 表示“沒有”,3 表示“總是”,得分越高表明其抑郁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9。
2.2.3 DSM-5 的PTSD 癥狀核查表
采用Zhou,Wu 和Zhen(2017)修訂的,Blevins,Weathers,Davis,Witte 和Domino(2015)編制的PTSD 癥狀核查表(PCL-5)測查被試的PTSD 癥狀水平。該量表按照DSM-5 的分類標準將PTSD 劃分為侵入性癥狀、回避性癥狀、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以及警覺性增高癥狀四個癥狀簇,在經歷了自然災難后的青少年群體中具有較高的信效度(Zhou et al., 2017)。量表共20 道題目,采用0~3 的4 點計分方式,0 表示“從未”,3 表示“總是”,得分越高表示其PTSD 癥狀水平越嚴重。該量表總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侵入性癥狀、回避性癥狀、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警覺性增高癥狀的Cronbach’ s α 系數分別為0.73、0.50、0.74、0.77。
2.2.4 安全感量表
使用叢中和安莉娟(2004)編制的安全感量表測量汶川震后青少年的安全感狀況。該量表共16 道題目,包括人際安全感和確定控制感兩個維度,采用1~5 的5 點計分方式,1 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被試在該量表上的得分越高意味著其感受到的安全感越低。為了便于解釋數據結果,將該量表的所有題目反向計分后再進行統(tǒng)計分析。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
2.2.5 兒童行為問題核查表
以美國中學生危險行為量表為藍本(Brener,Collins, Kann, Warren, & Williams, 1995),同時結合災區(qū)的實際情況對這一量表進行了修訂,用于測查青少年的睡眠問題、攻擊行為、自殺意念、飲食行為等7 類問題行為,共19 道題目,要求被試按最近半年內的表現進行1~3 的3 級評分,1 表示“沒有”,3 表示“時常”。本研究選取自殺意念這個指標進行統(tǒng)計分析,包括3 道題目:“有自殺的念頭”、“為自殺做準備”和“計劃自殺”,其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
2.3 程序和數據處理
本研究得到了北京師范大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采用整群抽樣的方式,于2016 年11 月(地震8.5 年后)對汶川縣和都江堰市三所中學的青少年展開調查。研究者首先征得了當地教育局、學校校長、年級主任和學生本人的同意,然后與學生簽訂了知情同意書,最后由臨床與咨詢專業(yè)的研究生以相同的指導語統(tǒng)一施測。要求學生仔細閱讀指導語,并按照要求匿名填答。研究者共計發(fā)放問卷1204 份,回收有效問卷1136 份,采用SPSS17.0 和InterAction1.7 進行統(tǒng)計分析,在數據分析過程中采用回歸插補法對缺失數據進行處理。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Harman 單因素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共出現了19 個特征值大于1 的公共因子,且第一個公共因子的解釋率為23.52%,小于40%的臨界值,故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變量間的相關
首先依據DSM-5 中PTSD 癥狀的篩查標準(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計算得到在參與調查的1136 名學生中,PTSD 癥狀的檢出率為5.3%;自殺意念的檢出率為10.6%(總分大于3)。然后對所有變量進行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從表中可以看出,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與抑郁癥狀、PTSD 及其各個癥狀簇、自殺意念呈顯著正相關,與安全感呈顯著負相關;抑郁癥狀與PTSD 及其各個癥狀簇、自殺意念呈顯著正相關,與安全感呈顯著負相關。PTSD 及其各個癥狀簇與震后青少年的自殺意念呈顯著正相關,與其體驗到的安全感呈顯著負相關;安全感與自殺意念呈顯著負相關。

表1 各變量間的相關
3.3 安全感在PTSD 與自殺意念間的調節(jié)作用
采用分層逐步回歸法檢驗安全感在PTSD 及其各個癥狀簇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調節(jié)作用,具體步驟如下:第一步將性別、年齡、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和抑郁癥狀作為協(xié)變量放入第一層回歸方程;第二步將中心化后的自變量(PTSD 及其四個癥狀簇)與調節(jié)變量(安全感)放入第二層回歸方程;第三步將自變量與調節(jié)變量的乘積項放入第三層回歸方程。結果發(fā)現(見表2):侵入性癥狀(β=0.01,p>0.05)和回避性癥狀(β=-0.03,p>0.05)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β=0.19,p<0.001)、警覺性增高癥狀(β=0.13,p<0.001)以及PTSD 總分(β=0.13,p<0.001)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安全感對震后青少年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p<0.01);安全感與侵入性癥狀(β=-0.08,p<0.01)、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β=-0.21,p<0.001)、警覺性增高癥狀(β=-0.12,p<0.001)以及PTSD 總分(β=-0.16,p<0.001)的乘積項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與回避性癥狀的交互項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3,p>0.05)。

表2 安全感的調節(jié)作用
而后進一步采用簡單斜率檢驗(Preacher,Curran, & Bauer, 2006)對上述調節(jié)作用進行分析,結果見圖1、圖2、圖3 和圖4。由圖1 可知,在高安全感水平下(高于平均數一個標準差,以下同),侵入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t=-1.02,p>0.05);而在低安全感水平下(低于平均數水平一個標準差,以下同),侵入性癥狀顯著正向預測自殺意念(t=3.93,p<0.001)。由圖2 可知,在高安全感水平下,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t=1.68,p>0.05),在低安全感水平下,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顯著正向預測自殺意念(t=8.61,p<0.001)。由圖3 可知,在高安全感水平下,警覺性增高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t=0.40,p>0.05),在低安全感水平下,警覺性增高癥狀顯著正向預測自殺意念(t=10.75,p<0.001)。由圖4 可知,在高安全感水平下,PTSD 總分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t=0.87,p>0.05),在低安全感水平下,PTSD 總分顯著正向預測自殺意念(t=9.31,p<0.001)。

圖1 安全感在侵入性癥狀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調節(jié)作用

圖2 安全感在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調節(jié)作用

圖3 安全感在警覺性增高癥狀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調節(jié)作用

圖4 安全感在PTSD 總分與自殺意念之間的調節(jié)作用
4 討論
4.1 PTSD 對自殺意念的影響
本研究在控制了性別、年齡、創(chuàng)傷暴露程度和抑郁癥狀之后,發(fā)現汶川震后青少年的PTSD 癥狀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與Ying等人(2015)以及Mazza(2000)的研究結論一致。這表明震后青少年的PTSD 癥狀是導致其產生自殺意念的危險因素之一,關注震后青少年的PTSD 癥狀對于做好其心理健康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考察PTSD 的各個癥狀簇對自殺意念的影響時,發(fā)現侵入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這與Bell 和Nye(2007)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項研究開展于震后8.5 年,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災區(qū)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此時幸存的青少年能夠對闖入腦海的創(chuàng)傷相關線索做出合理的解釋,從而使得侵入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再顯著。同樣,回避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也不顯著,這與Davis,Witte 和Weathers(2014)的結論相一致。Davis 等認為,盡管DSM-IV 將情感麻木性癥狀和回避性癥狀歸類為一個癥狀簇,但測量回避性癥狀的2 道題目對自殺意念的正向預測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DSM-5 本質上就是將PTSD 由DSM-IV 中的3 因子結構轉變?yōu)榱? 因子結構,把回避/情感麻木性癥狀拆分成了回避性癥狀(2 道題目)與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Kilpatrick et al.,2013)。但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對震后幸存青少年的自殺意念則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與Guerra 和Calhoun(2011)的研究結論一致。與PTSD 的其他癥狀簇尤其是回避性癥狀相比,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對個體身心健康造成的破壞往往會更加嚴重,這一癥狀會導致震后青少年體驗到的社會支持減少以及人際關系網絡的破碎,進而導致其產生自殺意念。同時,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Briere et al., 2015),本研究同樣發(fā)現警覺性增高癥狀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警覺性增高癥狀主要表現為緊張焦躁和易怒、坐立不安、高度警覺以及睡眠問題,而焦躁不安和嚴重的靜坐不能同樣是導致個體產生自殺意念的危險因素(Hamilton & Opler, 1992)。
4.2 安全感的調節(jié)作用
對安全感的調節(jié)作用進行檢驗,發(fā)現在侵入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中,安全感發(fā)揮了顯著的調節(jié)作用:在低安全感水平下,侵入性癥狀能顯著正向預測自殺意念;而在高安全感水平下,侵入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則不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高安全感的青少年往往能體驗到更強的歸屬感和意義感,會主動與他人傾訴和表達闖入到主觀世界中的創(chuàng)傷線索,并且能夠主動學習和尋求創(chuàng)傷事件的意義(Leroy et al., 2012),這就緩沖了創(chuàng)傷事件對自殺意念的消極影響。而安全感較低的青少年在經歷創(chuàng)傷事件后可能會產生自己是沒有價值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等消極假設(Janoff-Bulman, 1989),這就會導致他們拒絕向他人尋求幫助,也就無法正確處理闖入到主觀世界的創(chuàng)傷線索,進而產生自殺的想法。但安全感在回避性癥狀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中沒有起到調節(jié)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個體的回避性癥狀反而可以作為其應對創(chuàng)傷事件的一種手段和策略。青少年在面對地震這一重大創(chuàng)傷事件時,回避相關線索有利于暫時避開地震帶來的巨大心理沖擊,緩解消極的身心反應(周宵, 伍新春, 袁曉嬌, 陳杰靈, 陳秋燕, 2015),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無論青少年的安全感水平如何,都不會產生自殺意念。
此外,安全感在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中發(fā)揮了調節(jié)作用:在高安全感水平下,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對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而在低安全感水平下,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對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是因為安全感水平較高的青少年往往會表現出較高的人際信任水平,對外界抱有更加積極的認知和情感,在人際交往中也能收獲更多的信任,在遭遇創(chuàng)傷事件時便不容易產生無助感,也就緩沖了創(chuàng)傷事件對自殺意念的消極影響;與此相對,安全感水平較低的青少年會認為外部世界是不可控的、他人是不值得信賴的,對自己的評價也更加消極悲觀(陳小萍, 安龍, 2019),在遭遇創(chuàng)傷事件時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痛苦感和無助感,為自殺意念的產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樣,安全感在警覺性增高癥狀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中也起到了相似的調節(jié)作用,這是因為高安全感的個體能夠更好地把控自身的情緒,在面對困難時也較少會陷入焦躁易怒的狀態(tài)(Snaith & Taylor, 1985);而安全感水平較低的個體則往往容易產生焦慮的情緒體驗,在遭遇到創(chuàng)傷事件時產生自殺意念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由此可見,PTSD 是導致震后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危險因子,且不同的癥狀簇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不同,同時安全感在其中所起到的調節(jié)作用也不同。這就提示災后心理援助工作者不僅要關注震后青少年的PTSD 綜合征,更應該從PTSD 的各個癥狀簇入手,采取有針對性的幫助措施降低PTSD 對自殺意念的消極影響。同時也要注重提高震后青少年感受到的安全感,給予其必要的支持和引導,以緩沖創(chuàng)傷事件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
5 結論
(1)從整體上看,PTSD 綜合征對震后青少年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是顯著的;具體到PTSD 各癥狀簇,僅有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以及警覺性增高癥狀能顯著預測震后青少年的自殺意念,侵入性癥狀和回避癥狀的預測作用都不顯著。(2)安全感在侵入性癥狀、負性認知和情緒改變癥狀、警覺性增高癥狀以及PTSD 與自殺意念之間起負向調節(jié)作用,在回避性癥狀與自殺意念之間不起調節(ji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