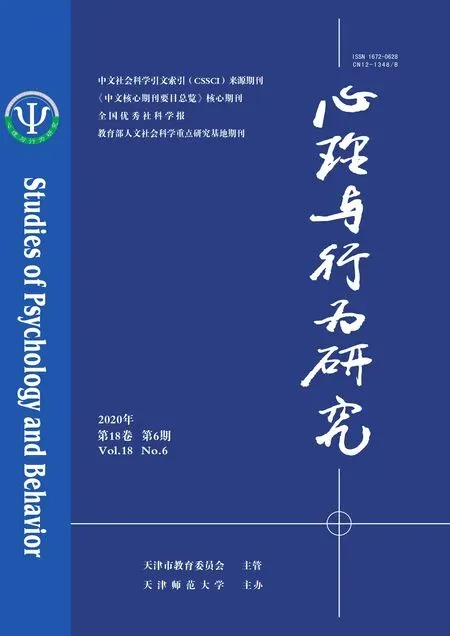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憤怒和報復動機的多重中介效應 *
呼軍艷 張慶霞 王海峰
(1 蘭州大學管理學院,蘭州 730000) (2 西北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管理學院,蘭州 730070)
1 引言
人際沖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指不同主體間由于在觀點、需求及價值觀等方面不兼容而引起的緊張狀態(Weingart, Behfar, Bendersky,Todorova, & Jehn, 2015)。組織內部員工之間的結構性、聯結性和互動性決定了人際沖突的不可避免,人際沖突也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存在(沈秉勳, 2009)。根據研究內容的差異,人際沖突被分為“任務沖突(或認知沖突)”、“關系沖突(或情感沖突)”和“過程沖突”三種類型(劉玉新, 張建衛, 彭凱平, 2012; Barki & Hartwick,2004)。任務沖突側重于工作任務,指員工在任務完成過程中關于工作時間、順序及流程等方面存在分歧或爭論;關系沖突側重于人際關系,指員工之間人際關系的不和睦或不協調;過程沖突聚焦于任務的推進方式,指員工在任務分配、責任承擔等方面存在分歧。
作為一種典型的壓力源(Eatough, 2010),人際沖突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人際沖突一方面凸顯甚至放大了個體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也極大降低了員工之間的協作效率。其不僅破壞團隊成員之間的互動關系,還會對團隊或組織績效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已有研究發現,人際沖突能夠激發員工的負面情緒(Bao, Zhu, Hu, & Cui,2016),減少信息共享(De Jong & Elfring, 2010),引起反生產工作行為(劉玉新等, 2012),而且會顯著降低組織的任務績效(De Wit, Greer, & Jehn,2012)。由于人際沖突的廣泛性與危害性,該問題正引起國內外學者越來越多的重視。
與一般類型的工作任務不同,安全工作具有獨特性。除了一般工作的特點(如正確的工作方式、規范的操作流程及嚴格的時間界限等),安全工作還包含較多的安全屬性,如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安全、企業正常運營的安全及他者的生命安全等(丁宗廣, 葉龍, 郭名, 2016; Beus & Taylor, 2018; Neal,Griffin, & Hart, 2000)。這就要求員工在工作過程中付諸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資源以保障安全工作的順利進行(岳俊林等, 2018; Beus & Taylor, 2018;Smith, Hughes, Dejoy, & Dyal, 2018)。所以,在人際沖突的情況下,員工能否嚴格遵守工作程序,能否正確使用防護用品,能否高度集中地完成工作任務,即人際沖突是否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影響?若是,其傳導機制有哪些?以上問題尚未得到解答。
已有研究證實,憤怒情緒在外界刺激與個體行為之間發揮著重要的傳導作用(Berkowitz, 2012;Ghim, Choi, Lim, & Lim, 2015)。Bao 等(2016)還發現,消極情緒往往是人際沖突發生后個體最直接的外在表現。與其他消極情緒不同,憤怒往往被視為人際互動過程中的一種威脅,對個體消極甚至暴力行為發揮最直接的預測作用(徐四華, 楊釩, 2016)。根據資源保存理論,個體有獲取新資源、維持已有資源及防止自身資源迅速流失的內在動機(Hobfoll, 1989)。在外界條件有利的情況下,員工會積極處理與同事的關系,增加工作投入等以獲取新資源;而當外界條件不利時,員工將消耗有限的資源予以應對,若這種資源消耗超出員工的承受范圍,便會引起巨大的心理壓力,進而導致異化的工作行為(Hobfoll, 1989, 2011)。人際沖突這一緊張的關系處境將消耗員工的有限資源,易引起緊張、焦慮及痛苦等負面情緒,并進而導致較多的負面工作行為(如減少安全工作行為)。因此,本研究假設人際沖突能夠通過激發憤怒情緒進而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消極影響。
除憤怒情緒之外,報復動機也可能發揮重要的傳導作用。自我決定理論指出,自主性、勝任力及關聯性是個體三個最基本的心理需求(Deci &Ryan, 1985)。若外界條件或刺激滿足個體的三種基本心理需求,個體便會主動地將外界刺激進行內化,進而產生積極的后果(如愉悅、興奮及高工作投入等);而當外界刺激無法滿足甚至損害三種需求時,個體便通過負面情緒、消極態度和行為等予以回應。當員工感受到被他者冷落、嘲笑甚至攻擊時,報復動機的產生往往不可避免。此外,報復動機是對個體負面行為進行預測最準確的效標之一(張珊珊, 唐輝, 劉艷艷, 呂少博,2015)。所以,在人際沖突的情況下,員工的三種基本心理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而應對這種緊張狀態,員工更傾向于進行被動地內化,進而激發出較高的報復動機,最終減少其安全工作行為。因此,本研究假設,人際沖突能夠通過激發員工的報復動機來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負向影響。
公共交通作為社會運輸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正常運行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共安全。伴隨著國家對社會公共安全風險治理的重視,公共交通安全問題已成為近些年新興的研究議題(丁宗廣等, 2016;岳俊林等, 2018)。與其他領域不同,公共交通因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性與自身系統的開放動態性使得其脆弱性特征顯著(盧文剛, 舒迪遠, 2016)。然而,作為公共交通脆弱性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的人際沖突研究仍不多見,尤其是有關人際沖突與道路運輸駕駛員安全工作行為關系的研究(丁宗廣等,2016; De Wit et al., 2012)。鑒于我國城市公交安全基礎依然較為薄弱,重特大事故時有發生的現實背景,以及公交安全對于社會運轉效率的重要意義,以公交司機為研究對象,探究人際沖突與其安全工作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可能的傳導機制,不僅能夠實現新的理論突破,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本研究基于資源保存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以公交車司機為研究對象,以憤怒和報復動機為中介,探究人際關系沖突對安全工作行為的影響及多重中介機制。研究理論模型參見圖1。

圖1 理論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以公交車司機為研究對象,采用時間滯后的縱向追蹤調查法進行兩次數據搜集,時間間隔為兩個月。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西安市三家公交公司中具有三年以上從業經驗的公交司機作為被試。第一次問卷調查測量人際沖突、憤怒及報復動機三個變量及社會人口統計信息,共有389 名公交司機參與測查,回收有效問卷293 份;第二次問卷調查由公交公司的主管對公交司機的安全工作行為進行評價,定向發放293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36 份。將兩次獲得的數據進行配對,最終獲得229 份有效樣本數據。其中男性176 名(76.86%),女性53 名(23.14%);年齡均值為3 8.0 1 歲(S D=9.2 6 歲);高 中 及 以 下2 1 名(9.17%),大專128 名(55.90%),本科77 名(33.62%),碩士及以上3 名(1.31%);工作年限3 ~5 年2 3 名(1 0.0 4%),6 ~1 0 年3 3 名(1 4.4 1%),1 1 ~2 0 年6 8 名(2 9.6 9%),21~30 年89 名(38.86%),31 年及以上16 名(6.99%)。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際沖突量表
本研究采用Jehn(1995)編制的人際沖突量表,共8 個題目,采用5 點計分,從“從不發生”到“總是如此”分別計1~5 分。8 個題目的均值代表人際沖突的水平,分數越高說明人際沖突越嚴重,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在原始文章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6。
2.2.2 憤怒量表
本研究采用Gelbrich(2010)編制的憤怒量表,共3 個題目,采用5 點計分,從“非常不贊成”到“非常贊成”分別計1~5 分。3 個題目的均值代表憤怒的水平,分數越高說明憤怒情況越嚴重,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在原始文章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
2.2.3 報復動機量表
本研究采用Hung,Chi 和Lu(2009)編制的報復動機量表,共4 個題目,采用5 點計分,從“非常不贊成”到“非常贊成”分別計1~5 分。4 個題目的均值代表報復動機的水平,分數越高說明報復動機越強,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在原始文章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2。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
2.2.4 安全工作行為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安全工作行為量表包含安全遵守行為與安全參與行為兩個子量表,分別由Cheyne,Cox,Oliver 和Tomás(1998)和Neal 等(2000)編制。子量表各包含6 個題目,整體共計12 個題目,采用5 點計分,從“非常不贊成”到“非常贊成”分別計1~5 分。12 個題目的均值代表安全工作行為的水平,分數越高說明司機表現出越多的安全工作行為,該量表信效度良好,在原始文章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3 和0.94。本研究中,兩個子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9 和0.92,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與分因子相比(GFI=0.95, TLI=0.95,CFI=0.96, SRMR=0.03, RMSEA=0.08),合并為單因子的擬合指標更好(GFI=0.96, TLI=0.95,CFI=0.97, SRMR=0.03, RMSEA=0.07)。所以,后續的假設檢驗過程中將其合并為單因子進行分析。
2.3 統計方法
使用SPSS22.0 進行數據錄入,并采用SPSS22.0 和AMOS22.0 對獲取數據進行分析。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首先,本研究參考Harman(1976)的方法,采用未旋轉的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共析出6 個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第一個因子可解釋的變異量為38.22%,6 個因子的累計可解釋的變異量為66.24%,均低于臨界值(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其次,驗證性因子分析也顯示各變量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四因子模型的擬合指數優于其他因子模型(參見表1)。綜上可知,共同方法偏差不會對本研究造成嚴重影響。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n=229)
3.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四個關鍵變量之間兩兩相關(p<0.01),這為后續的假設檢驗提供初步支持(參見表2)。
3.3 中介效應檢驗
基于相關分析結果,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人際沖突、憤怒、報復動機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的關系。同時,對公交司機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工作年限進行控制。
首先,以人際沖突為自變量,以安全工作行為為因變量,檢驗模型的主效應(即M0)。分析結果顯示,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的路徑系數達到顯著水平(β=-0.54,p<0.001),即人際沖突能夠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并且,此模型各項擬合指標良好(χ2/df=2.67,GFI=0.92, TLI=0.93, CFI=0.91, SRMR=0.04,RMSEA=0.04)。
其次,在M0的基礎之上,以憤怒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模型M1。結果顯示,人際沖突、憤怒及安全工作行為三者之間的路徑都達到顯著水平(β人際沖突→憤怒=0.38,p<0.001; β憤怒→安全工作行為=-0.43,p<0.001; β人際沖突→安全工作行為=-0.38,p<0.001),說明人際沖突通過激發公交司機的憤怒情緒進而降低其安全工作行為。此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數滿足統計要求(χ2/df=2.48, GFI=0.92,TLI=0.92, CFI=0.90, SRMR=0.03, RMSEA=0.04)。
此外,在M0的基礎之上,以報復動機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模型M2。結果顯示,人際沖突、報復動機及安全工作行為三者之間的路徑系數達到顯著水平(β人際沖突→報復動機=0.57,p<0.001;β報復動機→安全工作行為=-0.53,p<0.001; β人際沖突→安全工作行為=-0.23,p<0.01),說明人際沖突也能夠通過觸發公交司機的報復動機來減少其安全工作行為。該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良好(χ2/df=2.34, GFI=0.95,TLI=0.93, CFI=0.91, SRMR=0.03, RMSEA=0.04)。
最后,以人際沖突為自變量,以憤怒和報復動機為中介變量,以安全工作行為為因變量,構建復合中介模型M3(參見圖2)。分析發現,各路徑系數都達到顯著水平(p<0.01),模型擬合指數良好(χ2/df=2.21, GFI=0.92, TLI=0.92,CFI=0.90, SRMR=0.04, RMSEA=0.04)。因此,本研究的復合中介模型成立,說明人際沖突通過激發憤怒情緒和報復動機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消極影響。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n=229)

圖2 人際沖突、憤怒、報復動機與安全工作行為的復合中介模型
3.4 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憤怒和報復動機的中介效應,提高研究結論的準確性,運用Bootstrapping 程序,采取5000 次不放回抽樣的分析方法計算復合中介模型95% 的置信區間(參見表3)。分析結果顯示,三種不同類型中介路徑的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零,說明憤怒和報復動機在人際沖突和安全工作行為關系之間發揮著復合中介的作用,即人際沖突分別從憤怒和報復動機兩個方面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負向影響。
4 討論
本研究以公交車司機為研究對象,以憤怒和報復動機為中介,構建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時間滯后的方式進行數據搜集,并借助結構方程與Bootstrapping 對獲得的數據進行分析。

表3 中介效應顯著性檢驗分析結果(n=229)
首先,本研究發現人際關系沖突對安全工作行為有著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以往安全工作行為前置影響因素的探討主要從心理資本(高偉明,曹慶仁, 2015; 岳俊林等, 2018)、管理者行為與風格(曹慶仁, 李凱, 李靜林, 2011; Wu, Chen, & Li,2008)以及安全氛圍(葉新鳳, 李新春, 王智寧,2014; Neal et al., 2000; Smith et al., 2018)視角進行考察,人際沖突作為一種重要的負面壓力源,其潛在影響被忽略了。為了彌補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創新性地從人際關系視角探究人際沖突對安全工作行為的影響,這一研究推動了相關理論的發展與完善。員工面對的人際沖突源是多方面的,如組織內部(如上級或同事)、顧客和家庭,沖突源的多樣性、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均提高了員工遭受負面壓力的概率,也大大提高了員工對抗此壓力的難度(沈秉勳, 2009; Weingart et al.,2015)。所以,員工正常的工作行為受到嚴重威脅,進一步影響其工作績效。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這些人際關系沖突能夠激發司機的負面情緒,減少其理性的工作行為;另一方面,員工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應對負面壓力源,將引起極大的資源損耗,導致員工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容易引發不安全工作行為。
其次,本研究發現了憤怒在人際關系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數據分析結果顯示,人際關系沖突通過激發員工的憤怒情緒進而降低其安全工作行為,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似(Berkowitz, 2012; Ghim et al., 2015)。本研究結果再次體現了憤怒情緒在外部消極刺激與主體負面行為之間重要的中介作用,也表明了憤怒情緒的重要傳導作用。對遭受人際沖突的員工而言,其基本心理需求(如自主性和社會聯系)未得到滿足,于是產生緊張、焦慮及失望等,進而引起憤怒情緒(徐四華, 楊釩,2016)。他們更容易做出消極的工作行為,如攻擊行為、沖動行為及反社會行為等。將憤怒情緒納入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研究框架同樣也拓展了憤怒情緒的研究范圍。
再次,本研究表明人際關系沖突能夠通過激發報復動機對安全工作行為產生負面影響。通過探究報復動機在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重要的傳導作用,本研究一方面豐富了報復動機的相關研究,加深了對報復動機的理解,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凸顯出報復動機的破壞性與危害性。研究發現,遭受人際沖突員工的報復動機更強,所表現出的安全工作行為更少。這主要是因為員工為發泄由人際沖突所引起的負面情緒,表達自己的不滿,容易將同事、上級或顧客當作發泄對象予以報復(張珊珊等, 2015)。比如,對于公交司機而言,可能通過更改操作流程、隨意調整行駛路線以及蠻橫駕駛等行為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些異化的反生產工作行為將大大降低公交車行駛的安全性,最終威脅到乘客安全。
最后,本研究發現了憤怒與報復動機在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的復合中介作用。通過對多重中介模型的分析,本研究揭示了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復雜的傳導機制。一方面,人際沖突能夠激發憤怒情緒來對安全工作行為發揮消極作用;另一方面,人際沖突也能夠刺激員工的報復動機,從而降低其工作的安全性。多重中介效應的發現,顯示出人際沖突不僅通過改變員工情緒,還通過激發他們的報復動機來對其安全工作行為產生影響。從情緒和動機兩個方面進行中介機制探究有助于在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構建清晰完整的理論框架。并且,研究再次揭示出人際沖突對員工施加負面影響的多面性及嚴重性。
本研究為增強員工(尤其是公交車司機)安全工作行為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一方面,組織應對員工所正在遭受的和潛在的人際沖突予以高度重視,通過提高組織公平性、構建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及開展及時的心理疏導等避免人際沖突的發生,或最大程度地降低其危害;另一方面,員工也應正確看待各種人際沖突,減少其對自身情緒和動機的負面影響,將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中,避免其負面影響波及到日常工作。
5 結論
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人際沖突能夠顯著減少安全工作行為,憤怒能夠中介人際沖突對安全工作行為的負面影響,報復動機也能夠中介人際沖突對安全工作行為的負面影響,憤怒和報復動機在人際沖突與安全工作行為之間發揮著多重中介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