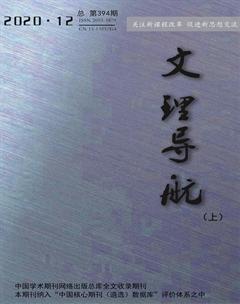《神的一滴》深層意蘊探究
馬占奎
【摘 ?要】要想弄明白文章中蘊含的作者的深層思想,我們必須深入文本。有人認為可以理解為“神的一滴眼淚”,它為世人而流,啟示人們在渴盼留住湖光山色的同時,更應該反思自己如何去對待自然,對待生命和生活。
【關鍵詞】神的一滴;思想;文本理解
要想弄明白文章中蘊含的作者的思想,我們必須深入文本。
首先,我們從文章題目入手,“神的一滴”源自文章最后一句,“有人建議過,這湖可以稱為‘神的一滴”。有人認為可以把它理解為“神的一滴眼淚”,它為世人而流,啟示人們在渴盼留住湖光山色的同時,更應該反思自己如何去對待自然,對待生命和生活。
要想明確這個問題,請大家認真閱讀文章第6段中“對它,就算只有一瞥,也已經可以洗凈現代繁華大街上的污濁和引擎上的油膩了”一句。我的第1個問題是“現代繁華大街上的污濁和引擎上的油膩了”是什么意思?很明顯,我們可以推斷出“現代繁華大街”“引擎”是現代工業文明的代表,“污濁”和“油膩”指工業文明對環境的污染或工業文明對人的靈魂的侵蝕污染。我的第2個問題是這句話的主語是什么?聯系上文“每天他們至少有一次機會與莊嚴、純潔的瓦爾登湖相遇”一句,我們不難看出主語應該是“瓦爾登湖的莊嚴、純潔”。
“有人建議過,這湖可以稱為‘神的一滴”一句的英文文本是:One proposes that it be called "God's Drop." 這句話有兩個譯本:一是徐遲譯的“有人建議過,這湖可以稱為‘神的一滴”,一是李繼宏譯的“有人曾經提議將其命名為‘上帝的水滴”。
據美國專家研究,“有人”應該是指“愛默生”,他曾將鵝湖稱為“水滴或上帝之湖”。李繼宏的譯本把“Drop”譯作“水滴”含義更明白。
作者之所以把它和上帝聯系起來,只是表達了在梭羅的眼里瓦爾登湖有著無上的地位,在文本中這樣的句子俯拾皆是。譬如:“它的四周完全……水上可以演出山林舞臺劇。”“這是和恒河之水一樣圣潔的水!”“啊,這是瓦爾登湖,還是我許多年之前發現的那個充滿著神秘和活力的林中湖泊。”“……我幾乎要驚呼:瓦爾登湖,是你嗎?”
當梭羅情不能自已的時候,還做了一首小詩,其英文文本是:It is no dream of mine, To ornament a line; I cannot come nearer to God and Heaven. Than I live to Walden even. I am its stony shore, And the breeze that passes o'er; In the hollow of my hand. Are its water and its sand, And its deepest resort Lies high in my thought.我們同樣來看李繼宏和徐遲兩個譯本:
我從來不曾夢想,成為詩句的裝扮;最為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地方,莫過于我生活的瓦爾登湖畔。我是清風吹拂在它身上,是它那鋪滿石子的堤岸;我的手掌掬起了,它的清水和沙子,而它最幽深的處所,在我的思維里高臥。——李繼宏譯
這不是我的夢,用于裝飾一行詩;我不能更接近上帝和天堂,甚于我之生活在瓦爾登。我是它的圓石岸,飄拂而過的風;在我掌中的一握,是它的水,它的沙,而它的最深邃僻隱處,高高躺在我的思想中。——徐遲譯
其中“In the hollow of my hand”一句,李繼宏譯本譯作“我的手掌掬起了”,而徐遲譯本譯作“在我掌中的一握”,二者差異的關鍵在于“hollow”一語,其中文義是“空的”“中空的”,這樣分析來看李繼宏的“掬”更能體現梭羅的本義,因為“掬”在現代漢語中含義是“雙手捧(東西)”,含有深深的敬意。
在這首小詩中,“I cannot come nearer to God and Heaven/Than I live to Walden even.”徐遲的翻譯有點艱澀,李繼宏的翻譯很是澄亮,譯文是“最為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地方,莫過于我生活的瓦爾登湖畔”。這句翻譯把梭羅對瓦爾登湖的贊美上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稱它是“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地方”。
那么,我們最渴望知道的事情是在“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地方”,梭羅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文章第2段:“一個夏天的上午……推送到哪一個岸邊來了。”第4段:“我還可以站在那兒,看到一只飛燕坦然掠下,從水面銜走一條小蟲,正和從前一樣。”這兩段文字記錄的是他的日常生活,是一種梭羅式的富足生活:1.消磨光陰;2.慵懶;3.揮霍;4.偷閑。
而這種富有與金錢無關,為了突出這種富足生活方式,作者還用一個段落專門寫世間的蕓蕓眾生的生活。那么,世間的蕓蕓眾生們又是如何和瓦爾登湖相處的呢?
1.村民:把湖水引到村中洗碗洗碟子。2.伐木人:樹木先后砍光。3.愛爾蘭人:鐵路線已經侵入。4.冰藏商人:已經豪取過它的冰。
作者選擇了四類人給我們展示了工業化時代的大眾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雖說也“富足”,但這種“富足”,過于物質化,改善的只是人們的物質生活。
這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注重精神享受與提升,一種注重物質獲得與改善。而這兩種生活方式,在梭羅的思想里,精神享受與提升才是生活的本真。
這樣梭羅很容易給大家一種“苦行僧”“退隱林泉”的印象,其實,梭羅不反感這些新生的社會,但他特別擔憂客觀條件的改善無法提升人們的思想境界,甚至會導致人們忘記生活的意義,本末倒置地去追求一些外在的東西。他曾在《瓦爾登湖·生計》和《瓦爾登湖·居所和生活的目標》中這么寫道:“談論重大的話題,我們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速度。我們渴望在大西洋底下鋪設隧道,讓舊世界和新世界的距離縮短幾個星期;但第一道傳過來敲打美國人耳朵的新聞也許是阿德萊公主罹患百日咳。”
至此,我們明白了梭羅寫作《瓦爾登湖 湖泊》一文的真正用意:1.呼喚生活的本真,呼喚自身的靈性回歸。2.批判工業化破壞了大自然的美,把改善物質條件當成人生最高,甚至唯一目標的現象。
當我們靜心品讀完這篇文章時,怎么會不產生一種“‘偷閑是一種人生的境界”的感觸?李商隱曾在《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同樣描寫過他的“偷閑”生活,詩文寫道: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留得枯荷聽雨聲。”一句足夠“悠閑”,但這種“悠閑”在李商隱這里僅僅是一種精神的寄托,大自然只是一種襯托,是一個客人罷了。
可我們輕輕吟誦著“我先把船劃到湖心,而后背靠在座位上,似夢非夢地漂流著,直到船撞在沙灘上,驚醒的我才欠起身來,看看命運已把我推送到哪一個岸邊來了”時,明顯感受到的是大自然就是和作者共處的友人,是這個世界的主人,而這種狀態在梭羅那里就是生活的本真。
一種是中國式的儒道佛相融式的哲學,一種是梭羅式的哲學。對精神的生活的享受與提升才是梭羅追求的人生至高目標,才是創作《瓦爾登湖·湖泊》的本意。
【參考文獻】
[1]尉建芳.沉靜,讓課堂別樣精彩——《神的一滴》教學引起的思考[J].教學月刊,2011
[2]肖培東.《神的一滴》教學節錄[J].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18(001):116-120
(浙江省慈溪市慈中書院,浙江 寧波 31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