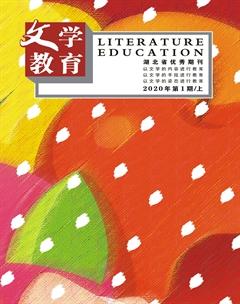詩歌是一種反熵的媒介
熵本是物理學上的一個術語。如果能量在空間中分布得越混亂,熵就越大。從物理學的這種規律中進行遷移,耿占春看到了話語、文字、真理、思想等也難逃這樣的“晚景”和命運。因此他認為,一個活著的人要具備反熵的意義。
活著的人只有具有一種責任感、正義感、神圣感的時候,才可能具有一些反熵的力量,盡管到最后也是“安靜如同宇宙最終的沉寂”,或者難逃一死,或者被人遺忘,或者在某種歷史書中只占據零星頁面的敘述。而一個詩人,要想具有反熵的價值,也必須使自己的思想一開始出現就擺脫“閑談的面孔”,擺脫使思想一出生就徒具形式的窘境。在詩歌中,耿占春寫下了許多“為之擔憂的話語”。比如在《旅途之歌》中,他為身處困境中的自我擔憂;在《盛世危言》中,他從盛世看到潛在的危機,為此寫下了警世的話語:“我唯一所求的,是別堵上/那些還能說話的嘴,別侮辱//本來就有限的智商,我承認/它是幾希禽獸的最后一點區分。”其實耿占春深明拿破侖“當代的悲劇,就是政治”這句話的含義,他深知這就是我們的主要境況之一。在《論惡——讀〈羅馬史〉》中,他擔憂“每個信仰強權的人/都在為新神開光要求血的祭禮”;在《論語言》中,他深深地為語言帶來的各種危機擔憂。當權力成為最高真理,成為唯一正確的意志,它便會成為一種絕對的存在。于是,強權可以強迫他人流血犧牲,可以制約新聞自由,可以拿語言來控制思想,甚者暴力判決、殺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在這樣無法擺脫的境況當中,作為有某種角色的個體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呢?耿占春在近二十年前就曾為我們傳達出其內心的這種普遍性體驗:“在無處不在的吞并一切的權利組織和網絡中,一個人難能有自由的本真的生命形式,也許他只有可以稱之為失去自我喪失靈魂的那種體驗。”對于這個不甚理想的世界,他是有深切感知的。
此外,在《世界美如斯》中,他還曾擔憂“驚夢的闡釋者/曾經改變過/人類的編年史”,擔憂“如今只有一個魔咒/還未曾實現——‘美,能拯救世界”;在《論快樂》中,他也指出“當快樂出現在有權力感的地方/它就與厭倦等同”。總之,耿占春在他的詩歌中不厭其煩地表達著他的擔憂,他不希望看到熵在最后的狂歡。盡管在談論傳統讀書人責任的時候,他認為閱讀與書寫可能是對責任的一種逃避或偏離,“把閱讀與書寫轉變成一種快樂,把責任降低到自身的快樂或‘語言的歡樂”但這無疑也是“他的自卑自謙”。但至少語言可以幫助實現對良知的一部分救贖。
耿占春指出,詩歌是一種反熵的媒介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種非封閉、反耗散的結構。“偉大詩篇的話語是一種非封閉的象征結構。”耿占春認為,詩歌要保持持續性的能量,要在歷史中一直保持它的“秘密”,就要持一種開放的結構,否則當它封閉、固有的意義分散殆盡,其生命也就結束了。為此,耿占春喜歡詩歌持一種旁白的姿態,青睞詩歌的畫外音,期待詩歌成為“未完成的陳述”,厭倦詩歌“沒有個性的經驗”及其“致命的單調”。鑒于這樣的詩歌認知,耿占春在寫作中也貫穿了同樣的理念。他的《一首贊美詩》,其實并不是一首用以贊美的詩。在這首詩中,詩人其實是在進行一個詩的呼喚,是以一首詩來喚起另一首詩:“浮云詭秘看蒼山,憶起一首詩——”這即是一種“未完成的敘述”。從結構經營上看,他的《精神分析引論》也具有一個令人深思的架構,盡管全詩前三節均以理性的邏輯在建構一種“瞻對”的視角,第四節又以理論歸結的方式收束了全詩,這種推導思路分明,并無任何向外突破的“犄角”,然而一旦聯想到詩的題目“精神分析引論”,我們的視野就豁然打開了:全詩與“精神分析引論”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為什么“一個人就必須是又不是另一個人”?它與弗洛伊德有內在思想上的一致嗎?此外,《辯護詞》一詩也是如此,前兩節還在探討人類與智能機器人之間的矛盾關系,第三節就以比喻的修辭引入了詩人和上帝,最后一節又拋出了“漫游奇境的愛麗絲”的“辯護”。那么,詩人到底意在以什么為鏡,又想鑒照出什么呢?他期望以“辯護”為幌子來達到什么樣的“修行”?這首詩制造了美妙的畫外音,它寄望他的讀者去進行一番有趣的找尋。
詩的這種開放性結構當然與語言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耿占春對于語言是敏銳的。他看到了語言有一種分裂的力量。這是他的詩歌寫作的一個秘密所在。
趙目珍,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