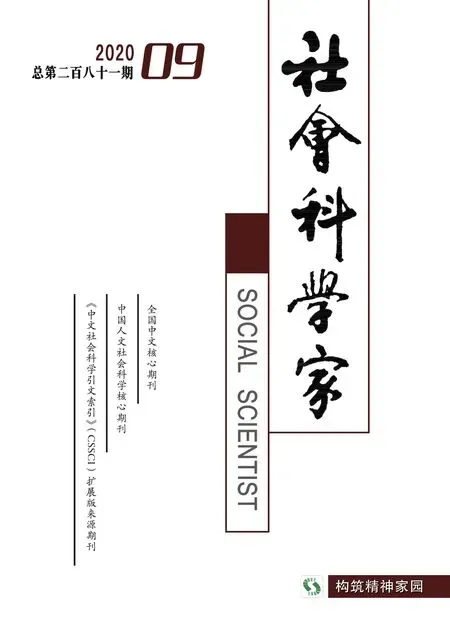總體國家安全觀視角下我國間諜罪立法問題檢視與修正建議
梅傳強,董 為
(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1120)
長期以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和各種敵對勢力把中國作為顛覆、滲透和破壞主要目標,利用我擴大開放之機,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廣泛收集、竊取、刺探我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情報,從事危害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動[1]。反觀我國間諜犯罪立法,卻顯得極為滯后,并無法適應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新要求和反間諜工作的新形勢,間諜犯罪行為在刑法上難以得到全面評價和有效規制。因此,根據新形勢、新要求,對我國《刑法》中間諜罪立法完善展開系統研究,是當前學界必須面對的一項重要而又緊迫的任務。
一、總體國家安全觀背景下我國間諜罪立法問題檢視
現階段,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立法主要問題有:
(一)規制范圍過窄,無法適應構建“國家安全體系”的國家政策新需求
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立法是基于傳統國家安全觀,其構成要件中對“間諜組織”和“間諜組織代理人”的過度強調,已無法滿足構建國家安全體系的國家政策需要①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及“11種安全”,黨的十九大把“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總體國家安全觀兼顧了傳統和非傳統兩個方面的國家安全問題,最主要表現為其全面性和完整性,國家安全涉及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既有經濟的又有政治的,既有文化的又有軍事的,既有社會的又有生態的,既有國際的又有國內的,既有傳統的又有非傳統的,相對于傳統國家安全觀只關注政治、軍事安全而忽視經濟、文化、社會、網絡、生態等領域的安全,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認識和把握各領域各方面的安全問題,比傳統的安全觀更具全面性、完整性。參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頁。。例如,對于日益猖獗且危害極大的經濟間諜,《刑法》往往僅能以“侵犯商業秘密罪”進行規制,其原因在于經濟間諜隱蔽性更強,竊密對象范圍更廣,案件中往往難以查出能夠被國家安全部認定的間諜組織。例如,在2009年的“力拓案”中,對被告胡士泰等人的竊密行為的法律定性,即究竟應當認定為間諜行為還是侵害商業秘密行為,在司法實踐中便引發了分歧[2]。最后由于該案中未能查出能夠被國家安全部認定的間諜組織及代理人,最終僅能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定罪量刑。此案充分反映出我國間諜罪立法對于經濟間諜的規制缺失以及《刑法》與《反間諜法》關于間諜行為認定標準銜接的脫節。反觀國外,美國首先對經濟間諜進行了專門立法,其在1996年的《經濟間諜法》中將經濟間諜視為與傳統間諜類似的行為,美國國會也堅定地認為經濟利益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利益的侵害應當構成對國家安全利益的侵害,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包括對本國經濟利益的維護,經濟間諜因侵害美國經濟利益而侵害美國國家安全[3]。同樣,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立法②日本于1998年參照美國《經濟間諜法》制定了《技術情報適當管理法案》,也強調對公司高科技的保護。德國聯邦政府則設有專門的“經濟間諜工作委員會”,并由德國政府的情報機關和反間諜機關——聯邦憲法保衛局直接負責對經濟間諜進行防范,并對風險進行評估。。中外對比,我國間諜罪立法對“間諜組織”和“間諜組織代理人”的過度強調,導致間諜罪在面對新型間諜時被排斥適用,其缺陷一目了然。
(二)規制重點失偏,無法適應新形勢下反間諜工作新需求
通過對已公開的間諜案件進行研究分析可以發現,與傳統的間諜滲透威脅相比,近年來我國所面臨的間諜威脅呈以下特點:一是掩護身份更加隱蔽。間諜機關及其代理人更多地采取以公開掩護秘密、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手段進行滲透和竊密活動,大大增加了案件偵破難度和間諜組織認定難度。二是竊密范圍更加廣泛。竊密對象從傳統的政治情報、軍事情報增加為政經情報、科技情報、軍事情報等多種情報,竊密和滲透的方向也由黨政機關、軍工部門擴展到國有企業、高科技公司、高校科研機構等多個方向。三是竊密場所更加寬廣。隨著中國社會經濟與世界的進一步融合,“一帶一路”倡議不斷向全球各地延伸。除傳統的使領館外,大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逐步成為間諜機關滲透的目標。但目前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立法嚴重滯后,規制重點明顯失偏,已無法應對間諜滲透的新特點以及適應反間諜工作的新需求。
歸納已公開的間諜案件可以發現,間諜犯罪常見的犯罪模型為:間諜組織或其代理人通過各種手段策反可資利用對象——該對象參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及間諜組織代理人任務——該對象按照間諜組織部署運用各種手段搜集竊取情報——該對象向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交付情報——獲取間諜組織報酬。我國間諜罪立法規制重點放在第二個階段,重點打擊參加間諜組織和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任務的行為,其存在以下問題:
1.對于更為源頭的“間諜組織或其代理人的滲透、策反行為”缺乏規制,不合理地限縮了間諜罪犯罪圈。目前我國《刑法》中間諜罪所規定的四種罪狀均未規制間諜犯罪的源頭——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本身。有學者認為,間諜組織必然通過成員或代理人在境內活動,其成員本身已經加入間諜組織,而代理人也必然接受了間諜組織的任務。因此,間諜罪的罪狀實際包含了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本身。[4]但是,此觀點并不成立,因為間諜組織成員在境外加入間諜組織的行為,并無法為我國《刑法》所規制。事實上,間諜組織成員絕大部分為外國籍人(排除我國刑事管轄權中的屬人管轄),加入行為絕大多數是在國外進行(排除我國刑事管轄權中的屬地管轄),而該加入行為,在其所在國不可能被認定為犯罪(排除我國刑事管轄權中的保護管轄),加上間諜行為被視為各國的國內管轄事項(排除我國刑事管轄權中的普遍管轄)③間諜行為目前在國際法上更多處于既不是合法也很難說是非法的“灰色地帶”,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各國的國內管轄事項。參見黃志雄:《論間諜活動的國際法規制———兼評2014年美國起訴中國軍人事件》,《當代法學》2015年第1期。,同樣,間諜組織代理人接受間諜組織任務,往往也在國外進行。因此,作為間諜威脅的來源——外國人在境外參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任務,再入境開展間諜活動,此類行為已因缺乏刑事管轄權而被排斥于間諜罪適用范圍之外,間諜罪立法缺失進一步凸顯。
2.對于更容易取證的“交付”“竊取”行為缺乏規制,不合理地增加了間諜罪證明難度。一是我國間諜罪立法,對于“心照不宣”的情況無法處理。根據已公開的案例分析,間諜組織、間諜組織代理人與間諜罪犯罪嫌疑人之間有時會處于一種“心照不宣”的狀態,即犯罪嫌疑人知道或已經猜到自己在為間諜組織工作,甚至可能已經成為該組織成員,但實際并不清楚長期與自己聯系的具體是什么間諜組織。此情況下,對間諜組織的認定存在相當的困難,很大程度地排除了間諜罪的適用。二是我國間諜罪立法,對于“避重就輕”無法處理。根據已公開案例分析,間諜罪犯罪行為人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備較強的應變能力,同時,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在通聯過程中還會對其進行培訓。因此,在面對審訊時,其往往避重就輕,絕不會承認自己接受間諜組織或其代理人任務。因間諜罪入罪條件不合理的嚴苛性,此情況下很難再以間諜罪入罪,最終僅能以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罪定罪量刑。三是我國間諜罪立法,對于“主動投靠”無法處理。目前已公開的案例中不乏此類案件:部分接密人員直接攜涉密資料主動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希望長期為對方“效力”,例如給我國黨政軍帶來重大損失的黃宇間諜案。如果在與對方通聯后,在尚未接受對方任務,也未正式成為間諜組織成員之時案發。此時,其行為首先不符合間諜罪的完成形態。同時,因學界普遍認為間諜罪屬行為犯[5],其既然已主動投靠間諜組織,便不應當按間諜罪未遂加以處罰。另外,由于案件中已經明顯出現了間諜組織,以《刑法》第111條①我國《刑法》第111條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罪規定: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來定罪量刑也不合適,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來定罪量刑更是罪責刑不相適應。反觀國外關于間諜罪的立法,《法國刑法典》第411-6條關于間諜罪的規定為:“向外國國家……提供或者使之得到如被使用、泄密或收集足可危害國家基本利益之情報……處15年拘押并科225000歐元罰金”;《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276條關于間諜罪的規定為:“……向外國國家、外國組織或其他代理人交付以及為交付而收集、竊取或保存構成國家機密的情報……處10年以上20年以下剝奪自由”;《德國刑法典》第98條“叛國的諜報行為”中規定“從事下列活動……處5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1.為外國搜集和傳遞國家機密,或2.向外國或其中間人承諾從事上項活動”。由以上大陸法系主要國家的刑法可以看出,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國關于間諜罪的立法,其規制重點更多地放在“提供”“使之得到”“交付”“傳遞”的環節,更加強調的是“向外國”和“危害國家安全”兩大特性,而并不糾結于對“間諜組織”及“間諜組織代理人”的發現和認定。
3.對于專有概念的認定程序煩瑣,進一步阻礙了間諜罪的適用。我國間諜罪罪狀表述中的關鍵詞“間諜組織”“間諜組織代理人”為專有概念,間諜罪的入罪必然需對這兩個專有概念進行認定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實施細則》規定,間諜組織和間諜組織代理人由國務院國家安全主管部門確認,即由國家安全部認定。。從已公開的案件來看,隨著間諜滲透方式的逐步發展,間諜組織的掩護方式越發隱秘,往往披著“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基金會”“慈善組織”等外衣開展間諜活動。加之其竊密對象寬廣,涵蓋政經情報、科技情報、軍事情報等多種情報,依照目前認定方式,對間諜組織的認定恐不客觀、不完整,導致部分間諜犯罪因無法認定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而被迫以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定罪量刑。但該罪與間諜罪相比,一是刑罰配置明顯偏輕,無法起到較好的打擊和預防效果,二是需進行密級認定,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等往往難以被認定為國家秘密,其適用本身也存在障礙。
(三)規制銜接失當,破壞法秩序統一
因立法滯后,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的立法與多部法律及實施細則存在沖突③具體而言,與《反間諜法》《反間諜法實施細則》《國家安全法》等法律存在沖突。參見李永升,胡勝:《論間諜罪的司法誤區及立法完善》,《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7第7期,第100頁。。其中,間諜罪的立法與《反間諜法》的沖突尤其明顯,而該沖突又集中體現于對間諜行為的范圍劃定并不一致。
1.對“不一致”之處的對比分析
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涵蓋四種行為①我國《刑法》第一百一十條(間諜罪)規定,有下列間諜行為之一,危害國家安全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二)為敵人指示轟擊目標的。據此,可以分解出四種行為:一是參加間諜組織的行為;二是接受間諜組織任務的行為;三是接受間諜組織代理人任務的行為;四是為敵人指示轟擊目標的行為。。與之相對,我國《反間諜法》規定的間諜行為至少包括十二種②《反間諜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本法所稱間諜行為,是指下列行為:(一)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二)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三)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的竊取、刺探、收買或者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或者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四)為敵人指示攻擊目標的;(五)進行其他間諜活動的。據此,可以至少分解出十二種行為:一是間諜組織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二是間諜組織代理人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三是間諜組織指使、資助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四是間諜組織代理人指使、資助他人實施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五是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其勾結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六是參加間諜組織;七是接受間諜組織任務;八是接受間諜組織代理人任務;九是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的竊取、刺探、收買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或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十是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指使、資助他人實施的竊取、刺探、收買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或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十一是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其勾結實施的竊取、刺探、收買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或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十二是指示攻擊目標。。
對比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立法:《反間諜法》規定的前四種間諜行為,主要打擊對象為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本身;《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五種間諜行為,與間諜罪四種間諜行為第二、三種不同之處在于,其并不強調“接受任務”;《反間諜法》規定的第六、七、八種間諜行為即間諜罪四種間諜行為的前三點;《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九、十種間諜行為則把范圍擴大至“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所實施或指使、資助他人實施的兩類行為③兩類行為分別是:一是竊取、刺探、收買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二是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反間諜法》規定的第十一種間諜行為則是該法第五種間諜行為的補充④把反間諜法認定的第五種間諜行為(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其勾結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范圍擴展到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勾結實施的兩類行為:一是竊取、刺探、收買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二是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反間諜法》規定的第十二種間諜行為與《刑法》間諜罪的第四種行為類似,但反間諜法改“轟擊目標”為“攻擊目標”,一字之差,實則是范圍之擴大;《反間諜法》對間諜行為的認定,最后還設有兜底條款,即其他間諜行為。由此可見,《反間諜法》規定的間諜行為范圍,涵蓋且廣于間諜罪所規制的間諜行為。
2..對“不一致”之處的傾向性選擇
針對我國《刑法》中間諜罪的規制范圍與《反間諜法》關于間諜行為的規定范圍不一致的情況,筆者更傾向于以《反間諜法》第38條為標準,對《刑法》中間諜罪的客觀行為進行修正。首先,相對于我國《刑法》對間諜行為的單向單層次認定,《反間諜法》對于間諜行為的規定更加科學合理。同時,符合《反間諜法》規定的間諜行為,如果危害了國家安全,達到犯罪的程度,就沒有理由不作為間諜罪處罰。其次,《反間諜法》頒布于2014年,相對于1997年《刑法》關于間諜罪的立法,《反間諜法》是防范、制止和懲治間諜行為的“新法”,更加能夠適應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形勢,承擔起構建國家安全體系的新任務。例如,《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一、二、三、四種間諜行為,其主要打擊對象為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本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對間諜威脅源頭打擊不力的缺陷;《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五種間諜行為,其并不強調“接受任務”,其原因在于司法實踐中存在境內人未接受明確的任務而主動出賣情報等情況;《反間諜法》規定的第九、十種間諜行為把認定范圍擴大至“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也是為了適應“掩護身份更加隱蔽”“竊密范圍更加廣泛”等間諜滲透新特點,并為把經濟間諜、科技間諜納入間諜罪規制范圍掃除了部分障礙。再次,除《反間諜法》外,我國《刑法》中間諜罪立法還與《國家安全法》等法律存在沖突,其中一個重要沖突點就在于間諜罪所規制的間諜行為范圍過窄,無法實現《國家安全法》維護國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2個領域國家安全的立法目的,與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總體”,突出“大安全”的理念相沖突。
另外,我國《刑法》間諜罪立法與《反間諜法》的沖突還表現在,《反間諜法》對自首、立功的特別寬容條款以及對特殊情況“不予追究”條款缺乏《刑法》法條支撐。具體表現在《反間諜法》第27條第二款①我《反間諜法》第27條第二款規定:實施間諜行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給予獎勵。與《刑法》第68條②《刑法》第68條規定:立功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存在出入,以及《反間諜法》第28條③《反間諜法》第28條:在境外受脅迫或者受誘騙參加敵對組織、間諜組織,從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及時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國機構如實說明情況,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過所在單位及時向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如實說明情況,并有悔改表現的,可以不予追究。與《刑法》第67條④《刑法》第67條: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以及《刑法》第13條“但書”存在出入,《反間諜法》相關規定既與《刑法》總論相關法條存在沖突,又在《刑法》分則間諜罪的立法上缺乏支撐,其在適用上必然存在一定障礙。
二、總體國家安全觀背景下我國間諜罪立法修正建議
因我國目前間諜罪構成要件異常封閉,難以采取刑法解釋的方法解決前述問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背景下,需對我國間諜罪立法進行修正,使其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
(一)參照《反間諜法》38條對間諜罪規制范圍進行調整
參照《反間諜法》第38條對間諜行為的認定范圍,擴大我國《刑法》110條間諜罪規制范圍。此處應注意,反間諜法第38條已明確的12種間諜行為其實仍有明顯遺漏,法益保護仍然不周。⑤據此立法,“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所實施或指使、資助他人實施兩類固定的行為(1.竊取、刺探、收買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情報。2.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才能被間諜罪所規制。同樣,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間諜組織及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個人勾結實施的以上同樣兩種行為才能被間諜罪所規制。如此修改,間諜罪規制范圍仍然較窄,對科技間諜、經濟間諜適用仍然困難。但《反間諜法》第38條設有兜底條款,即“進行其他間諜活動”。筆者認為,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野下,為全方位維護12種國家安全,可在《刑法》間諜罪中也加入此兜底條款,即加入“進行其他間諜活動的”。如此,既可以應對層出不窮的新型間諜犯罪,又有利于維護《刑法》的安定性。為遵循謙抑性原則,如果加入此兜底條款,對間諜行為的認定,仍需嚴格按照以下標準:
1.涉外性。被認定的間諜行為必須具有涉外性質,即必須出現境外因素[7],否則無法被認定為間諜行為。需注意,此處的“境外”,系邊境而非國境。在195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曾把間諜組織與特務組織進行區分。例如,在該條例第11條反革命破壞罪中,即把間諜組織與特務組織進行并列。而到1979年《刑法》已無“特務”這一表述,不再區分特務組織與間諜組織。在認定間諜行為時強調的境外因素,自然也應指邊境之外,即包含港澳臺地區。
2.危害國家安全性。被認定為間諜行為需事關國家安全,其應包含兩個方面,既在范圍上事關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12種安全,又在程度上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程度。當然,在12個不同領域,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程度的標準會有所差異,例如事關軍事安全、核安全與事關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必然有所不同,需綜合考量現實危害等多個方面因素,再加以評判。
3.隱蔽性。間諜行為,通常還是指以竊密為主的各類非法諜報活動,其應當具備一定程度的隱蔽性,包括身份隱蔽,即以掩護身份開展行動;手段隱蔽,即以秘密手段進行竊密、滲透;對象隱蔽,竊密的最終目標要么是國家秘密,要么是被采取了保密措施不能為外界所知悉的秘密。間諜行為隱蔽性的特點,有助于更好的認定間諜行為,進而把間諜行為與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相區別。
(二)把單位納入間諜罪犯罪主體
我國現行《刑法》中間諜罪立法并無單位可成為犯罪主體的規定。因單位犯罪需以《刑法》明文規定單位應受刑罰處罰為前提[8],因此,單位無法成為間諜罪犯罪主體。但就已公開的案例分析,隨著間諜滲透方式的逐步發展,間諜組織更多地披著“跨國公司”“基金會”“慈善組織”等外衣開展間諜活動。間諜罪僅以個人為犯罪主體,將導致對境外間諜組織及其成員在境內的掩護機構缺乏打擊。例如,在胡士泰案中,如果以間諜罪對胡士泰本人進行處罰,為胡從事間諜行為提供掩護的力拓新加坡公司(隸屬澳大利亞)則無須承擔刑事責任。而依照美國《經濟間諜法》,傳統間諜通常由外國政府控制下的情報機構及外國政府的代理人直接實施①See Nathan Alexander Sales,Secre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s,58 Alabama Law Review,811 (2006-2007),pp.811-812.See also LT.Col.Geoffrey B.Demarest,Espionage in International Law,24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321(1995-1996),pp.321-323.,而經濟間諜的實施者可以是任何主體,包括獨立的個人或者外國政府、公司以及它們的代理人。相比之下,我國《刑法》排除單位成為間諜罪犯罪主體并不合理。因此,建議在我國《刑法》第110條間諜罪后加入單位犯罪條款。
(三)《反間諜法》第27條、28條直接寫入間諜罪相關條款
如前所述,需在我國《刑法》第110條間諜罪后加入與《反間諜法》第27條、28條相對應的條款。
修改后的《刑法》第110條間諜罪為:
有下列間諜行為之一,危害國家安全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
2.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
3.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的竊取、刺探、收買或者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或者策動、引誘、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活動;
4.為敵人指示攻擊目標的;
5.進行其他間諜活動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
實施間諜行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在境外受脅迫或者受誘騙參加敵對組織、間諜組織,從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及時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機構如實說明情況,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過所在單位及時向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如實說明情況,并有悔改表現的,可以不予追究。
三、我國間諜罪立法修正長遠方向展望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在國際上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9]。如果對我國間諜罪立法按前文所述修改建議進行修改,可以適當拓展目前間諜罪的規制范圍,并有效解決間諜罪規制重點失偏、規制銜接失當等問題,能夠較好地適應新形勢下反間諜工作實際和構建“國家安全體系”政策新需求。但是,長遠來看,要實現間諜罪的科學立法,我們還應思考以下問題:
一是“間諜”一詞的本質含義問題。盡管目前我國大部分刑法學者認為,間諜是指被間諜機構秘密派遣到對象國(地區)從事竊密為主的各類非法諜報活動的人員,又指被對方間諜情報機構暗地里招募而為其服務的本國公民,即間諜既包括派出國人員,也包括對象國公民。但也有學者認為,“間諜是一國為秘密獲取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種情報而派往境外的秘密人員”[10]。此時,站在對象國的角度,間諜被認為是從國(境)外派入的人員。從世界各國立法例分析,大陸法系主要國家對于間諜罪的立法,大部分也肯定了間諜是指從國(境)外派入的人員的觀點,甚至不少國家的間諜罪立法直接肯定了間諜只能是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例如,在法國新刑法典第四卷危害民族、國家及公共安定罪第一編危害國家基本利益罪中,在第一章即對叛國罪與間諜罪予以明確區分。在該法典第411-1條即寫明“第411-2至第411-11條所規定之行為,由法國人或為法國服務之軍人實施的,成立叛國罪;由其他任何人實施的,成立間諜罪”。而其411-2至第411-11條基本涵蓋了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包括向外國交付國家領土、武裝力量之全部或一部或者交付物資罪、通謀外國罪、向外國提供情報罪等。再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29章侵害憲法制度基本原則和國家安全的犯罪中也對背叛國家的活動與間諜活動予以明確區分。其在第275條背叛國家罪中規定:“背叛國家,即俄羅斯聯邦公民從事間諜活動,出賣國家機密,或以其他方式為外國國家、外國組織或其代理人進行危害俄羅斯聯邦外部安全的敵對活動提供幫助”。其在第276條間諜活動罪中規定:“外國公民或無國籍人向外國國家、外國組織或其代理人交付以及為交付而搜集、竊取或保存構成國家機密的情報,以及接受外國情報機構的任務交付或搜集其他情報,以便用來危害俄羅斯聯邦的外部安全的……”。按以上規定,俄羅斯公民從事間諜活動,成立叛國罪,外國公民或無國籍人從事間諜活動,則成立間諜活動罪。另外,即使是二戰戰敗國德國,其在刑法典中也明確區分叛國罪與外患罪。由此來看,間諜更多的是被認為是外國人或無國籍人。而間諜犯罪,更多的也被認為是一種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的犯罪。
二是我國《刑法》中危害國家安全罪打擊對象整體失偏問題。反觀我國《刑法》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立法,更多的是站在打擊我國國籍人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角度上。除明顯打擊我國國籍人員犯背叛國家罪外,我國《刑法》在第103條至105條即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暴亂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后,規定了與境外勾結的加重處罰情節①我國《刑法》第106條規定: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從重處罰。。由此可見以上罪名的打擊目標,仍然是“境內人員”。而依前文所述,我國《刑法》中的間諜罪打擊重點失偏,其打擊目標也并不是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本身。因此可見,我國《刑法》中危害國家安全罪立法現狀,整體呈現出對外國組織、人員等從事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行為打擊力度較弱的特點。
我國間諜罪規制范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1979年《刑法》②因79《刑法》另設有反革命破壞罪,97《刑法》間諜罪中“為敵人指示轟擊目標”被納入該罪。至1997年《刑法》,呈現逐步收窄的趨勢。間諜罪規制范圍收窄,有時代的原因,更多的是為了契合我改革開放基本國策。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擴大,各領域面臨的間諜威脅也逐步增加。對此,習總書記在2014年4月15日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基于我國《刑法》中危害國家安全罪打擊對象整體失偏,長遠來看,應契合“間諜”一詞的本質含義,考慮進一步擴大間諜罪的規制范圍,把其規制重點偏向境外,即偏向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源頭,用間諜罪更好地處置和預防來自境外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危害,進而與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相區分,徹底解決間諜罪與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法條競合的問題,從而更好地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