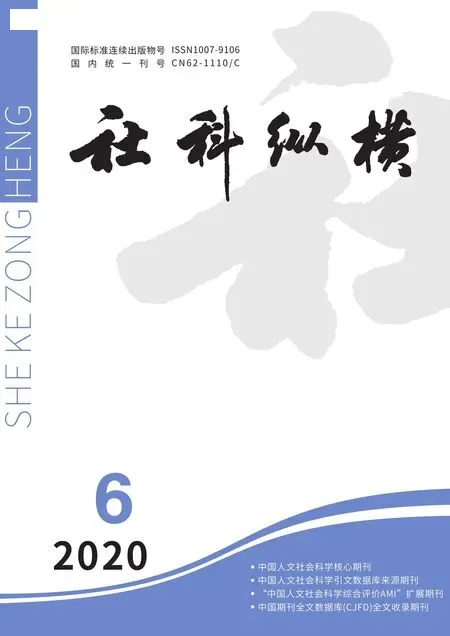“重建”共同體:論“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應對
李俊豐 唐曉春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廣東 廣州 510303)
2020年1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國,對我國社會造成極大影響,高等教育亦不例外。除了實施延遲開學的措施,高校還應盡早開始考慮開學之后課程教學內容如何變動和安排的問題。
其中,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特別有必要就疫情作出回應,對教學內容進行適當修改。高校思政課本來就要求做到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1],強調立足現實和實踐來向大學生闡釋相關內容和理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遍及全國,可以說幾乎所有大學生都被卷挾其中,對疫情有著相當程度的關注、思考,疫情成為一個和高校思政課內容密切相關、給思政課教學提出“新問題”的現實事件。例如,“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概論”課的重要內容之一[2](P244-249),筆者的一名學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且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問題:疫情會否對此目標的實現造成影響。因此,高校思政課對“新冠肺炎”疫情作出回應既有必要性,亦有普遍意義。本文即擬結合筆者所在高校一些大學生反饋的情況和疑問,以“概論”課為中心,就“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高校思政課應如何作出應對等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及其核心
現今的大學生成長于網絡時代,其日常生活已和手機、網絡高度“捆綁”在一起,這意味著他們在獲悉“新冠肺炎”疫情相關情況時渠道較為多樣,讀到的信息也較為多元立體。他們不僅從官方媒體了解疫情的基本情況,也從各種公眾號、微信文章、視頻APP 等處接觸到關于疫區情況、疫情發展、防護措施等等多個方面的同時也是或真或假、良莠不齊的信息。現今的大學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時還是只有幾歲的孩子,對當時的事情并無深刻的認識和記憶,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他們第一次目睹甚至親身參與的全國性重大公共安全危機事件,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和沖擊不容忽視。
“新冠肺炎”疫情涉及到的層面和問題較為繁多,大學生也因個人興趣、經歷等原因而有不同的關注點,因此,從高校思政課如何應對的角度看,則必須找出、抓住“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學生思想所造成的影響之核心,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意識形態引導和教育的工作。而“共同體的撕裂”,則是這樣的一個核心問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對民族主義進行探討時,提出著名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所謂“想象的共同體”,是“一種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根植于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的建構”[3](P17)。換言之,共同體不僅存在于實體意義上,也與人們的主觀認知和認同密切相關。這一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新冠肺炎”疫情為何及如何對大學生的思想造成較大影響。毋庸置疑,在實體意義上,我們的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都構成一個共同體,但對這些共同體的主觀認知有時可能和實體本身并不一致。而“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大影響,便在于影響人們關于各種共同體的主觀認知,讓人們原來心目中所認知的共同體“撕裂”開來。
根據學生反饋的情況,這種“共同體的撕裂”主要體現如下幾個方面。
(一)地域方面
為了控制疫情蔓延,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主要城市均采取了非常嚴格的封城措施,但由于事出突然,相關措施沒有完全跟上,導致一些地域矛盾出現,例如,一些湖北省以外的酒店不愿意接待湖北籍人士住宿,網絡上出現一些針對湖北人的不具善意的聲音,有些湖北人則覺得自己當了其他地方的“馬前卒”之類。此外,由于疫情嚴峻,不少地方,特別是如村、街道等基層單位,采取了一些較為極端化的措施,例如貼出一些被網民形容為“硬核”的防疫標語,甚至把道路挖斷,等等。
疫情期間,這類事件得到了較多的報道,大學生們幾乎不可能對此毫不留意。不少學生反映說,此前他們所感知的地域差異主要是一些文化、習俗方面的,或是帶有善意的“開玩笑”性質的,例如湯圓究竟應該是咸的還是甜的、廣東人吃福建人之類,這次疫情卻讓他們第一次意識到,不同地方之間及其人群之間的差異真實存在①。
從整體來看,不同地區、民族的人們對中華文化有非常高的認同度和歸屬感;從國家結構形式的角度看,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中央對地方具有統一領導權,各級地方均應服從中央的領導。因此,在今天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里,“中國”“中國人”這兩個概念往往被感知、理解為是一個成分單一、恒定的“共同體”。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造就了一個較為極端、嚴重的情景,讓人們直觀上感知到一些他們此前沒有留意到的情況:對疾病的畏懼轉化為對疫情地區人員的畏懼和戒備,疫情地區似乎成為一個和其他地區有所不同甚至對立起來的名詞。這樣的一種思想上的沖擊,在大學生身上也可見到。
(二)群體方面
這里所說的群體方面是指:不同身份、階層的群體就“新冠肺炎”疫情形成各種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看法、意見和行為,這些看法、意見和行為通過各種媒介途徑被包括大學生在內的人們所感知、關注,讓人們意識到各個群體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例如,大學生非常關注2020年1月份網絡上“學者為了發表論文隱瞞‘人傳人’”的討論,以及科學技術部發文要求科研人員“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的事件[4]。不少學生表示,如果學者“為了論文而隱瞞事實”一事屬實,他們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再如,很多學生關心疫情初期武漢的地方官員為什么不及時公開相關信息;還有的學生比較關心和醫生有關的新聞,包括廣州某位醫護人員以賣口罩為名詐騙、湖北一些小區不許下班的醫護人員回家,等等。
大學生關注這些新聞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們從中感受到了某種“共同體的撕裂”。在大學生們的一般認知里,在這些新聞里發生摩擦甚至沖突的不同群體,理應是屬于同一“陣營”,是應該共同抗“疫”的:學者、官員理應以人民的利益為先,醫護人員和其他老百姓理應守望相助。那為什么有些學者、官員、醫護人員、普通人還會做出一些有悖于這種“共同體”的行為呢?不少大學生迫切地希望獲得答案。
(三)個人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存在于網絡世界,也明顯影響到人們實際的生活和行為方式,大學生身處其中,其個人感受也相當強烈,不容忽視。
“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大特點,是潛伏期較長,且可能存在癥狀輕微的病人,這讓病毒顯得防不勝防,也讓人們只能保持對他人的高度戒備。于是,本來對“人群”非常熟悉,以人際交往為社會生活基本要素的人們,此時不得不盡量保持“個體化”的狀態以保證自身的安全。疫情開始后一些媒體報道的“女朋友咳嗽遭男朋友舉報”“父母不愿帶口罩女兒報警”之類的新聞,便是這種“個體化”的反映。
也正是從這些新聞可見,這種“個體化”意味著個人迫于疫情壓力而暫時從其所在的共同體中退出,讓共同體在某種意義上被“撕裂”開來,就算共同體屬于“家族”這種親密性非常強的,也是如此。拜年等傳統風俗對于維系家族這個對中國人而言最重要的共同體具有深遠意義,但這些風俗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都被禁止。這種情況發生在本來應是家人團聚和親密接觸的春節期間,更是造成了一種極大的反差,對人們的感受和情緒造成較大的沖擊。
這種“共同體的撕裂”不僅發生在家族層面。一位大學生說,有一天他看見她母親碰巧在在走廊上遇到一位鄰居并聊了起來,他當時非常擔心,等了一分鐘左右看母親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終于忍不住,找了個借口把母親拉走了。另一位大學生如此描述她某次上街時的感受:“從來沒見過這樣空蕩蕩的廣州……遇到迎面而來的行人,大家都自覺地互相避讓。停共享單車時,余光掃到街角一個行人向我走來,我明顯感覺我的身體下意識地向反方向縮了一下,盡管他離我足有3、4 米遠。”概言之,當人們因自我保護的需要而變得“個體化”時,其本來所處和熟悉的各種共同體均在相當程度上被“拆解”和“撕裂”,而大學生也親身體驗著這種經歷。
當然,在今天,包括大學生在內的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高度認可,也具有對祖國和中華民族的高度認同感,這不會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改變。不過,疫情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也是客觀存在的,對此我們不能予以忽視。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
(一)直面“新冠”疫情的事實和影響
對于“新冠肺炎”疫情,高校思政課教學不應避而不談,也不應輕描淡寫、避重就輕,而應該直面之,在此基礎上正確闡釋之。
1.直面“新冠肺炎”疫情符合高校思政課的教學要求
必須承認的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們國家和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高校思政課如要直面“新冠肺炎”疫情,便相當于要直面這些問題,這也是部分思政課教師覺得“棘手”的地方:在他們看來,“新冠肺炎”疫情不夠“正面”,很難講好。
但必須認識到的是,高校思政課的改革創新,必須堅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3]。“‘正面宣傳為主’和注重建設性并不是……只講建設而不講批判。正面宣傳如果不與反面批判相結合,就不能真正發揮正面宣傳的主導性作用。”[5]只有直面問題,特別是直面一些錯誤的做法,對其展開有理有據的理論批判,才能更好地向大學生揭示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確性,才能保證高校思政課的正面教育真正行之有效。
直面問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前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黨和國家正是這樣做的。例如,就李文亮醫生一事,黨和國家并沒有予以無視和忽略,而是作出了適當的反思,“李醫生的遭遇,讓人們看到了阻塞這種預警的驚天后果,看到了輕率處理無主觀惡意的言論,可能比虛假信息本身帶來的危害要大得多”[6],并及時作出了由國家監察委員會派調查組進行調查等措施。因此,如果高校思政課教師在教學中不愿直面“新冠肺炎”疫情,反而有悖于黨和國家的正確做法,有悖于高校思政課的正確導向,不利于大學生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2.直面“新冠肺炎”疫情才能保證高校思政課的教學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是當下中國的重要現實,如果不能直面之,便可能導致高校思政課不僅顯得缺乏現實關懷,也容易變得缺乏說服力,從而極大地削弱了高校思政課所應具有的教學效果。
如上文所述,大學生較多關注“新冠”疫情,思考相關的涉及國家、社會、法律、文化等諸多層面的問題,而這些層面又是高校思政課必然涉及到的。仍以“概論”課為例,“新冠肺炎”疫情在諸多方面和該課程的教學內容存在關聯,故大學生們很自然會將相關課程內容和“新冠肺炎”疫情關聯起來進行思考。例如:社會保障、人民健康是民生問題的重要方面[2](P231-233),“新冠肺炎”疫情與此密切相關;“新冠肺炎”疫情可引發人們對建設生態文明進行反思——有學生認為,過往對環境生態的重視主要還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故捕食野生動物之類的一些看上去似乎不會直接影響人類利益的層面便常被忽略了,“新冠肺炎”疫情則對此敲響了警鐘;有的學生關注香港、澳門地區如何應對疫情,在疫情的背景下當地人對內地的認知是否發生變化,這就涉及到“一國兩制、祖國統一”的課程內容[2](P219-223),等等。換言之,在教學過程中,很難完全“避開”“新冠肺炎”疫情這一事實。只有正確地、恰當地談及“新冠肺炎”疫情,才能避免讓相關教學顯得空洞無物,才能更好地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重視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學理分析
高校思政課教學必須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1]。
“思想政治理論課重在講理,以理服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就要善于用學術講政治,以透徹的學理分析回應學生,以徹底的思想理論說服學生,用真理的強大力量引導學生,以深厚的理論功底贏得學生。”[7]如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如果教師不能通過適當、精辟的理論將這些問題闡釋清楚,僅僅采取簡單的“灌輸”“喊口號”的方式來教學,便可能反過來削弱高校思政課的說服力。這就要求思政課教師必須加強教學中的學理分析,而不能僅僅強調政治性,更不能以政治性為名將思政課變成純粹的“雞湯”課。
具體而言,在教學實踐中應當注意如下兩個方面。其一,教師在講課時必須將學理貫穿在授課內容中,保證講授的內容和思想有足夠的理論支撐,以盡量做到有理有據地、有說服力地回應學生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和疑問。例如,在講述“建設美麗中國”時,似有必要超越“列舉我國近年生態環境建設的成就”這種比較淺層次的授課思路,適當加入一些“關于人和自然”的哲學思考之類的內容;在回應學生所感受到的“共同體的撕裂”時,則必須借鑒共同體相關理論,幫助學生理解這種“撕裂”的背后機理,引導“重建”共同體。其二,不同層次、類型的學校均應重視思政課的學理性。有種觀點認為,一些非重點高校的學生的理論水平相對較低,他們對學理性較強的內容較難接受。雖然不同學校的學生具體情況確實不盡相同,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卻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有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都迫切希望對這一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其生活的事件能得到一個深入的、有說服力的解釋,即便對于那些所謂層次較低的大學生而言,亦是如此。也許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確實較難理解一些抽象的理論,覺得這些理論枯燥乏味,但在親身經歷的影響下,他們反而可能被激發出“好奇心”,從而更愿意去了解、學習相關理論。不可否認,這對高校思政課教師提出了一個比較高的要求,但如果應對得當,“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成為一個促進高校思政課變得更符合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的要求的契機。
(三)以“重建”共同體為核心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學生思想影響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于“共同體的撕裂”,故在向大學生闡釋“新冠肺炎”疫情時,有必要借鑒“共同體”相關理論,以實現疫情過后高校思政課教學的一個重要目標:如何引導他們把主觀認知中的共同體“重建”起來?可考慮的一個思路,是回到并借鑒安德森的理論:
其一,承認“共同體的撕裂”確實存在,引導學生理解其背后機理。
上文述及的“共同體的撕裂”,是大學生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確切感受到的,如果直接否認或否定學生們的這種親身感受,對高校思政課的教育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關鍵在于,應如何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種“共同體的撕裂”。
安德森在論述“想象的共同體”時,特別談及報紙,他指出,報紙是一種“文化產物”,具有“深深的虛擬想象性質”[8](P30)。在今天,對于大學生這一代年輕人而言,報紙的作用和影響主要由網絡媒介所繼承,同時,網絡媒介也繼承了報紙的“虛擬想象性質”。一方面,網絡媒介所呈現的信息是已經被選擇過的:不同性質、不同立場的媒介——例如各種微信公眾號——都在呈現自身想呈現的信息,這些信息之間觀點、角度、立場、感情互不相同甚至相互沖突,其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另一方面,發達的網絡媒介讓這些信息并置在一起而被呈現出來,從而很容易讓讀者強烈地感覺到,這些事情同時地、密集地、普遍地發生著。由此,讀者們接受信息時的感受被夸大,通過信息所獲得的認識和理解也容易變得相互沖突。從這一角度看,今天大學生所感受到的“共同體的撕裂”,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媒介的“虛擬想象性質”的產物。
其二,引導大學生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雖然存在上文述及的一些“共同體的撕裂”的現象,但與此同時,“中國”“中國人”共同體的特征也在此過程中更清晰地顯示出來。
根據安德森的理論,“同時性的經驗”對于暗示共同體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唱國歌就是一個典型的“齊唱”意象[8](P139)。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全國人民絕大部分都能做到按照國家的要求而行為,這種全國性的“同時性經驗”以往頗為少見,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卻為全國的人們所共享。也正是這種“同時性經驗”,能讓全國的人們都認識到,每個中國人都身處“中國人”這個共同體當中,每個中國人都和“中國”休戚與共,每個中國人的行為也都和“中國”密切相關。我們常說“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一大表現,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還看到了,“集中力量辦大事”還體現在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以及以此為指導的行動中,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其三,引導大學生看到,“新冠肺炎”疫情能讓人們對超越國家、民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更深層的認識和認同。
自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迅速成為國際上的共識。但必須承認的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等諸多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差異,某一國家、民族的人很難真正體驗、理解并由此認同另一國家、民族的人們的生命體驗,這恰是不同國家、民族的人們容易產生分歧甚至沖突的原因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一是能讓人們清晰認識到在全球化語境下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很難獨善其身,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真正的、重大的現實意義;二是讓抗擊疫情成為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行動,反映出讓全人類聯合起來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并不是虛幻的,而是切實可行的。更重要的是,當“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到多個國家的時候,人們得以通過“疾病”這一人類的普遍性經驗來感受其他國家、民族的人們的生命體驗——正如疫情下的中國人對日本“鉆石公主”號郵輪里被隔離的游客能感同身受。由此,人們得以真正地理解為何說人類的命運是休戚與共的,為何說全人類的的確確構成一個“共同體”。
總言之,“共同體的撕裂”其實并不可怕,當思政課教師認識到這一關鍵時,反而可以有的放矢地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導他們認識、思考和分析上述“中國”“中國人”共同體的特征、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和認同等問題,從而在思想觀念中把共同體“重建”起來。
三、結語
研究者和一線教師一般認為,高校思政課具有理論性較強、相比起其他課程較難吸引學生興趣的特點,故必須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用現實問題充實理論性內容,以提升思政課的教學效果。由此角度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有助于上好高校思政課的現實素材。如前所述,對于幾乎所有大學生而言,這次疫情都是一件就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件,這一特點是以往思政課教師所尋找、展示的素材都不具有的。只要引導得當,大學生通過“新冠肺炎”疫情既能更真切、深刻地認識到,課本上討論的看似抽象、枯燥的理論知識,實際上和國家、民族以及每一個個人均密切相關,也能就我們的國家、社會、文化、制度等諸多方面產生更深刻的思考;只要引導得當,“新冠”疫情也能成為一個有助于大學生加深對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思考和認同的契機,高校思政課教師理應擔當起這種引導責任。
注釋:
①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地域人群之間的差異也可歸入下文討論的“群體方面”。
——評《新時代高校思政課的打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