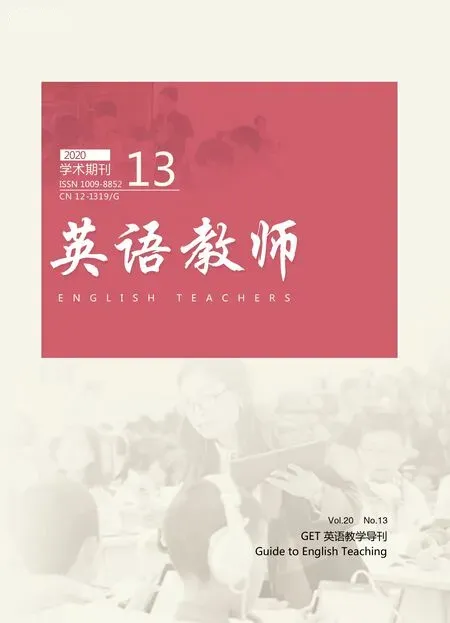從組合、聚合關系角度看翻譯的歸化現象
——以金莉、秦亞青翻譯的《一小時的故事》為例
周秋璐 祁文慧
引言
翻譯是指用一種語言將另一種語言的意義準確、全面地表達出來,是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與闡釋。而組合關系與聚合關系作為符號系統的核心,自然與整個翻譯過程緊密相連。譯者作為連接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一方面需要理解作者的意圖,內化作品內容;另一方面也需要揣摩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需求,使譯文貼合其語言文化表達習慣,讓他們體會到最佳的語境效果,使譯文達到歸化的效果(陳心妍、邵華 2019;章璐、王富銀 2019;伍靜、肖飛 2019;祝一舒 2018)。理解文章內容其實對許多譯者而言并非難事,但他們在表達時往往受限于原文字的桎梏,致使作品“充其量只能成為剝制的標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鳥,徒有形貌,沒有飛翔”(余光中 1984;丁婉寧、邵華,等 2019;周方琴、王富銀 2019)。
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是語言結構系統中的兩種根本關系,它們最早源于現代語言學之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的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祝一舒 2018;馮欣、劉祥海,等 2019;薛香云、王富銀 2019;潘云天、肖飛 2019)。組合關系,顧名思義,就是語言符號互相組合起來形成的關系,是以語言線性特征為基礎,排列在語言線條上的一種橫向關系。而聚合關系則是在話語之外,可能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且功能相同的單位之間的垂直關系(李金艷 2013;金瑞、邵華 2019:113)。以a white horse和a black horse為例,white和black分別與horse存在修飾與被修飾的關系,屬于橫向組合關系;而white和a black horse中的black形成對比,且可以相互替換,這兩者屬于縱向聚合關系。
《一小時的故事》由凱特·肖邦(Kate Chopin)所著,全篇雖僅一千詞左右,但用詞簡練恰當,句子結構多樣化,句子順序編排適宜,充分體現了英語的表達習慣。下面將以組合、聚合關系理論為基礎,以金莉、秦亞青(1995)翻譯的《一小時的故事》譯本為例,探析翻譯過程中選詞、組句的技巧方法。
一、橫向組合關系與語序的排列
組合關系有四個特點:序列性(組合體內各單位必須按一定次序排列)、整體性(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構成的復合體)、制約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影響)、擴展性(組合體內的各單位和組合體本身都可以擴展)(徐盛桓 1983;呂鵬、張弛,等2019;鄭長明 2019;金瑞、邵華 2019:164)。因此,言語里并不存在絕對自由的詞語組合,詞與詞的組合往往會受到語言邏輯、表達習慣、語言環境、語法規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只有按照組合關系將詞語進行合理排序,才能得出貼合目的語讀者表達習慣且富有邏輯的譯文。
【例 1】源文本:Knowing that Mrs.Mallard was afflicted with a heart trouble,great care was taken to break to her as gently as possible the news of her husband’s death.
譯文:大家都知道馬拉德夫人的心臟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訊告訴她時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
中英文表達習慣存在明顯差異,中文傾向使用有靈句(即以人為主語),而英語則更傾向使用無靈句(即以物作主語)(吉鑫、王富銀 2018;吉鑫、肖飛2019;李榮榮、邵華 2019;祝一舒 2018)。由于長期受語言環境的影響,中國一直信奉人本主義的儒家學說,更注重人的主觀感受,因而在表達時大多以人為句子的主體;而西方國家則強調理性與客觀的邏輯分析,在表達時注重以物為句子的主體。例1中,譯者深悉中英文表達習慣,在漢譯過程中,給源文本中的great care was taken to增添了主語“大家”,通過改被動為主動,增添主語的方式,使譯文更加貼合目的語讀者的表達習慣。
【例 2】源文本:Into this she sank,pressed down by a physical exhaustion that haunted her body and seemed to reach into her soul.
譯文:全身的精疲力竭,似乎已浸透到她的心靈深處,她一屁股坐了下來。
在語言邏輯方面,中文語序一般比較固定,定語一般置于名詞之前,但英語語序更為自由,定語可前置可后置,所以在翻譯時,一定要考慮到不同語言的不同語法特點,根據定語的長度將其進行合適的位置排列。例2中,a physical exhaustion that haunted her body and seemed to reach into her soul從英語角度來看,將長定語后置,完全合乎英文表達習慣,但在翻譯成中文時,要注意中文的定語一般置于名詞之前,所以在譯文中將定語分成兩個部分,前部分haunted her body采用了定語前置的方式,譯成“全身的精疲力竭”,又將后面的seemed to reach into her soul另起一句,譯成“似乎已浸透到她的心靈深處”。將定語從句拆分為簡短的句子表述,更有利于目的語讀者的理解。
由此,在譯文語序的編排中,掌握好中西方不同文化表達習慣固然重要,仔細鉆研上下文語境,及時總結不同的排列規則也必不可少。只有在掌握組合關系的基礎上不斷進行調整,才能熟練掌握語序排列方法,準確、高效地產出高質量的譯文。
二、縱向聚合關系與詞語的選擇
聚合關系有類型性(不同特點、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聚合體)和可置換性(即同一聚合體內的各個體可以在組合體內相互置換)兩個特點(徐盛桓 1983;劉晶晶、邵華 2019)。因此,要實現翻譯的歸化,勢必要培養發散思維,充分掌握各個詞匯的不同釋義、不同性質及盡可能多的同義替換詞,沖破源語言的桎梏,從而尋找貼合語境的最佳譯詞。
【例 3】源文本:She did not hear the story as many women have heard the same,with a paralyzed inability to accept its significance.
譯文:要是別的婦女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是手足無措,無法接受現實,她可不是這樣。
在《朗文現代漢語詞典》中,significance意為“事件的重要性”及“單詞的意義”,但在例3的語境中,以上兩種意義似乎都不適用。根據上下文可以推測出,別的婦女肯定難以接受其丈夫去世的噩耗這一現實,所以在這里將significance引申為“事實”更加貼切源文本語境。
例 4:源文本:When she abandoned herself a little whispered word escaped her slightly parted lips.
譯文:當她放松自己時,從微弱的嘴唇間溜出了悄悄的聲音。
例4源文本中abandon和escape的使用甚是巧妙。在《朗文現代漢語詞典》中,abandon意為“離開某人或某地”“停止做某事”,這里abandon herself不能翻譯成“放棄自己”,根據上下文可以看出,女主是在極其放松的情況下,情不自禁地發出的聲音,所以這里譯成“放松自己”最貼切。而escape主要用來修飾氣體、液體、聲音等事物,所以當搭配的賓語不一樣時,有不同的譯法。考慮到源文中該詞修飾的是“悄悄的聲音”,所以“溜”一詞既形象、貼切地給予了“聲音”一定的生命力,又顯示出了聲音的輕微,嘴唇的微弱狀態。
【例 5】源文本:In the street below a peddler was crying his wares.
譯文:下面街上有個小販在吆喝著他的貨色。
cry一詞最常見的意思是“哭”,但在《朗文現代漢語詞典》中,其亦可表示為“大聲叫喊”。例5中cry一詞的發出者是小販,在整個語境中,其意為小販在賣貨品時發出的聲音。若在這里使用“大聲叫喊”,雖意義上能夠貼合,但并不簡明。“吆喝”一詞則彌補了這一不足,其本義便是“大聲叫喊”,而且專門用來形容小販賣貨似的叫喊聲,用在這里既貼合源文本,又簡明扼要,十分恰當。
【例 6】源文本:The notes of a distant song which someone was singing reached her faintly,and countless sparrows were twittering in the eaves.
譯文:遠處傳來了什么人的微弱歌聲;屋檐下,數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
twitter一詞主要用來形容鳥短而響亮的聲音,但由于鳥的種類各異,其叫聲也有所不同,所以在不同語境中會選用不一樣的動詞修飾。在例6中,twitter的發出者是麻雀,其叫聲特點為“嘁嘁喳喳”,所以將twitter譯為“嘁嘁喳喳”更貼合源文本語境,且將麻雀的叫聲更形象、生動地呈現了出來。
弗斯(Firth 1957)說:“每一個詞用在新的語境中就是一個新詞。”所以在翻譯時要為源文本中的詞語找到一個合適的目的語釋義,必須要反復斟酌上下文語境,根據其前后并列關系推敲該詞的含義,根據上下文語境猜測語言環境(張思、邵華 2019),同時也要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適當進行補充說明。只有充分利用源語言的聚合關系,不斷嘗試替換,才能實現對源語言的最佳翻譯。
結語
橫向組合關系與縱向聚合關系是語言符號系統的核心。在漢英或者英漢翻譯中只有通過熟悉不同語言的用語習慣和文化背景,仔細推敲上下文語境,不斷嘗試斟酌,才能進行合理的語序排列與詞語選擇,從而使譯文符合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規范和表達習慣,實現翻譯的歸化。翻譯中的選詞排序方式靈活多樣,使用歸化策略時出現的問題也是不勝枚舉,故還需進一步探索、歸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