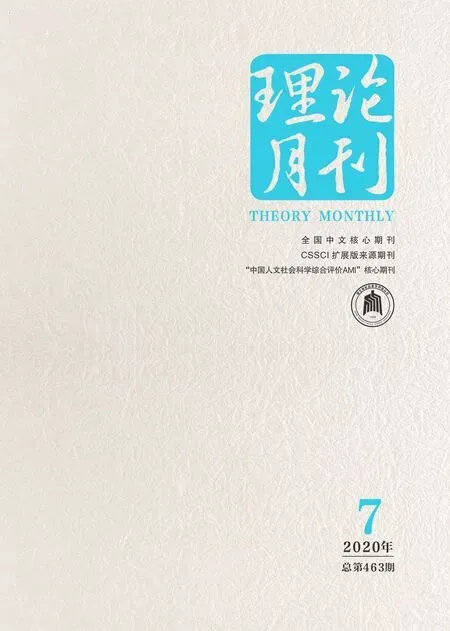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綱領性文獻
——紀念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發表40周年
□胡 偉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 200233)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極為重要的講話,史稱“8·18講話”,深刻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尤其是高度凝練了無產階級政黨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從制度根源上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敏銳指出了我國政治制度領域存在的種種弊端及其產生的原因,精辟闡述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目的、意義和主要內容,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系統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建設如何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思想。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講話。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1983年7月1日《鄧小平文選(1975—1982)》(1994年10月再版時改為《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公開發行,收錄了這篇重要講話。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通欄標題予以發表。1987年7月1日,值建黨66周年之際,《人民日報》頭版整版再次隆重刊發這篇講話,并配發社論《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人民日報》兩次在頭版刊登同一篇講話,足見其重要性非同尋常。隨后,《光明日報》等50多家報刊全文轉載并配發社論或學習文章,《紅旗》雜志于1987年第13期發表社論《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1](p34)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年10月—2019年9月)記述:“8月18日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對現行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必須進行改革。”[2]由此可見,這篇講話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新時期我國推進改革開放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在2019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特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黨孜孜以求的宏偉目標。自成立以來,我們黨就團結帶領人民為此進行了不懈奮斗。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深化,我們黨對制度建設的認識越來越深入。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就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3]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正是基于鄧小平的這篇綱領性文獻。雖然鄧小平并沒有使用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概念,但其深邃的理論洞見恰恰構成了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寶貴思想財富。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篇講話得到如此多的關注并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非常罕見,彌足珍貴,在鄧小平諸多講話中也很少見。“8·18講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不可多得的經典文獻,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一座豐碑。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發表40周年之際,在中國共產黨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重溫鄧小平的這篇光輝文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深刻認識和反思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弊端
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而言之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很長時期里在實踐上是懸而未決的。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必須實行民主共和制,并提出“社會共和國”的政體思想。列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原則。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家長制”“一言堂”,形成了高度集權的體制,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巨大危害。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也未能走出這一窠臼,一度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深刻反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自身的慘痛教訓,《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代表了這一反思的最高理論成果。
作為對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經驗體會最為深刻的領導人之一,鄧小平對傳統社會主義所存在的體制性弊端也認識得最為透徹。在這篇講話中,他以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尖銳地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4](p327)尤其是“8·18講話”對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的剖析,至今讀來仍入木三分。他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4](p328-329)
如何處理民主與集中、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是長期困擾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關鍵的體制性問題。從“蘇聯模式”開始,就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后來被實踐證明是各國社會主義的制度頑癥。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曾飽受權力過分集中之苦,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也曾提出過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這涉及地方分權的問題,但總體上對制度上的分權缺乏認識,實踐上還是形成了高度集權的體制。歷史教訓告訴人們,對于社會主義制度而言,問題不是集中太少或民主太多,而是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弊端不是來自分權,而是高度集權。
對此,“8·18講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事業、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4](p328,329)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又與家長制作風相互助長,“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由此造成“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黨內民主,什么社會主義民主。”[4](p329-331)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講話指出:縱觀社會主義從誕生到現在的歷史過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后,不斷探索這個問題,也發生了嚴重曲折。[5](p91)這段話,正是沿著上述“8·18講話”的思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高度總結,進一步印證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科學性和深刻性。追根溯源,中國共產黨自十八屆三中全會起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就緣起于鄧小平的這篇講話。
正是基于對以往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制度弊端的深切洞察,鄧小平在“8·18講話”中明確提出必須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進行改革。他意味深長地指出:“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4](p333)后來,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6](p237)這些論斷,可謂高瞻遠矚,高屋建瓴,迄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對于當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依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總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必須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雖然40年的時間帶來了時代變遷,但中國共產黨強烈的問題意識不能變。從這個意義上說,“8·18講話”不僅是20世紀80年代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也是當前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綱領性文獻。
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光輝文獻的理論價值,不僅是系統分析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對此進行改革的基本措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率先闡述了制度與人孰輕孰重的問題,明確提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要論斷。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發展。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博大精深,但以往沒有直接論證過人和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關系和地位。對此,鄧小平在“8·18講話”中鞭辟入里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4](p333)
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是“8·18講話”留給后人最偉大的思想遺產之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被此后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正式文件所反復引用,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制高點。其中最具有學理價值的是,鄧小平畫龍點睛地對人類政治學千百年來研究的一個主題——即“好人”與“好的制度”哪一個更重要,做了深入淺出的回答。從儒家的內圣外王、德治仁政,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哲學王”及其對政治至善的追求,無不崇尚的是“好人”政治、“賢能”政治或圣賢之道,但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幻想。直到近代以后,政治思想才開始發生轉向,出現了恩格斯所概括的“法學世界觀”,把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提到了應有的地位和高度[7](p22-26)。但是,與以往思想家的煩瑣論證不同,鄧小平“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的概括,言簡意賅地把制度與人的關系揭示得淋漓盡致,這樣的話語表述堪稱經典,也體現了鄧小平一貫生動、務實的語言風格。
這一概括,對于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建設極為重要。以往的政治理論都強調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構成的,特別強調理想信念、思想覺悟和黨性修養的重要性,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對于制度建設往往缺乏足夠的關注,把重點放在了人格塑造而非制度構建上,造成人和制度關系上的畸輕畸重,甚至把兩者的重要性給弄顛倒了,這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重大失誤和嚴重挫折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問題的癥結不是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好,而是制度不健全。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要正確理解這一歷史結論,要真正記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沉痛教訓,就必須深入領會“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的思想深邃性,搞懂“好人”“壞人”與“好的制度”“不好的制度”孰輕孰重,從而進一步提高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改革總目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
歷史反復揭示,只有構建好的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究竟在全局上是依靠好人還是依靠好的制度,究竟從根本上是以思想為主還是以制度為主來進行國家治理,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走向現代化的分水嶺。“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訓也說明,靠“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并不能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政治和美好的社會。正如鄧小平在“8·18講話”中所說的:“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4](p328,330)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核心問題就在于制度建設薄弱,尤其是缺乏對黨的領袖的制度性約束,缺乏對于最高決策的糾錯機制。
殷鑒不遠,不可失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溫《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重要講話,正確把握制度與人的辯證關系,對于當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仍具有綱領性指導意義。在“8·18講話”過去12年后,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6](p372)可見,制度建設是貫穿鄧小平理論的主線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旨所在。對此,習近平曾說:“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我們黨不斷思考應當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8](p104-105)
知易行難,能夠認識到的問題不一定都能夠做到。然而,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特別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候,能夠提出這樣的真知灼見也并非易事。那么,如果能夠在實踐中真正貫徹這一真知灼見,在國家治理中正確處理“好人”與“好的制度”的辯證關系,做到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有機統一,達成知行合一,則更是善莫大焉。
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僅揭示了制度建設的極端重要性,而且給我國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這是對黨和國家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所做的質的規定性,也闡明了我國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的現代化方向,進而言之也指明了塑造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向。
在不少人看來,鄧小平理論主要是關于經濟建設的,特別是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理論突破。實際上,鄧小平在政治建設上也是很有見地的,尤其是他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思想也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意義同樣重大。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3月,鄧小平就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4](p168)在“8·18講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并強調“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4](p322-323)。鄧小平的這一觀點,不僅把民主政治作為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高屋建瓴地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從經濟、政治和人才三個方面進行了創新性界定,把民主政治建設提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議事日程,這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蘊。
民主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中高揚的一面旗幟。但是在奪取了全國政權以后,能否不忘初心,把民主政治落到實處,不僅關系到黨的旗幟是否改變顏色,也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如前所述,社會主義運動在國際上之所以遭受嚴重挫折,一個主要原因是民主政治滯后、黨內形成“家長制”“一言堂”局面。正如“8·18講話”所披露的:“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制還沒有成為嚴格的制度。”[4](p328,330)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鄧小平在1985年又進一步概括說:“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6](p115)
鄧小平不僅把民主政治提上了現代化建設的議程,而且把民主和法制有機統一起來,他在“8·18講話”中精辟地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許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因此,早在1978年12月13日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基調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鄧小平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4](p146)
不言而喻,民主和法治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杠桿,兩者密不可分。沒有法治,民主就沒有保障;沒有民主,法治就會迷失方向。在現代民主理論中,法治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不存在沒有法治的民主。沒有法治,只能是多數人的暴政、民粹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而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鄧小平講得很清楚:“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6](p189,224)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教訓來看,沒有民主的法治,只能是中國歷史上法家所主張的“法治”,即法、術、勢三位一體,法治與權術糾合在一起,把民眾變成法的奴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法治”實際上就是君主的個人專斷亦即“人治”,成為專制主義的工具。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過程,經受了三落三起的極為復雜的嚴酷政治考驗,不僅熟知黨的歷史,親歷和參與了許多重大事件和決策過程,有治黨治國治軍的全面經驗,而且有著不同尋常的寬廣的國際視野,從早年出國勤工儉學到后來親身參加中蘇論戰,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親身感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洞悉深刻,這無論在中共領導人還是外國共產黨領導人當中,都十分難得。正是豐富的政治歷程、非凡的領導經驗和坎坷的人生起伏,才使他能夠做出比其他前輩和同輩領導人更為深刻的理論總結,特別是把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只有使國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才能切實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制度建設不是隨意的、盲目的,而是有明確方向的,這一方向就是民主和法治;同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不是隨意的、盲目的,也必須有明確方向的,這一方向同樣是民主和法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歷程,我國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建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還不能完全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必須進一步補短板,不斷完善民主政治的各項制度,深刻認識民主法治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極端重要性和質的規定性。這是“8·18講話”的思想精髓所在。
以制度建設肅清封建主義殘余的影響
綜上所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不朽文獻,體現了制度為本、問題導向、民主取向,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依然具有綱領性的指導意義。其中一個重要的邏輯前提和結果,就是要從制度建設的高度上肅清封建主義殘余的影響,這在講話中占了很大篇幅,也是其亮點之一。
“8·18講話”不僅對傳統社會主義體制所存在的弊端進行了清晰的概括,還深入分析了這些弊端產生的歷史原因。針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長期存在且危害十分嚴重的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等現象,鄧小平指出:“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4](p329)從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遺產的雙重視角對黨和國家的制度弊端進行分析,是極具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由于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政權都是在相對落后的國家中建立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擺脫這些落后國家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封建主義政治文化傳統的不良影響。如果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主要問題是打碎資本主義舊的國家機器;而對于這些落后國家而言,本來就缺少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歷,也沒有資本主義的歷史傳統,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危險更多的是來自封建主義的腐朽政治文化。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這方面的教訓都十分深刻。尤其是中國有著數千年的專制主義文化傳統,形成了十分成熟完備的封建政治文化,盡管經歷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依然根深蒂固,很難消弭。正像鄧小平在講話中所說的:“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4](p335)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8·18講話”首先關注的是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問題,提出要“要劃清社會主義同封建主義的界限”。針對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官僚主義,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弊端,鄧小平分析說:“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封建主義的殘余影響當然不止這些。如社會關系中殘存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系和干群關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經濟領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農’式的體制和作風;片面強調經濟工作中的地區、部門的行政劃分和管轄,以至畫地為牢,以鄰為壑……;文化領域中的專制主義作風;……對外關系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觀念來說,‘文化大革命’中,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一人倒霉,株連九族,這類情況曾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甚至現在,任人唯親、任人唯派的惡劣作風,在有些地區、有些部門、有些單位,還沒有得到糾正。一些干部利用職權,非法安排家屬親友進城、就業、提干等現象還很不少。”[4](p334-335)
鄧小平的上述分析,可謂十分精辟、中肯、到位,以至40年過去了,至今讀來仍不陌生,甚至有些問題還愈演愈烈。需要反思的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思想理論工作,長期以來的重點是抵御資產階級或西方文化的侵蝕,但對封建主義缺乏應有的批判,特別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治理國家的思想資源,甚至形成了一股文化復古主義的反現代化思潮。就此而言,“8·18講話”不啻為一支清醒劑,警鐘長鳴。一方面,鄧小平提出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另一方面他對封建主義殘余的影響予以更大的警惕,甚至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上。正像講話所指出的:“對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當然也要采取科學的態度。前些時候解放軍為了進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興無滅資’的口號,總政治部文件我是看過的,當時沒有感覺到有什么問題。現在看來,這個老口號不夠全面,也不很準確。有些同志因為沒有充分地調查和分析,把我們現行的一些有利于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就不對了。”[4](p338)
應當認識到,資本主義是對封建主義的否定,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在缺乏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中國,直接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跳躍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進程很容易造成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融合。因此,雖然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制度既要“反資”也要“反封”,但封建主義腐朽文化的危害通常更大,很多封建政治文化往往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借尸還魂,迷惑性很強。在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認為是“右”,而堅持傳統那一套被稱為“左”,并且長期形成了“寧左勿右”的傾向。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但一些人對不走“邪路”津津樂道,而對不走“老路”卻避而不談,問題也在于此。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振聾發聵地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p375)這一精辟論斷余音繞梁,同樣適用于“反資”與“反封”的問題。
那么,如何才能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呢?“8·18講話”也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4](p336)由此,他才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問題,提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命題,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課題。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鄧小平所痛感的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個人獨斷專行等現象,也才能從根本上鏟除封建主義留下的沉疴頑疾。
前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幾個方面的主要思想,一以貫之、相互聯系,構成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典范。總的來說,封建主義思想傳統是前現代的產物,其政治文化總體上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相悖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正確辨明傳統與現代的關系。現代化意味著要批判性繼承傳統,但決不能以“前現代性”去否定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更不能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在當前各種思潮和觀點魚龍混雜、魚目混珠的情況下,重溫鄧小平的“8·18講話”,恪守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可以保持更為清醒的頭腦,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厘定正確的方向。這是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發表40周年最真誠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