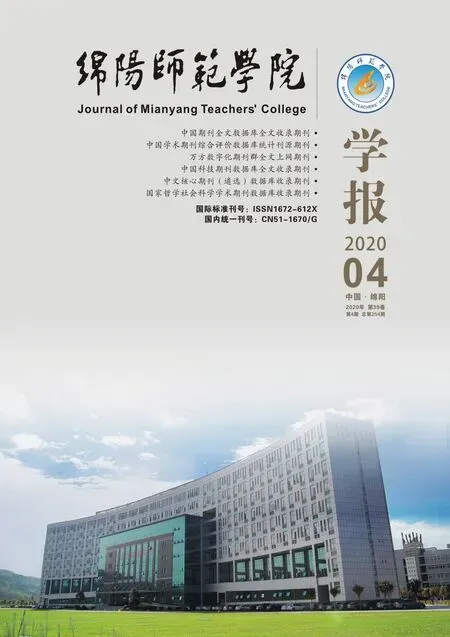月亮、牢籠和人的“異化”
——許鞍華版《金鎖記》中小說意象的圖像呈現(xiàn)
周洪斌
(湖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湖南長沙 410000)
“一個語言符號,既是可說可聽、也是可想可‘視’的,當(dāng)下廣泛使用的理論術(shù)語‘語象’在這個意義上成立。”從這一角度看,語言到圖像是可以構(gòu)成一組生成關(guān)系的,“閱讀由可視的語言藝術(shù)為本質(zhì)規(guī)定的文學(xué)作品后,藝術(shù)家可按照視覺藝術(shù)構(gòu)圖的基本要求,將自己或受眾感興趣的語言符號或符號群圖繪或雕刻出來,使其生成為以繪畫和雕塑為代表的圖像藝術(shù),于是便產(chǎn)生了‘語圖關(guān)系’問題域”[1]。許鞍華版的《金鎖記》舞臺劇與張愛玲原著小說《金鎖記》在這種意義上構(gòu)成了一組“語圖關(guān)系”。
韋勒克曾指出:“各種藝術(shù)之間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建立在分析實(shí)際藝術(shù)品,也就是分析它們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之上的。”[2]121豐富的意象是張愛玲小說創(chuàng)作中無法忽視的創(chuàng)作成就,許鞍華版的舞臺劇對張愛玲小說中意向的還原較其他版本的舞臺劇更勝一籌。故而本文選取了小說《金鎖記》和粵版舞臺劇《金鎖記》中呈現(xiàn)的三組意象對兩個作品進(jìn)行比較研究,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字到圖像生成過程中形成的對照關(guān)系,同時也可以看到文字和圖像兩種不同載體表達(dá)同一對象時的差異。
一、張愛玲的“月亮”
“月亮”在《金鎖記》里是一個重要的意象,在小說的開篇和結(jié)尾都有提到: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