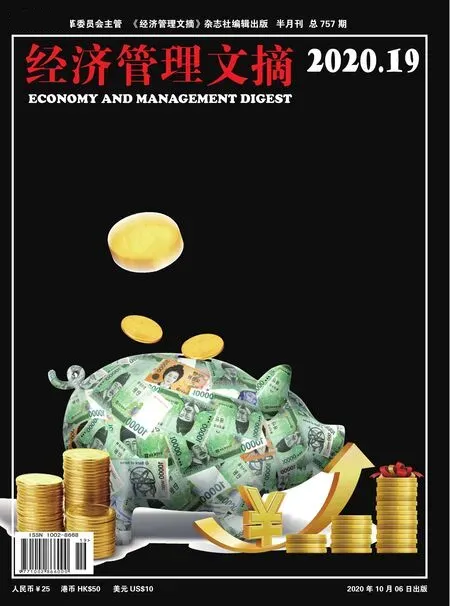基于分級診療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探析
■虞鳳鳳
(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1 問題的提出
取消藥品加成使得公立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的營運成本補償由醫療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補助三個渠道縮減為醫療服務收費和政府補助兩個渠道。以藥養醫僅是不合理醫療收費問題的一種表現,如果新的補償機制不能維持公立醫院平穩發展需要,那么生存發展的內在需求動機會使得公立醫院尋求其他牟利方式,這種收入結構的改變解決不了病人的降費需求,也解決不了衛生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最終都與取消藥品加成政策的改革初衷相違背。醫療是三醫聯動的核心,公立醫院的補償機制改革是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核心[1]。因此,合理設計新的公醫院補償機制是攻克醫改難題、鞏固破除醫藥養醫成果、推動醫改向縱深發展道路中的一個迫切問題。本文將從取消藥品加成后公立醫院的補償渠道入手,分析補償渠道對不同類型公立醫院的影響進而對公立醫院進行定位分組,并結合分級診療制度以期針對不同類型的公立醫院設計合理的差異化補償機制。
2 從內外部環境看公立醫院補償渠道
補償機制設計就是要將公立醫院在取消藥品加成收入后的不平衡在醫院、政府、病人三者之間建立一種更經濟、科學、穩固的新平衡,以使公立醫院能在保持公益性的前提下獲得經濟性,實現價值醫療。對補償渠道的探析,有助于了解取消藥品加成后外部環境對公立醫院補償結構、方向和程度的影響,進而為更好的設計補償機制提供思路。
2.1 醫療服務收費渠道
醫療服務收費渠道作為主要的補償渠道,通過提高體現醫療技術含量和醫護人員技術勞務性服務項目的價格,實現對藥品差價的大部分補償,使得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收費由藥品依賴轉向技術勞務依賴。因此,取消藥品加成政策的落地實施對于兩類醫院會產生不同效果,藥品依賴程度高的醫院在醫療費服務價格調整中得到的補償程度低于技術勞務依賴的醫院,技術勞務性收入在原本醫療服務收入中的比重越高,補償率越高。正如徐元元(2014)指出專家醫生市場認可度高、技術服務水平高,醫事服務費可以有效彌補取消藥品加成減少的收入[2]。
2.2 政府補助渠道
公立醫院補償的第二條渠道是政府補助。我國政府補助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醫保支付的醫保基金,第二種是直接的財政投入。醫保支付作為調節醫療服務行為、引導醫療資源配置的重要經濟杠桿是深化醫改的重要環節,直接影響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值的實現效果。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的主要直接目標是利用支付的經濟杠桿作用促進公立醫院補償機制轉變[3]。新醫改以來,各地積極探索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將單一的由按項目付費這種后付制轉向按人頭付費、按病種付費(包括 DRGs)、按床日付費、總額預算等預付制的多元復合式支付方式,使醫保由被動付費者轉變為兼具激勵與監管功能的戰略性購買者。然而這種支付方式的轉變無形中加劇了區域內各公立醫院對有限醫保基金的競爭,影響醫療服務價值的貨幣實現,產生不同的補償效果。醫療服務收費補償與醫保支付補償都是基于價值的市場競爭補償,用市場競爭機制的活力促進公立醫院主動改革,提高服務質量、提升服務效率、實現衛生資源的優化配置。
財政直接投入作為政府補助的第二種方式是政府作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主導力量用來引導市場、彌補市場失靈的一種調控補償手段,保障公立醫院能在秉持公益性的前提下,提高醫療服務可及性、促進公平公正。然而,過多的衛生財政投入不僅加劇財政負擔,還會導致醫療服務成本剛性化和醫療服務高管制化,使公立醫院惰性依賴補貼而非通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形成資源浪費。而財政投入不足又會使公立醫院在市場化競爭中追逐利潤偏離公益性。因此,為使財政資金實現精準補償,財政直接投入需要建立在動態監控市場補償對不同類型公立醫院產生的不同的效果下進行合理平衡設計。
3 基于分級診療的公立醫院補償設計
3.1 市場競爭補償下公立醫院的劃分
以醫療服務收費補償為橫軸,以醫保基金補償為縱軸,不同內部環境的公立醫院對市場補償的兩個渠道會產生不同的競爭優勢和劣勢,呈現兩維度四個象限的不同補償效果。第一類,勞務技術依賴程度和醫療價值創造能力均有優勢的公立醫院,取得高的醫療服務價格補償的同時能夠得到高的醫保基金份額。第二類,相對勞務技術更傾向藥品依賴,但是具有高的醫療價值,這類公立醫院雖然在醫療服務價格中的補償率不高,但是能獲得高醫保基金份額。第三類與第二類相反,更夠獲得高的醫療服務價格補償但是獲得的醫保基金份額不高。第四類,相對前面三類不僅具有藥品依賴性而且醫療價值也相對不高,醫療服務價格補償和醫保基金份額都相對較低。
3.2 基于分級診療的差異化補償機制
以上對公立醫院四種類型的劃分不是為了實現優勝劣汰,而是為了對不同類型的公立醫院進行服務能力和功能定位的分組,通過市場機制晴雨表的功能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指引,實現對資源結構及配置效率的雙優化。以縱向醫聯體為代表的分級診療制度能夠調節醫療資源的“倒三角”配置、防止虹吸效應的同時實現公立醫院的同質化管理,促進不同類型公立醫院的良性協同發展,進而為差異化補償機制的設計和落實提供更清晰明朗的思路。
根據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總體要求和指導意見可將公立醫院縱向分為三層,第一層城市公立醫院,第二層城市二級醫院、縣級醫院,第三層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上文市場兩維度補償效果的的劃分可分別對應縱向醫聯體的三個層級,即第一類對應第一層,第二、三類對應第二層,第四類對應第三層。以城市三級醫院為代表的第一層不僅在醫療人才、技術上有較大優勢,在與醫保、供應商談判時也更具議價能力,并且患者對價格的彈性相比其他層次更不敏感。因此,在醫療服務價格調整中這一類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可相對高些,層級越往下價格相對越低。這種差別化的定價不僅能體現不同層級醫療服務的勞務技術價值,符合價值導向的定價規則,還可以利用價格杠桿夯實分級診療促進醫療的同質化管理。
其次,要在一個醫院主體中同時采用多種混合支付方式比較有難度,并且按病種付費和DRGs等捆綁打包的付費方式在多步驟流程化醫療服務開展中具有控費提效的作用,而對少步驟甚至單步驟的醫療服務并不能體現其優勢。因此,可以在第一層級實行按病種付費為主,并積極探索DRGs支付,第二層可更多的采用按病種付費、按床日付費方式,而在基層醫療機構可主要采用按床日、或按人頭付費方式。對于縱向醫聯體單位還可以鼓勵實施總額預付制。
最后,基于分級定價及分級混合支付方式對公立醫院的市場補償效果能為政府精準財政投入指明方向:對于市場補償效果較好的第一層,財政投入以對重點專科建設、高精尖技術和設備的項目補助為主,減少經常性財政補助;第二層以政策性虧損補助為主,探索按服務量、績效指標完成度等分類財政補助方式;而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主要以政府購買服務為主,并對公共衛生服務例如疫情防控、應急醫療物資等實行專項補助或政府兜底補助。分類補助有利于在保障各層級不同功能定位的公立醫院協同發展的同時,將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4 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4.1 成本核算及控制
不論是醫療價格服務調整、醫保支付方式改革還是政府直接補助投入的衡量都需要醫院真實、準確、合理的成本數據支撐。然而,一方面醫院成本核算起步較晚,成本控制與管理意識較為薄弱,另一方面醫療服務種類繁多,不同利益相關方對成本核算的內容及方法也各有不同,我國尚未建立公立醫院成本核算制度[4],醫院間數據缺乏可比性,不利于補償制度的設計和執行。鑒于基于分級診療的補償機制設計中對公立醫院同質化分組思考,筆者認為可以探索分級成本核算制度,比如在城市三級醫院在全成本的基礎上更多進行基于價值鏈管理的病種成本核算,二級、縣級中小型公立醫院可在全成本基礎上多采用床日成本核算,而基層醫療機構多采用診次或單項目成本核算。
4.2 分級診療推進實施
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動態調整需要將現階段雜糅且不合理的就醫方式予以同質化分工。分工分組下的精細化內涵管理及流程優化才能逐步改進醫療服務這種特殊生產力,進而實現供給側改革使醫療服務的生產力(供方)與醫療服務關系(需方)相適應的目標。然而當前我國分級診療模式存在“難以放”“接不住”“流不出”“連不起”“立不穩”“信不過”等現實困難[5]。因此,要不遺余力的建立并促成科學合理的分級診療模式,一方面通過醫療服務價格的分級定價、不同級別醫療機構差異化的醫保支付政策以及醫保報銷比例引導患者就醫流向,另一方面通過補償機制的設計落實各類醫療機構的功能定位,進一步夯實分級醫療結構,實現補償機制與分級診療聯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