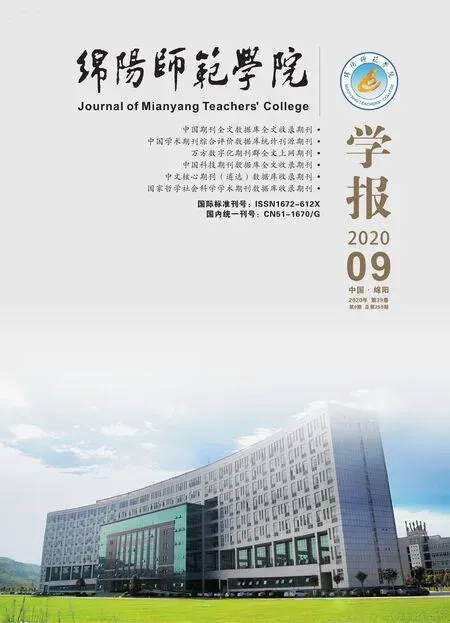旅游敘述何以成為可能:一個符號敘述學(xué)的分析
朱昊赟
(四川大學(xué)符號學(xué)-傳媒學(xué)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隨著休閑經(jīng)濟時代的來臨,人們對旅游休閑的需求日益高漲,旅游業(yè)態(tài)的發(fā)展、旅游形式的變化等問題日益受到廣泛關(guān)注。旅游現(xiàn)有的研究路徑主要從以下兩方面展開:一是構(gòu)建視角,從自然地理層面探討旅游目的地資源的開發(fā)與保護,側(cè)重個案分析;二是效果視角,通過引用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歷史學(xué)、文化學(xué)、營銷學(xué)等概念,對旅游的經(jīng)濟價值與文化作用進行研判。以上研究,其對象多是指旅游資源或者旅游影響,實則在某種程度上欠缺了對旅游體裁本身核心特征的思考。
旅游之所以鮮少被當(dāng)作完整的敘述體裁進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旅游”敘述的文本邊界存在疑慮。現(xiàn)如今常見的旅游敘述多是圍繞具體文本體裁中的“旅游描寫”展開,包括但不限于中英文導(dǎo)游詞文本的翻譯、旅游網(wǎng)站的宣傳、文學(xué)作品的描寫、影視體裁的展示、口碑分享、旅游攝影等。這些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都很明確地選擇以風(fēng)景作為一種敘事資源,或者描寫中心”[1],承認(rèn)“旅游目的地之所以能夠被文學(xué)敘述所影響,主要便是由于游客自身、文學(xué)作品、文學(xué)作品的作者三者之間存在情感聯(lián)系,以此建構(gòu)出旅游景觀的意義”[2]。以上視角下的研究雖對旅游敘述價值作出肯定,但遺憾的是,其研究對象已是被再次媒介化的“旅游”衍生品,而不是對旅游對象自身。
旅游定義紛繁復(fù)雜,雖無權(quán)威定義,但也有學(xué)界共識。旅游不僅僅是指空間位置的暫時移動,而是“一種基于人自身的需要, 而產(chǎn)生的一種普適的人文現(xiàn)象”[3]。“在文學(xué)之外,敘述的范圍遠(yuǎn)遠(yuǎn)廣大得多”[4]3,“無論是國學(xué)熱、旅游熱、古跡熱、奧運熱、消費熱、品牌熱,都因敘述而獲得意義關(guān)注”[4]16。旅游敘述的研究對象不應(yīng)該僅僅局限于媒介化的文本再現(xiàn),而應(yīng)回歸到旅游體裁自身的特征與本質(zhì)上來,旅游敘述應(yīng)當(dāng)“透過‘內(nèi)容’這一現(xiàn)象載體,直指‘?dāng)⑹隆@一問題本質(zhì)”[5]。囿于傳統(tǒng)敘事學(xué)的媒介邊界問題,旅游敘述研究一度陷入僵局,直至趙毅衡《廣義敘述學(xué)》的出版,才讓旅游擺脫“媒介化文本”的困擾,能夠以獨立的體裁形式納入到敘述學(xué)的研究框架之中。
“廣義的符號敘述學(xué),即研究一切包含敘述的符號文本的敘述學(xué)”[4]416,“廣義敘述學(xué)超越了門類敘事的閾限,試圖為一切敘事,真實的/虛構(gòu)的、不同媒介和不同時間軸的所有敘事提供一個更貼切的概念,一個有用的方法論,一套通行的術(shù)語,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廣義敘述學(xué)的理論建構(gòu)恰好體現(xiàn)了這種包容萬象的能力”[6]。《廣義敘述學(xué)》一書中對于媒介邊界、敘述類型、主體沖突等問題展開的思考,不僅突破了以往旅游敘述研究的文本邊界,樹立了旅游敘述合法性的研究地位,更是對旅游作為一種獨立敘述體裁核心問題的正視,是對其文本性和敘述性的升華。只是,該書尚未對旅游作為敘述文本的各環(huán)節(jié)進行詳細(xì)討論。本文通過剖析敘述底線的定義,探究旅游敘述作為獨立敘述文本的體裁特征,并解答一直被學(xué)界所忽略的有關(guān)旅游敘述的特征問題。
一、旅游敘述的合法性
依據(jù)趙毅衡在《廣義敘述學(xué)》中提出的論述基礎(chǔ),任何敘述成立的前提條件,都需滿足以下兩個要求:“1.某個主體把有人物參與的事件組織進一個符號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為具有時間和意義向度。”[4]7判定旅游是否能夠成為敘述,則需判斷其是否扣合以上“敘述定義”規(guī)定的標(biāo)準(zhǔn)。因此,對旅游敘述文本性的探討,也將從符號組合、人物參與及理解意向性的角度展開。
首先,旅游符號組合的定義要求。旅游文本與傳統(tǒng)二維關(guān)系呈現(xiàn)的文本不同,它是一個立體三維的呈現(xiàn)。“在旅游活動中,功能單一的旅游者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們只有進入到旅游符號的連續(xù)體中才能起作用。”[7]這個連續(xù)體被稱之為區(qū)別于其他符號空間的“旅游符號空間”。鄭哲為了突出旅游空間文化浸潤的全面性,特意在“文化旅游的范疇中將‘環(huán)境’指代明確化,引入‘文化環(huán)境泡’概念,‘泡’是立體的、多角度的,在我們身上的映射是無死角的”[8]。如將旅游文本從多維度構(gòu)建的話,則需囊括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旅游的靜態(tài)符號,即旅游目的地內(nèi)供接收者直接面對和觀賞的旅游對象。彭丹將旅游吸引力的建構(gòu)翻譯分為“神圣化景物的命名狀態(tài)、框限和提升、奉祀秘藏、機械化再生產(chǎn)和社會再生產(chǎn)”[9]五個步驟。前三個步驟以旅游資源的選取、旅游目的地空間范圍進行框定的方式,實現(xiàn)旅游空間與慣常生活空間的區(qū)隔。任何旅游目的地都是“旅游規(guī)劃師”設(shè)計出來的產(chǎn)物,只是“旅游規(guī)劃師”并非指具體的個人,而是以發(fā)號施令的方式實現(xiàn)旅游目的地內(nèi)符號組合的功能性總稱。在符號敘述學(xué)視野下,“旅游規(guī)劃師”實則是以區(qū)隔旅游世界和慣常生活世界為目的,以搭建起可供敘述的框架為手段的文本敘述者。通過“旅游規(guī)劃師”(作為文本敘述者)的籌劃,景觀的布局、導(dǎo)覽的線路、配套的設(shè)施、具體的表演活動等均以符號組合的方式落在了旅游文本之內(nèi)。此時的靜態(tài)旅游符號為游客的游覽體驗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且不以接收者的意志而出現(xiàn)任何形態(tài)上的改變。
其二,旅游的動態(tài)符號,即游客“此時此地”的親自參與。只有游客以投入自己的時間、體力、智力、金錢等方式,按照“旅游規(guī)劃師”前期籌謀的路線、環(huán)節(jié)、導(dǎo)游的帶隊、活動等具體的游覽規(guī)則進行線路游覽,才可促進旅游靜態(tài)符號產(chǎn)生意義價值。靜態(tài)旅游符號是旅游的基礎(chǔ)形式,動態(tài)旅游符號是對靜態(tài)旅游符號體驗過程的具體記錄與結(jié)果呈現(xiàn)。旅游文本是靜態(tài)符號與動態(tài)符號相組合的產(chǎn)物,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旅游文本”是以旅游規(guī)劃為前提,通過旅游靜態(tài)符號與動態(tài)符號相互交織而出的共同結(jié)果,單獨從一個主體出發(fā)而對旅游文本進行解釋與分析,必然不足以概括旅游全貌。
其次,人物參與是旅游文本概念中較為明顯的一點。旅游目的地范圍內(nèi)的導(dǎo)游、游客、販賣紀(jì)念品的商人、工作人員等,他們在旅游文本的動態(tài)化過程中以此時此地具象的“人物”方式現(xiàn)身,并在旅游文本中充當(dāng)著不同的功能角色,共同為旅游這個文本的豐富提供著自己的力量。“文本的構(gòu)成并不取決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接收方式。”[10]43敘述底線定義中對“接收者”進行強調(diào),實則是明確了文本的“裁判人選”。此時的文本無需獲得所有人的認(rèn)可與接受,只要“接收者”能夠接收信息并解釋出意義便可使敘述成立。同樣的北京之行,在愛好人文建筑的游客眼中,北京的故宮、長城、圓明園等古代建筑的風(fēng)采成為北京旅游之行的意義;在愛好美食的游客眼中,全聚德的烤鴨、稻香村的點心、六必居的醬菜等傳統(tǒng)小吃的美味則成為了北京旅游之行的意義。北京這座現(xiàn)代都市的客觀存在沒有絲毫變化,但是在不同的游客眼中卻有不同解讀。因此,文本完整意義的獲得,實際上是文本存在的具體形態(tài)與接收者所擁有的主觀感受相互“協(xié)調(diào)”的結(jié)果。
綜上所述,只有同時具備以上敘述條件的旅游才可以稱得上是旅游敘述研究的范疇,旅游敘述的文本合法性問題已經(jīng)界定清晰。“敘事不僅可以解釋旅游的現(xiàn)實建構(gòu)問題,同時也可以理解游客如何將旅游經(jīng)驗轉(zhuǎn)變?yōu)橛幸饬x的經(jīng)驗故事。”[11]因此,對旅游敘述問題進行論證,不僅可從學(xué)理化角度厘清旅游文本的內(nèi)在機理,而且也是對旅游行業(yè)發(fā)展進行的現(xiàn)實觀照。
二、旅游敘述的演示性
當(dāng)我們介入到旅游文本內(nèi)部之后,對旅游文本敘述源頭的討論則接踵而來。在符號傳達(dá)的過程中,敘述者是所有敘述文本產(chǎn)生的源頭,敘述文本的接收者必須按照敘述者的所思所構(gòu)進行接收。西摩·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中,將文本的敘述交流過程概括為“真實作者——隱含作者——敘述者——受敘者——隱含受眾——真實受眾”[12]14。此敘述理論多用于文學(xué)作品或電影的解釋,而對于媒介類型較為豐富的旅游文本而言,解釋性難免受限。
趙毅衡洞察到了媒介在當(dāng)今信息傳輸過程中的重大作用,在《廣義敘述學(xué)》中創(chuàng)造性地將媒介—時間向度指標(biāo)納入對敘述體裁的分類考量。通過媒介—時間向度與“再現(xiàn)的本體地位(紀(jì)實/虛構(gòu))”相結(jié)合,敘述體裁可概括為實在性敘述、擬實在性敘述、記錄性虛構(gòu)敘述、演示性虛構(gòu)敘述、夢敘述、互動式敘述[13]六類。在這六類體裁中,敘述者以“人格—框架”的形式存在。“人格”“框架”分列線性兩端,當(dāng)文本體裁越靠近實在性敘述方向,敘述者越向“人格”一端滑動,且以顯身的人格形式出現(xiàn);當(dāng)文本體裁越靠近互動式敘事方向,敘述者越向“框架”一端滑動,且以框架形式出現(xiàn),人格化逐漸退場。
值得一說的是,敘述者不等同于真實作者,受述者不等同于真實受眾,敘述者與受述者是一組相對的概念,是功能性的指示符。“敘述者呈二象形態(tài):有時候是具有人格性的個人或人物,有時候卻呈現(xiàn)為框架,什么時候呈現(xiàn)何種形態(tài)取決于體裁,也取決于文本風(fēng)格。”[13]因此,筆者認(rèn)為旅游文本的敘述者是從做出各種旅游符號的安排、從旅游目的地的規(guī)劃指令發(fā)出者的身上分化出的一個抽象人格,只是這個人格在“人格—框架”兩端滑動,且更加偏向框架一端。前文所提及的“旅游規(guī)劃師”其實便是此處敘述者“人格—框架”的功能顯現(xiàn),它為旅游文本的成立搭建了一個空間層面的框架,將旅游靜態(tài)符號與日常符號做了物質(zhì)層面的區(qū)隔。
演示類敘述與紀(jì)實性敘述相比,具有“展示性、即興、觀者參與以及媒介的‘非特有性’”[14]特征。“旅游與常態(tài)生活之間有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首先一定表現(xiàn)為空間上距離的移動。”[15]依據(jù)上文中對旅游文本靜態(tài)符號與動態(tài)符號兩個層面的分析,旅游敘述文本是需要游客親身前往旅游目的地進行“身體力行”的體驗才可獲取意義的文本類型。旅游文本需要游客前往、即刻獲意的特征,恰好滿足展示性敘述的要求。在旅游目的地內(nèi)的游客,其行為言語均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并非獨創(chuàng)的新鮮事物,那么媒介的“非特有性”特征也由此展現(xiàn)。“游客總是在尋找或期待新鮮的、不同的事物。”[16]8游客之所以向往旅游很大程度上是對異地新鮮感的追求,這種意想不到的、充滿新鮮感的事物才是游客希望體驗到的。故而在媒介—時間向度下,旅游文本屬于演示類敘述。
旅游文本親自參與、現(xiàn)場獲取的特征規(guī)約,促使游客需分化出一部分人格充當(dāng)敘述者參與旅游文本的敘述,對敘述框架進行協(xié)同填充。因此,旅游文本在演示敘述的框架內(nèi),一方面可邀請游客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如扮演角色等)參與到敘述過程中,通過對旅游文本的各種靜態(tài)、動態(tài)符號進行安排與設(shè)計,完成對旅游情節(jié)時間和意義向度的建構(gòu);另一方面又成功地實現(xiàn)被敘述的旅游世界和現(xiàn)實經(jīng)驗世界的區(qū)隔,突出旅游目的地之獨特所在。
三、旅游敘述的二度區(qū)隔
“一度區(qū)隔是再現(xiàn)框架,把符號再現(xiàn)與經(jīng)驗世界區(qū)隔開來”[4]74,“二度區(qū)隔則是二度媒介化,與經(jīng)驗世界就隔開了雙層距離”[4]76。在我們的經(jīng)驗世界里,“游客”是我們面對的客觀實在的人:在一度區(qū)隔中,是一種身份區(qū)隔,游客成為一種需要以“體驗”為媒介進行景觀意義獲取的特殊身份類型;在二度區(qū)隔中,他是敘述框架的協(xié)同參與者,需分裂出一部分人格對旅游文本進行填充。在此,筆者需要著重強調(diào)一點,紀(jì)實類敘述屬于一度區(qū)隔,而虛構(gòu)敘述必然是以二度區(qū)隔的方式與經(jīng)驗世界進行的分離,但并不是只要進行了二度區(qū)隔就是虛構(gòu),這一因果關(guān)系不能夠混淆。
“旅游世界不是客觀科學(xué)或宇宙論意義上的世界,它是作為旅游主體從其特殊觀點體驗到的世界,顯然是一個主觀和相對的世界。旅游者對旅游世界的建構(gòu)可以通過敘事或?qū)嵉芈糜误w驗的方式進行。”[17]就再現(xiàn)的本體地位類型而言,旅游敘述與戲劇、演出、游戲、比賽等形式同屬于二度框架區(qū)隔的敘述類型,但與他們有明顯不同之處。
在一度框架下,旅游文本在組合的過程中通過篩選,對靜態(tài)、動態(tài)符號的呈現(xiàn)狀態(tài)已經(jīng)是被挑選出來用于展示的符號結(jié)果。旅游與戲劇、演出、游戲、比賽等形式相比,其一度框架是相似的,都是符號化的選取與再現(xiàn),均與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世界進行了空間的區(qū)隔。但是在二度框架的區(qū)隔下,它們則有明顯差異。在戲劇、演出的二度框架內(nèi),演員表演的人物是一個角色,這個角色并非演員個人自身;在游戲的二度框架內(nèi),游戲者充當(dāng)?shù)氖怯螒蛑械耐婕医巧@個角色是游戲規(guī)則制定下的“人物”,也非游戲者自身。但是在旅游設(shè)置的二度框架之下,游客卻不是虛構(gòu)的角色人物,而是主體自身。
“人一旦面對他人表達(dá)意義,或?qū)λ吮磉_(dá)的符號進行解釋,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為某一種相對應(yīng)的身份。”[10]1游客在現(xiàn)實生活中和普通人一樣,具有一個現(xiàn)實人格。“游客”被作為研究對象從人類群體中抽取出來,產(chǎn)生了一度區(qū)隔。只有在游客面對旅游文本、進入到旅游體驗過程之后,才算進行了二度區(qū)隔。這時游客才可以分裂出一個人格,他以線路行進、觀看景色、聆聽講解、拍照留念等行為推動著敘述文本的進行,協(xié)同敘述者進行框架敘述。我們當(dāng)然不能說此時游客的體驗是虛構(gòu)的,因為游客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扮演框架要求下的其他角色人物。因此旅游二度框架的設(shè)定并非將其指向了虛構(gòu)敘述的類型,而是對其敘述框架的再次豐富。
游客才會有“虛構(gòu)”的感覺呢?那便是進入到旅游文本內(nèi)部以“扮演非本人的角色”之時。“當(dāng)我們看到了區(qū)隔框架時,我們才知道它是虛構(gòu)。虛構(gòu)的意義正是為主體提供了聚合軸上的可能,讓我們看到我們可能具有的其他本質(zhì)和存在形態(tài),從而豐富對自我的認(rèn)知。”[18]最為典型的是迪士尼樂園、侏羅紀(jì)公園這類旅游項目,游客在其范圍內(nèi)可以扮演怪獸、恐龍、公主、海盜等與日常生活差異極大的角色,他們期待與體驗的便是這種虛擬世界帶來的新奇感。不得不說的是,游客雖然是在二度框架之內(nèi)進行了各種體驗,但最終還是要回歸現(xiàn)實世界,或者說必須是回歸的。當(dāng)我們作為區(qū)隔框架世界內(nèi)的人物狀態(tài)出現(xiàn)時,是無法看到區(qū)隔內(nèi)的這個世界是符號再現(xiàn)的世界,因為區(qū)隔的作用便是把框架內(nèi)符號再現(xiàn)的世界與框架外的世界隔絕開來,此時虛構(gòu)以事實的方式呈現(xiàn)。“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是這個道理。
四、結(jié)語
旅游敘述何以成立,是研究旅游敘述問題的起點。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符號敘述學(xué)論域內(nèi)旅游與其他一般的敘述類型一樣,都可以作為獨立的敘述文本對象進行分析探討,這一結(jié)論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本文正是通過符號組合、人格—框架二象以及二度區(qū)隔的討論,嘗試完成對旅游敘述合法性與特征性問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