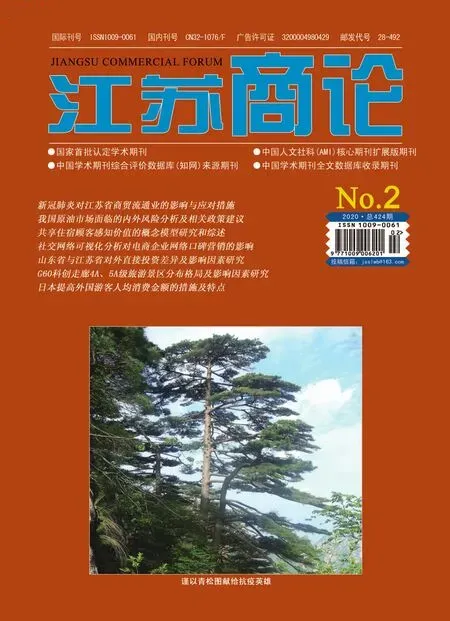消費社會理論及其影響
尤 峰
(南京農業大學 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南京210095)
一、引言
“消費社會指的是一種物品高度豐富、從生產為主導向消費為主導轉型的社會①。”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斷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過程,然而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力水平已經相對過剩,物質的需求已經逐步得到滿足,而物質財富卻依然豐盛。當人們已經無法停留在純粹對于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消費,從而轉向對于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的消費時,社會也就逐步過渡到一種以消費為生活核心的消費社會中來。
十九世紀實際上是一個物資相對匱乏的時代,用鮑德里亞的話來說,就是工業化時代。在十九世紀,人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較大幅度提升,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而當前的社會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候,生產力大幅提升,人們對物品的消費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核心組成部分。此時,人們對于物品的消費已經不僅僅取決于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更多地將商品看作是身份的象征,聲望的標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法國學者鮑德里亞以符號理論為基礎,發展了關于消費和商品的思想,同時不斷發掘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從而衍生出一套自己的“消費社會”理論。
對于鮑德里亞關于商品與消費觀點的研究,不僅能夠深入了解消費社會理論的視野轉變,更能夠展現出從物產匱乏的工業時代到消費社會的變遷過程。
二、從使用價值到符碼價值:消費社會的來臨
“消費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現象。但在匱乏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消費僅僅是維持生存②。”十九世紀正是這樣一個物質相對匱乏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商品的本質是通過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和價值體現的。商品之所以能夠被消費,是其不僅具有交換價值,更是因為其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使用價值也正是人們在生產商品時所賦予物的社會屬性。這一屬性反映出人們在購買商品時,更重要的是為了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因此,當時馬克思認為“在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中,生產是中心。交換、分配和消費是在生產的基礎上進行的,消費只是生產的產物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生產是消費的基礎,消費根植于生產并且依附于生產。只有完成生產,消費才成為可能。在工業社會中,生產是消費的基礎,因此消費實際上是商品的使用價值的貨幣交換過程。
但是,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工業社會逐步過渡到后工業社會,物質財富進一步豐盛,人們對于商品的追求除了使用價值,還有其背后的符碼價值。鮑德里亞十分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從而預見了消費社會的來臨。
鮑德里亞深刻地認識到,在后工業社會,商品已經和符號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融合體,符碼消費已經成為后工業社會的中心議題。在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里,商品已經逐漸被符碼價值和象征意義所取代,不同的商品被身份、名望、地位、權力以及階層等賦予了新的社會屬性。因此,在后工業社會中,人們的消費已經逐漸從對物的消費轉向了對符號意義的消費。這一點上,鮑德里亞充分利用了索緒爾“所指”與“所能”之間的互構關系來解釋符碼價值。他認為人們對符碼的消費從根本上抹去了對物本身的消費,這使得符碼價值徹底凌駕于使用價值之上。人們在購買商品時,首先并不是去考慮某一商品的功能與作用,而是更多地去在意品牌、價格,更多地去關注商品所能夠帶給自己聲望、地位等方面的附加價值,也即商品所承載的符號意義。這使得物品或商品成為消費社會中劃分階層的標志。商品已經成為控制人類思想與精神世界的罪魁禍首。隱藏在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徹底奴役了人類。因此,鮑德里亞明確指出,“人們一旦進行消費,那就絕不是孤立地行動(這種孤立只是消費者的幻覺,而幻覺受到所有的關于消費的意識形態話語的精心維護),人們就進入了一個全面的編碼價值生產交換體統中④。”這一切儼然成為了后工業社會中,在生產力大幅提高下所形成的消費特征。即在消費過程中,背離商品內含的使用價值,異化為關注商品背后的符碼價值。同時,這樣的消費特征也就意味著傳統的工業社會已經逐漸過渡到了以追求商品符碼價值為核心的消費社會。
三、從勞動異化到消費異化:消費觀的轉變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已經徹底變為資產階級統治、壓迫和剝削群眾的異己力量。生產活動已經成為資本家對勞動者制約和奴役的手段。在生產活動中,勞動者已經完全喪失了自身。與此同時,生產也扭曲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它將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異化為人與物的社會關系,只能通過物來表達。在資本主義商品交換模式中,勞動者需要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來獲得生存。因此,在十九世紀中后期,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也即勞動已經逐漸出現異化的傾向。
而進入二十世紀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生產力不斷提升,技術不斷進步,社會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致了物質生產水平的逐步提高,可供人們消費的商品逐漸增加。這使得西方社會逐漸向消費社會轉型,勞動的異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于是,以鮑德里亞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開始對新出現的消費現象給予關注。鮑德里亞開始用異化來解釋社會中消費的現象。
在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中,符碼成為鏈接社會關系的關鍵一環。符碼的存在,一方面將物與人們的精神世界構成一個緊密不可分的整體;另一方面也將人與人的關系轉變為物與物的關系。符碼價值隱藏在商品背后,成為展現不同人個性化特征的一種方式,也正是因此,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才成為人們所熱衷關注的焦點。商品中所體現出的符碼意義將人們分為不同身份、不同階層,它甚至成為群體特征的標志,但這也會導致人們的消費心理走向異化,甚至影響到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
鮑德里亞在總結前人的觀點后,更是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消費異化”論。他認為,盲目追求商品背后的符碼價值的人們,已經逐漸喪失了對于消費的主觀思考能力。“每一則廣告、每一條新聞都強加給人一種一致性,即所有個體都可能被要求對物品的符碼含義進行解碼,就是說,人們通過對媒介信息的解碼而不假思索地自動依附于那種它在其中被編碼的編碼規則⑤。”人們在選擇商品時,會將虛假需求與真實需要相混淆。真實需要是為了應對人生存條件而產生的必需品需要,而虛假需求的實質也就是消費者的內心欲望。在傳媒體系的不斷刺激下,人們內心的購買欲望同美好的幸福生活聯系起來,真實需要不斷被抑制,逐漸被隱藏起來,導致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無法察覺自身內心關于生存環境的必需品的需求,而轉向專注于自我欲望的滿足,從而出現了“消費異化”現象。這樣異化的消費觀導致人們沉浸在無邊的消費欲望中無法自拔,而大眾傳媒特有的宣傳手段中所展示的圖片、信息不斷給消費者營造出全新的,能夠展現出獨特性與更高身份象征的符碼意義。這些符碼意義抑制了消費者的消費主動性,使得消費者沉浸于這樣商品化世界無法自拔,盡情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愉悅感,從而逃避現實生存環境所帶來的壓力。于是,這樣的宣傳手段不僅可以控制消費者,甚至可以控制整個社會。從這樣的現狀來看,鮑德里亞的成就就在于,他的“消費異化”論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于“消費異化”在新的社會發展形勢下進行了廣泛的現象描述,從而試圖引起人們的警惕,改變消費中的一切不合理的成分,讓消費走上正確軌道。
四、從理論到實際:當下中國消費現狀的思考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個年頭,中國的經濟也已經走過飛速發展的40年,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空前成就。隨著2020年的到來,當下的中國即將徹底打贏脫貧攻堅戰,從而擺脫貧困,從一個物產匱乏的時代進入一個物產較為豐盛的時代。加之全球一體化浪潮的不斷推進,西方異化的“消費社會”也逐漸在中國生根發芽。在這樣的時代契機下,端正國人的消費觀,培育良好的消費文化,不僅可以促進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還可以維護社會的平穩運行。
(一)警惕未富先奢,端正國人消費理念
現如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可謂是勢頭良好。自2011年,中國超過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經濟發展勢頭絲毫沒有消退的跡象,反而趁熱打鐵,一鼓作氣,逐步擺脫貧困。但國內貧富差距依然較大。在中國,你既可以看到歐洲發達國家的繁榮,如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地區,同時也可以看到非洲地區的貧瘠,如中國的西部山區,貴州、云南等地。這樣的比喻雖然較為夸張,但還是將中國的貧富差距現狀反映出來。在西方消費理念的沖擊下,部分經濟基礎較差的地區許多人不顧自身經濟狀況,熱衷于追求奢侈品名牌消費,從而導致貧富地區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與此相反,在較為發達的地區則出現炫耀性消費和無益消費。豪車開過,風馳電掣,飲食娛樂,鋪張浪費。這些都是鮑德里亞所說的消費異化的表現。因此,應端正國人的消費觀,弘揚傳統消費理念,以節儉為榮,以揮霍為恥,始終警惕未富先奢現象的出現。從而逐步縮小國內經濟發展差距,始終保持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正確道路上。
(二)反對虛榮消費,強化消費者主體意識
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契機下,國內消費狀況顯現出多元化趨勢。其中,生存需求消費和虛榮型消費并存。許多社會大眾一方面為了追求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通過商品實現自我的階級歸屬和身份認同;另一方面自身的經濟狀況并不良好,于是“山寨”“高仿”商品一躍成為消費寵兒。這些商品對于部分消費者來說,既滿足了自身對于商品符碼意義追求的虛榮心,實現心理上的階級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同時又減少了經濟開支,可謂是一舉兩得。但是,這樣的消費者并未意識到這些不過是在身處的現實社會中,大眾媒體、廣告媒介通過狂轟濫炸而勾勒出的虛偽場景。消費者購買山寨產品這樣的做法,既沒有得到像鮑德里亞所說的從商品中區分出階級與獲得身份認同,又促使假冒偽劣商品大行其道。他們所獲得的自身的榮譽感與自豪感不過是從掩耳盜鈴的自娛自樂行為中所獲得的虛榮感。消費主體將二者混淆,從而被山寨商品所奴役,而喪失了自我意識與自我行為。因此,消費者必須將享受型消費和虛榮型消費相區分。在消費者經濟狀況允許的前提下,適度放松自身,如旅游消費,娛樂消費等,強化消費者的主體意識,反對不顧自身經濟狀況而產生的虛榮型消費。
(三)倡導綠色消費,培育健康消費文化
隨著我國的經濟不斷發展,消費者逐漸從物質消費領域轉向文化消費領域。人們對于文化,對于服務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同時,對消費品的質量,服務品質等要求逐步增高。高質量的商品消費的背后,必然與高價格相關聯。中國的消費主體年輕化趨勢越發明顯,年輕人的消費經濟能力并未達到高質量消費品的要求,但對于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的追求卻從未停止,對于品質的自身需求依然在不斷提升。而這種追求實質上就是被內心的購買欲望所刺激而形成的虛假需求。虛假需求遮蓋了年輕人心中的真實需要,從而一味地追求品牌,追求物質的符碼意義。因此,超前消費、分期消費等消費方式成為當下年輕人的消費首選,甚至出現裸貸等更為激進的超前消費方式。無疑,這樣的消費方式不利于年輕人對于財富的積累,無法實現可持續消費,更容易使得年輕人陷入一個被某些不良商家和媒體所營造出來的消費陷阱,不能自拔。最終拖垮青年消費者,甚至可能拖垮一個家庭。因此,在社會的主流宣傳媒體中,應該倡導年輕人樹立適度消費與可持續消費的理念,將年輕人的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現實需求相結合。在吸納西方消費理念的同時,積極引導,從而形成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使得年輕人,甚至社會大眾,減少對消費商品背后的符碼意義的困擾,擺脫物品對自身的控制,認清自身的真實需要,重建自身消費欲望。這樣,一方面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穩步發展,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另一方面可以培育國人健康的消費文化,從而促進消費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范和生,劉凱強.符碼消費鏡像中的心理異化及實踐邏輯——兼論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學[J].寧夏社會科學,2016,3:104-109.②張佳,王道勇.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理論的演進及啟示[J].科學社會主義,2018,(6).
③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第1卷,1972:93-97.
④張一兵.消費意識形態::符碼操控中的真實之死——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解[J].江漢論壇,2008,(9):25-26.
⑤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