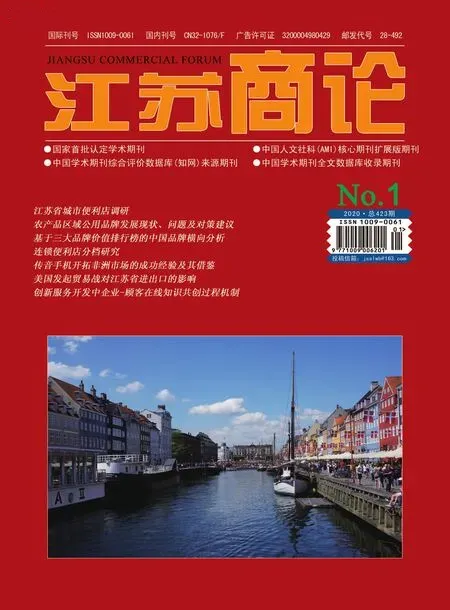工業4.0背景下,品牌群與品牌戰略傳播
高 栩
(南昌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330000)
工業化進程發展到現在,按照“N.0”來區分不同工業時代,目前公認的是大致處于“工業4.0”時代。不同的工業時代對應著不同的產業發展模式。參考國際上產業發展模式來看,產業集群作為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已經引起不少經濟學家的重視。從目前我國的產業集群發展情況來看,大部分地區仍處于同質化明顯、產業鏈單一、競爭力有限的初級發展階段。在工業4.0時代,借鑒不同時期的產業集群發展模式,提出品牌群發展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是對實踐的經驗回溯,更是中國實施品牌戰略傳播的基礎和現實中科技創新型經濟模式發展的需要。
一、工業4.0,科技創新的時代
從18世紀60年代水力珍妮紡紗機提高生產效率到18世紀后期瓦特改進蒸汽機并使之大量運用于工業采礦業為發端,機械運轉代替了手工勞動,從而開啟了以機械設備制造為主的工業1.0時代。這個時期生產規模擴大的特點,就是依賴于生產空間的擴大、生產機械臺數的簡單疊加以及勞動力的增加。
20世紀初,電氣化的發展,有線無線通信、化學、內燃機汽車的發明等,人類社會進入工業2.0時代,電氣化使得工業吸納的勞動人口大幅增加,工業分工愈發精細,企業規模在空間上擴大,需要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和人口規模上組織生產①。此時雖然也有通過采用新設備、新工具、新的生產方式方法,獲得更多的利潤,但究其本質,大部分企業仍舊是以“流水線生產-人口聚集模式”來組織生產,換言之,此時擴大生產規模更大程度上是依靠生產線的簡單疊加。
“工業3.0”則發展于二戰以后,這一階段,機器開始逐步替代人類計算和作業。此后的幾十年,第二產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不再依賴于生產器械或流水線的簡單疊加,而是更注重于生產方法和生產工藝的改進,利用大量的機械手替代人工操作。也即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不必再單純地通過生產空間的擴大和勞動力的增加來進行。
現在,人類終于再度步入由科技創新帶來工業生產與人類社會巨大變化的坎口。2011年,美國政府啟動了AMP2.0“先進制造伙伴計劃(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2.0)”提出了 “在哪里發明、在哪里制造”的口號,謀求重奪美國在世界市場的統治地位②。2013年,不甘落后的英國發布了《未來的制造》報告,為加快促進科研成果轉化,設立了先進制造、成形技術等7個“高價值制造推進研發中心③”。與英國的戰略相對應,法國提出了“新工業法國”的方案;日本則推出了“再興戰略”計劃;韓國開始實施“新增動力戰略”。而2013年德國政府在《高技術戰略2020》中為工業4.0正了名,并確定其為未來德國十大項目之一,將之上升為國家戰略,旨在支持工業領域進行新一代革命性的技術研發與創新④。
從工業1.0到工業4.0,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時代怎么變,其發展進步的本質都是科技的創新。并且,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影響更廣泛到國際的金融格局與政治事務格局。所以,真正能主導時代最強音的國家,是掌握了最前沿科學技術的國家。
二、品牌群是品牌戰略傳播的基礎
(一)兩種品牌群集群理論,不同的立論基礎
品牌群集群的基礎是產業集群。20世紀90年代Porter發現產業集群在國家競爭優勢中起著關鍵和決定性的作用,集群的發展和成熟會自然衍生出集群聲譽⑤。中國實施品牌戰略傳播的基礎是打造中國的品牌群,在此,我們可以通過考察產業集群的情況來品評不同品牌群集群模式的優劣。
(二)工業1.0和工業2.0時期,“單產業”簡單疊加的品牌集群模式
中國知名的產業集群,如“晉江鞋都”“廣東手機之鄉”等,看上去產業體量龐大,并且涌現了一批強勢企業,如“晉江鞋都”的安踏、特步、361°等龍頭產業,又如廣東手機之鄉的華為、小米、TCL、中興等龍頭企業。但是,這種模式的產業集群多為商品同質化集群。在晉江,百家鞋廠中僅幾家打出了牌號,并且還在遭遇“山寨”之名后,不少企業被市場“拋棄”。在珠三角,許多“山寨”手機通過抄襲品牌手機的研發設計,盡管可以做到功能齊全,甚至還可以增加某些超乎想象的功能,但制作工藝粗糙,質量無法保證。最嚴重的是,“山寨機”無法樹立自己的品牌,只會陷入價格戰的怪圈。這種產業集群雖有一定的分工,但終究是重復建設,隨著同質化程度增高,競爭也就益發激烈。為了爭奪更大的市場“蛋糕”,一些企業投機取巧模仿同行領先公司的技術,因此技術創新“惰性”肆意蔓延,企業的創新能動性極低。長此以往,該地區經濟增長不僅沒有得到預想中的增長,甚至因為擁擠效應而造成增長滯塞。在這種模式下,各個企業同處一個國內大市場,沒有形成梯形的產品鏈條,所以在應對國外成熟市場時缺乏統一有力的應對舉措⑥,終究要在世界市場敗退下來,其中的某些廠家最后也免不了煙消云散不知所終的結果。
產業集群如此,品牌的產生和品牌的集群也如此。李志起在《品牌:中國制造的唯一救贖》一文中談到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商業的“品牌”觀念:“品牌是什么?制造業一直規模化發展,就像是不斷圈地,而品牌要做的就是在這片地上蓋起高樓,進而成為地標⑦”。這種品牌發展與品牌集群模式猶如城市化初期的城市發展模式,從圈地到蓋樓,然后形成“地標”建筑;再圈地再蓋樓,然后又形成新的“地標”建筑,于是一座城市就在這樣的簡單重復中發展壯大,于是品牌也發展成品牌群。這是第一種品牌集群模式,可以看到,這種模式是工業1.0和工業2.0時期的產業集群所帶來的品牌集群模式,這種產業集群是通過空間拓展、生產機器或流水線簡單重復疊加以及勞動力人數大幅增長而達成的,本身缺乏內生性科技創新動力,發展的結果是許多同質性產業或者干脆破產消失了,或者被有科技創新能力的企業所兼并。
(三)工業3.0時期,“科技樹”成長的品牌集群模式
我們已經知道工業3.0時期產業規模的擴大不再依賴于生產空間的擴大和勞動力的增加來進行,那么這一時期的產業集群是怎樣進行的呢?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Perrour)在其《新發展觀》一書中提出了“大單位(LU)推進”模式。大單位的概念來源于:一個工業集團處于一種經濟空間之中,這個工業集團能夠像一塊磁鐵一樣地吸引一群其他企業和公司。大單位(LU)作為起支配作用的經濟單位,當它增長或創新時,能誘導其他經濟單位增長⑧。大單位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推進器的作用。也就是說這個區域空間內的大單位必須同時具有 “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其學生布代維爾則將佩魯的“增長極”定義擴充為相關產業的空間集聚⑨。這種模式多見于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
佛朗索瓦·佩魯和布代維爾提出的產業集聚模式是建立在區域經濟理論基礎上的,盡管后來的區域實踐證明佛朗索瓦·佩魯的理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不完全可行,但奇妙的是其理論在一個按經濟活動聯系所界定的空間內完全可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那是因為工業3.0時期的產業集群已經不再受區域限制,而是由科技創新所主導。我們可以借助佛朗索瓦·佩魯“大單位(LU)推進”模式來描述這一時期的產業集群:“大單位(LU)”猶如科技創新大樹的主干,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半導體理論和技術的發展,而在半導體主干上經“增長極”的作用長出不同的科技創新分枝,于是一棵大樹枝繁葉茂,欣欣向榮。想想當時的日本半導體企業松下、索尼、三洋、東芝、日立、夏普、三菱、先鋒、山水、jvc、富士、理光、佳能、美能達、愛華等產業群,就能明白這一道理。
(四)科技創新是打造品牌群的基礎
產業集群是提升國家以及區域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產業集群的發展過程是由產業集群萌芽、產業集群發展、產業集群成熟、產業集群升級四個時期組成,當達到產業集群升級時,就跨越為品牌群⑩。因此我們可以做出結論:產業集群的高級階段是品牌群。
通過對集群與品牌發展階段的考察,我們總結出一個現狀,歐美的企業善于將集群中的企業乃至不同行業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改造、創新等手段,最終形成大型資本集團,在強化自身母品牌的同時擁有諸多子品牌。而在中國,雖然許多區域形成了獨有的特色產業且地方產業集群遍地開花,但是這種產業集群仍是初級集群,單兵作戰,難以擰成一股繩。以至雖有諸多的國內品牌也難以走向國外。這對我們要打造一大批“高附加產業”品牌群以實施中國品牌戰略傳播是相當不利的。
現階段,在進入“中國制造2025”的征程中,提升中國品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首先,要以科技創新來引領產業集群的發展。其次,要通過產業集群的并購重組、改造創新以及形成品牌群來提升市場競爭力。第三,品牌群建立的過程,并不只是企業集聚的簡單品牌名稱疊加,而是通過產業集聚、科技創新并向國內外消費者、企業、集群、區域及國家通過一定的戰略,積極地、有計劃地宣傳品牌群的形象并以此構建“中國制造”新價值的過程。而這,也就是中國實施品牌戰略傳播的堅實基礎。
三、品牌戰略傳播對中國工業4.0發展的意義
(一)對內——以科技創新的高附加制造引領中國的品牌群塑造
2018年,美國掀起對華貿易戰,并污蔑稱“中國掠奪了美國的財富”。但實際上,美國從對華貿易中獲得極大好處,相當于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好多張皮。那么,美國為什么要和中國大打貿易戰,其直接目的,就是迫使中國荒廢其“中國制造2025”計劃。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一旦‘中國制造2025’計劃取得成功,中國將在微芯片、大型飛機、電動汽車和人工智能等尖端領域實現科技自主,到那時,美國只能向中國出口大豆、石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和能源?。”因此,如何在未來保持先進技術的主導能力,不僅與美國經濟安全息息相關,最直接影響的就是美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能力。
問題就在于,中國之前深度融入的發展戰略,是以自身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加入發達國家控制下的全球供應鏈,成為其中最大的低端制造環節。這使得中國制造2025之路任重而道遠。劍橋大學制造研究中心的Livesey教授認為:“制造業是英國的未來,這一未來基于獲得高附加值——對企業如此,對利益相關者和國家亦然”。高附加制造的企業是依靠高技能人才和知識密集型制造以獲得獨特價值和創新的企業,它不但有卓越的經濟績效,而且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且能夠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力?。
為應對歐美各國重塑制造業全球優勢的舉國戰略與行動,中國制造業不應是“求大求全”,不能鎖定在低端鏈條,應突破“價廉”的困境,中國制造業亟須通過科技創新,向價值鏈頂端加速邁進。2015年中國提出的《中國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的戰略,通過三步走戰略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最終實現綜合實力邁入制造強國的目的。2016年,財政部批準設立了經濟類重大研究項目“品牌價值提升工程”?,就是為了具體落實這一戰略目的。
(二)對外——以品牌群傳播來優化信息環境,提升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1.以品牌輸出回饋信息促進國內企業的科技創新。企業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根基。而企業競爭力的標志,其實就是世界品牌占有率。據聯合國工業計劃署統計,世界上各類品牌商品約8.5萬種,其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擁有90%以上的品牌所有權?,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缺乏著名的國際品牌,也就意味著在全球貿易中只能充當其他國家的貼牌生產基地,消耗本國資源、破壞自然環境、壓榨勞動力來賺取微薄的加工費。美國為什么經濟強大?就是因為美國不但是一個品牌大國,而且還是一個品牌輸出大國,其世界級品牌占全世界50%左右,這些品牌基本上是在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加工生產,成品后貼上其品牌標志,運到美國或直接經過其在當地公司的銷售網絡轉向各地發售。就是這樣,美國依靠品牌的輸出奠定了其第一經濟強國的地位。
說到底,企業競爭力就是企業的新產品研發能力。商場如戰場,品牌產品的輸出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一個適應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問題,有一個與當地品牌及其他外來品牌激烈爭奪當地市場的問題。這一切,都需要國內企業保持旺盛的生產斗志,及時分析與研究產品輸出后反饋的信息,及時采取應對的策略和措施。這一切,有利于促進國內企業加大對新產品研發的投入,有利于國內企業的科技創新。
(三)以品牌輸出帶動文化與價值輸出,優化信息環境,增強國家影響力
世界處在大變局中,技術創新將裹挾著新經濟和新政治力量崛起,同樣也是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期,但中國面臨的外部挑戰極大。首先,中國必須從經濟大國成長為經濟強國。要達到此目的,在提升經濟發展數量之際,要注重經濟發展質量。其次,中國必須突破美國對華的各種圍堵遏制,未來幾十年,中美博弈仍是全球事務的基調。中美之間不僅要在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競爭,還有諸如意識形態、文化影響、進出口貿易、全球國際事務話語權等方面的較量。第三,中國必須成功解決亞太地區臺海問題、南海領域等周邊爭端,同時,更要全面提升在中東、中亞、非洲、拉美、東歐的影響力。中國的戰略家們可以從約瑟夫·奈的提示中獲得啟發:“所有國家,包括美國,要學會通過新的權力源泉來實現其目標:操縱全球相互依存,管理國際體系結構,共享人類文化價值?”。換句話說,經濟上占據全球價值鏈的制高點,是政治上加強話語權的基礎。
實施中國品牌戰略傳播關系著我國強國地位的確立和穩定,當我們重視品牌群建設和品牌戰略傳播,有了大幅度提升的技術附加值和品牌附加值的高額貿易順差時,我們可以投入重金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可以投入重金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可以投入重金加大新產品研發與科技創新;可以投入重金扶持國內大中小企業引進更為科學的生產方式;可以為經濟建設營造更有利的氛圍環境。換句話說,實施中國品牌戰略傳播,提升中國品牌的技術附加值和品牌附加值,我們就可以有高額的貿易順差,用于大幅提升我國的經濟發展數量和質量,在貿易往來或者在解決國際事務爭端時,將能夠使我國擁有更多話語權。同時,也只有中國品牌做大做多做強并擁有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才能真正代表中國的崛起。
注釋:
①林炎志.工業4.0與中國社會的新挑戰[J].文化縱橫,2017,(06):46-53.
②王莉.德國工業4.0對《中國制造2025》的創新驅動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7,35(05):100-103+107.
③高望.中國如何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N].建筑時報,2015-04-16(005).
④耿楠.全球價值鏈的故事·系列之五“工業4.0”時代,全球價值鏈如何變革[J].世界知識,2015,(20):62-64.
⑤宋永高,何曉媛.是集群品牌無效還是不夠強勢?——基于消費者視角的集群品牌效應研究梳理和再解讀[J].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0(03):230-236.
⑥劉飛.日本企業集團模式對我國的產業集群發展的啟示[J].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07,(04):36-37.
⑦李志起.品牌:中國制造的唯一救贖[J].廣告大觀(綜合版),2010,(07):45-46.
⑧王劍芳.工業園區集成創新系統演化發展研究[D].昆明理工大學,2014.
⑨卞顯紅.城市旅游空間結構形成機制分析[D].南京師范大學,2007.
⑩張超.集群品牌:抱團向上正當時[J].中國品牌,2018,(10):9.
?單曉光.中美貿易戰中的知識產權問題分析[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17):18-26.
?陳勁,尹西明,趙闖.高附加制造:超越追趕的中國制造創新戰略[J].技術經濟,2018,37(08):1-10+19.
?劉平均.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J].工程建設標準化,2018,(11):20-23.
?王仙婷,王宗立.反壟斷視角下的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策略[J].商業時代,2009,(24):38-39.
?李智.文化軟權力化與中國對外傳播戰略[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0,(03):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