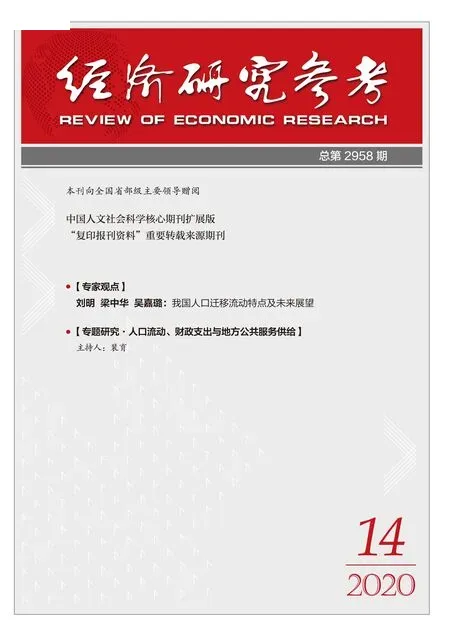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從價值重塑到價值創造*
焦 勇
制造業行穩致遠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壓艙石,尤其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部環境不確定加劇的背景下,制造業對國內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社會就業大局穩定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但是近年來中國制造業轉型面臨“兩端擠壓”的發展困境: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本被“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位置和低附加值環節的中低端制造業面臨越南、菲律賓等國家日益激烈的低勞動力成本競爭,愈發出現了“低端鎖不定”的新局面;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積極部署高端引領的“再工業化”戰略,依托創新驅動中國制造高端發展之路遭到發達國家的多重堵截,形式多樣的非關稅壁壘為中國制造業向高技術密集轉型筑起高墻,高端制造的競爭優勢仍處于不斷孕育形成的發展階段。除了“兩端擠壓”的發展困境之外,制造業自身的惡性競爭、低利潤率水平等問題進一步降低了民間投資熱情,在疊加國際、國內、產業等多種因素之后,制造業轉型面臨重重危機。
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正在深刻變革制造業的基礎理念,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依托開放共享與高效利用的數據資源,有效實現多樣化產品供給和異質性用戶需求的精準匹配,推動制造業從規模化生產向個性化定制的轉型,實現制造服務精準化和制造過程數字化。一是制造服務精準化。運用數字化優勢和互聯網優勢基礎,推動制造業模塊與下游服務業模塊相融合,提供更加個性化和精準化的產品和服務。海爾集團打造以實現顧客需求和顧客價值導向的物聯網生態平臺和系統,以“互聯網+”和智慧化實現產業升級與產品更迭。二是制造過程數字化。通過將制造過程與互聯網、大數據技術相融合,實現由傳統制造向智能制造、數字制造的轉型。青島紅領集團從制造端積極擁抱互聯網,打造互通互聯的智能數據共享系統,方便快速廉價地采集消費者的個性化體征數據,及時傳遞到服裝定制的各道工序。個性化數據成為支撐人機合一、生產個性化高效廉價運轉的靈魂。依托累積形成的大數據優勢,服裝版型設計從原本昂貴耗時的設計師創作轉變成為大數據自動匹配的過程。發生在中國制造業變革領域中的眾多故事充分表明,數字經濟成為賦能制造業轉型的關鍵。
從制造業產業鏈看,數字經濟在制造業中的運用程度存在“U型”曲線關系。制造業研發設計端和銷售端的數字化程度較高,制造環節的數字化水平不足。同時,即使是數字化應用程度較高的制造業兩端,依然面臨嚴重的外部依賴特征,這里存在兩項重要證據:一是芯片高度依賴進口,2018年中國進口芯片達到4175.7億件,進口金額達到3120.6億美元;二是構成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內核與基石的工業軟件長期處于高度依賴進口的局面,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仿真等工業軟件開發水平嚴重滯后于發達國家。總之,數字經濟在制造環節和制造工序中的運用程度和創新水平仍顯不足。
一、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維度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包含“投入—產出—企業—產業”四個維度,分別為“從要素驅動到數據驅動、從產品導向到用戶體驗、從產業關聯到企業群落、從競爭合作到互利共生”的四個轉變,構成制造業新模式、新業態和新理念的重要支撐。
(一)從要素驅動到數據驅動
制造業演變的歷史長河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無非是資本和勞動,在此基礎之上資本逐步拓展成為機器設備、廠房、原材料等,而勞動力則不僅包含熟練的產業工人,還包含富有管理技能的管理人員、富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建立在經典的生產模式之中,通過“流水線”將分工效率發揮到極致,以大規模生產降低制造業的固定成本,同步實現制造業物美和價廉兩個維度的訴求。數據并沒有成為制造業發展的要素,數字化也一直成為輔助原材料采購以及制造業產品銷售的渠道而加以利用,成為輔助制造業發展的一項便利因素,并沒有深度參與制造過程與制造環節。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第一個維度體現在從要素驅動向數據驅動的轉變。隨著數字化的深度發展,數據正在充分滲透到制造的各個環節,成為變革制造理念的關鍵變量,推動制造業企業生產投入實現了從要素驅動到數據驅動的轉變。數據資源同勞動、資本、能源一樣,已經成為必需的資源,并且成為賦能型企業構建的重要基礎,是提升制造業企業效率的關鍵。隨著經濟社會持續演進,逐步形成的海量數據因缺乏整合而沒有獲得充分挖掘與利用,企業為了獲得有效數據資源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極為高昂。所以在充分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以各級政府數據公開共享為引導,逐步推動行業、企業與消費者數據的合理公開,推動數據資源的合理流動,為多樣化的人工智能應用情境提供基礎支撐。從創新資源整合集聚看,以數字化推動創新元素的充分集聚,建立健全制造業數字化創新投入、創新產出與創新應用體系。同時,數據還需要同其他各種要素之間達到協同發展的狀態,協同推進服務于制造業轉型大局。
(二)從產品導向到用戶體驗
在傳統制造業的發展理念之中,產品導向極為重要,這是因為在追求規模經濟與追求差異化產品兩者之間,規模經濟成為企業考慮的首要因素。在汽車制造業利用福特制大幅度降低汽車生產成本時,顧客對產品的個性化需求交給了制造的最終環節——噴漆。追求極致的制造過程并生產大批量的產品,從而占領市場份額成為重點,顧客的個性化需求往往被抑制。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第二個維度體現在從產品導向向用戶體驗的轉變。制造業的發展逐步破除以生產過程、最終產品為核心,轉而以滿足用戶需求、用戶體驗為原動力。所以,判斷制造業轉型的如何、升級的好壞,最重要的是能夠讓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或享受服務中得到滿足。“用戶體驗”是在不騷擾、不產生厭煩情緒的基礎上滿足用戶需求,并令其在消費過程中感受到高興、愉悅,甚至驚喜。成功的用戶體驗應該使產品設計更契合用戶需求,通過信息與數據的黏合,考慮產品構造、功能質量和用戶情感,實現從增加供給數量到提高供給質量的轉變。當然,基于制造業接續轉換的實際要求,制造業既要考慮到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又要兼顧規模生產的成本優勢,并且擁有龐大的人口規模與用戶基數,推動制造業“適度規模定制”將成為制造業轉型的未來方向。為此需要以消費者需求的多維數據為支撐,通過將多維數據進行跨層次整合,利用多變用戶共生依賴和互補創新,實現提升用戶價值的目標。
(三)從產業關聯到企業群落
制造業關注于產業的關聯性以及產業的區域集聚發展特征,企業的連接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是產業維度的產業關聯和地理維度的產業集聚。這種發展模式的確會促進生產技術效率的提升,但是也會面臨路徑依賴、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企業之間的連接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與剛性雙重特征,企業存續暴露出較多的外部風險。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第三個維度體現在從產業關聯向企業群落的轉變。制造業內部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競爭或者合作的關系,而是形成以平臺為主導的企業群落,企業之間從“產業關聯”“地理集聚”等傳統連接關系走向“產業生態”“虛擬集聚”的新型連接關系。平臺本身即為重要的數據、技術的集散中心,具有開放特性,各要素捆綁所形成的經濟利益激勵著企業群落內部打破“信息孤島”的藩籬。基于數字經濟發展、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現實,企業群落成為制造生態豐富與發展的具體表現,形成依附于平臺型核心企業的眾多中小企業。從功能看,企業群落主要有兩種類型,分別是上游支撐企業群落和下游應用性企業群落,并且兩種類型企業群落的數量較多,共同形成“啞鈴型”結構。制造業企業的逐步發展不單純依據企業的投資意愿、企業的經營利潤,更多地需要根據制造業生態演化并融入特定生態位,形成抱團取暖的企業群落。
(四)從競爭合作到互利共生
在傳統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中,推動產業規模提升、產業集群發展、產業鏈延伸成為重要手段。這些手段主要是通過利用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范圍經濟等形式,帶來制造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生產成本的降低,但是它們均沒有逃脫已有的發展模式桎梏,制造業發展的本質特征和基本邏輯并沒有改變。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這些手段可以達到特定的發展目標,但是可以挖掘的發展潛力也愈來愈小。已有發展模式中,競爭與合作構成兩種重要力量,若是將制造業比喻成為生態系統,那么處于相同位置上的制造業企業則面臨競爭關系,而具有互補特征的企業——例如制造業互補商則處于合作關系。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第四個維度體現在制造業生態領域,實現從競爭合作向互利共生的轉變。第一,隨著數據資源逐步成為推動生態系統演化的關鍵資源,在系統中起到支配作用的企業充當平臺的作用,呈現出平臺內“共生”與平臺間“競爭”的關系。平臺內部企業之間處于共生關系,雖然企業處于系統的不同位置,但是用戶體驗是它們所追求的共同目標。不同平臺企業之間處于激烈的競爭關系,例如B2C市場中的天貓、京東和拼多多三家電商平臺,處于激烈的競爭狀態。第二,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走向互利共生的復雜關系具有內在穩定性,形成價值共創的有機整體。不同平臺型核心企業和上下游企業群落之間具備穩定的共生關系,平臺內的參與主體的共同目標是提供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與服務。不同平臺型核心企業之間則存在穩定的競爭關系,并且這種競爭關系不僅是平臺型核心企業的競爭,更是標準、規范、系統之間的競爭,競爭落后的代價不僅是平臺型核心企業的衰落,更是以平臺型核心企業所提供的技術標準、框架結構、生態系統的整體衰落。
二、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路徑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根本方式在于融合,推動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多維融合發展。所以應堅持數據驅動、創新驅動、需求驅動和供給驅動四輪驅動戰略,引導制造業與互聯網、研發端、服務業、新技術深度融合,為制造業轉型提供強勁動能。
(一)數據驅動制造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
制造業的本質遵循福特制,流水線生產是實現規模經濟的重要手段。面對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世界經濟潮流,制造業需要充分對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大力推動工業互聯網的創新發展,以互聯網思維促進精準服務和定制化服務成為主流形態。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第一要義是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外部性,降低信息不對稱,推動制造業銷售和采購渠道互聯網化。第二要義是發揮互聯網所提供的大數據資源優勢和云計算算法優勢,促進制造業發揮“1+1>2”的協同效應,推動產品生產更加契合需求類型和需求層次,營造智能生產和智慧制造蓬勃發展的局面。第三要義是充分發揮互聯網、大數據在制造中的主觀能動性,變“冰冷”“機械化”的制造過程為充滿創新、充滿創造、充滿期待的智慧過程(1)依托互聯網進行深度學習,初始階段互聯網憑借人類經驗進行學習,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人類所掌握的知識,進而輔助制造業更好更快地發展,但是這種模式仍然需要憑借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在既有的認識框架下輔助設計與制造產品。高級階段互聯網通過程序設計在設定情景中自主學習,從而突破已有認知框架的限制,在窮盡多種可能之后,創造出令人驚喜的思路、方案、設計和產品,這也是制造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的未來方向。。
(二)創新驅動制造業與研發端深度融合
依靠數字經濟推動全域視角下研發力量的整合,促進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業態創新和制度創新煥發制造業蓬勃生機。制造業的創新發展絕不是短時間的政策供給和資金投入就能夠獲得重大突破的,技術訣竅的掌握是從0到1再到2不斷爬坡過坎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長。19世紀的“德國制造”還是區別于“英國制造”而被嘲笑的低端品牌,在細分得極為狹小的領域內經過長達百年的歷史傳承與發揚,德國制造才逐步成為高端制造的代表,眾多隱形冠軍企業也僅僅是在單一制造產品中獲得絕對優勢地位。所以制造業轉型需要做好長期“臥薪嘗膽”的思想準備,沉下心來修煉內功。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繼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工作,推動制造業獨角獸企業發揚工匠精神,精細培育懂技術、愛鉆研的專業人才隊伍,塑造精細制造和品質制造的涓涓細流,最終匯聚成為制造業高端發展的生命之洋。同時還需要培育全社會推崇企業家精神的氛圍。制造業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瞬移,需要長時間潛心鉆研與傳承,需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干、勇毅篤行的企業家,不為熱點領域所動,不為一時快錢吸引,不為資本市場裹挾,讓制造業發展回歸制造、回歸產品、回歸服務。
(三)需求驅動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
加快制造業服務化并不是“去制造業”,而是充分依托數據資源,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更好地利用數據要素完成制造過程與需求滿足過程的有效對接與無縫銜接。所以制造業轉型既需要“上檔次”,著重依托創新驅動和數據驅動;也需要“接地氣”,加深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制造業服務化的第一要義是投入服務化,制造業的投入要素從資本、勞動不斷向技術、服務要素轉移,加快制造環節與研發設計、市場調研、物流、管理咨詢等與之相匹配的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制造業服務化的第二要義是產出服務化,直接面對消費者需求的生活資料生產的行業中,提供有形產品僅僅是完成其中的一個環節,而消費者需求的滿足包含大量與之配套的相關服務業。加快提升制造業產出服務化水平與層次,高度重視制造與售后服務、維修保養、金融租賃等服務的融合,使制造企業的重心從產品生產向關注消費者需求轉變,向綜合性解決方案提供商轉變,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
(四)供給驅動制造業與新技術深度融合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延伸方面也是大有作為的領域,就是推動制造業與新技術的融合發展。例如,數字經濟變革制造業“減材制造”模式,實現以“3D打印”技術為基礎促進“增材制造”手段蓬勃發展,推動3D打印技術在生物醫療、工業設計等領域的運用,尤其是以樹脂、塑料以及生物材料為主,生產具有高精度、復雜化結構的工業模型等產品。又如,洛克汽車公司(Local Motors)的汽車外觀是由3D打印技術完成,從而高效廉價地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智能化生產等新技術將會促進制造業的變革與融合,制造業的發展不僅需要埋頭苦干,專注于行業內的技術創新,還需要會干巧干,抬頭看路,以積極與變革的心態擁抱新技術,抓住新機遇,引領新發展。
三、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第一,數字經濟的影響逐步從彌合信息不對稱轉向信息創造,數據也逐步演化成為一種賦能制造業轉型的關鍵生產要素,走向直接參與制造環節與制造工序。基于數字經濟的新特征和新趨勢,數字經濟逐步從帶來既定社會福利的重新配置轉向促進社會福利的提升,實現發展初期導致價值重塑、長期影響帶來價值創造的作用機理,從而構建了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理論基礎。
第二,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基本模式主要包含四個維度,分別為:從要素驅動到數據驅動、從產品導向到用戶體驗、從產業關聯到企業群落、從競爭合作到互利共生。依托數字經濟實現以用戶體驗為內核的制造業發展目標,推動形成以適度規模定制化的未來制造模式,制造業企業之間不再是產業層面和地理層面的連接,而是形成了以制造業生態系統為基礎的企業群落,制造業生態不再是簡單的競爭合作關系,而是走向了更加復雜的互利共生關系。
第三,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的四條路徑。一是堅持數據驅動制造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以互聯網思維促進精準服務和定制化服務成為主流形態,發揮互聯網所提供的大數據資源優勢和云計算算法優勢,使得“冰冷”“機械化”的制造過程成為充滿創新、充滿創造性、充滿期待的智慧過程。二是堅持創新驅動制造業與研發端深度融合,依靠數字經濟整合研發力量,促進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業態創新和制度創新并煥發制造業轉型蓬勃生機。三是堅持需求驅動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加快制造業服務化并不是“去制造業”,而是充分依托數據資源,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更好地利用數據實現制造過程與需求滿足過程的“有效對接”和“無縫銜接”。四是堅持供給驅動制造業與新技術深度融合,制造業轉型不僅需要專注行業內的技術創新,同時還需要以積極與變革的心態擁抱新技術。
(二)政策建議
第一,提升制造環節與工序的數字化水平。制造業數字化不僅體現在采購與銷售等兩端環節,更應該聚焦于制造環節與制造工序。切實將大數據、互聯網的優勢運用到制造過程中,打通制造業不同設備、系統、數據和網絡的內在關聯,推動信息技術在制造業中的普及程度和融合創新程度,形成依托于信息互聯互通的制造業綜合集成系統,實現對客戶需求的實時感知與快速響應。推動信息技術與技術工藝、智能裝備、經營管理的深度融合水平,實現制造業全流程信息共享、實時交互和業務協同。充分發揮信息技術整合優化各類要素的優勢,實現跨企業、跨產業、跨區域的網絡協同,構建開放式組織體系。
第二,探索數字經濟賦能的制造業新模式。大數據海洋成為未來制造業最為重要的關鍵生產要素,而后通過云計算對海量數據的優化處理能力,實現數據化制造、智慧化制造模式。運用數字經濟突破產業鏈與價值鏈的垂直分布態勢,重組制造業內部各種要素,實現制造業要素橫向高效組合,進而形成制造業獨具競爭力的商業運行模式。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傾向于多產業的創新融合,推動數據資源和多種要素的共生共享,創建新產業生態系統,形成制造業全新的發展模式。
第三,培育數字經濟賦能的制造業生態。充分利用數字經濟賦能的強勁動能,推動制造業深度融合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實現制造業的衍生升級。依托于制造業與互聯網、服務業的跨界融合,以精準的數字化服務提升制造業個性化水平,大力培育發展數字經濟賦能的制造業新業態,實現跨時空的制造業服務化轉型。準確把握科技發展前沿趨勢和經濟發展脈絡,聚焦人工智能、物聯網、車聯網、虛擬現實、高端軟件、集成電路、量子技術等領域,推進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異軍突起,加速集成系統的創新性技術體系,為制造業領域新產業的發展提供技術基礎。
本文原載于《經濟學家》2020年第6期,轉載過程中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