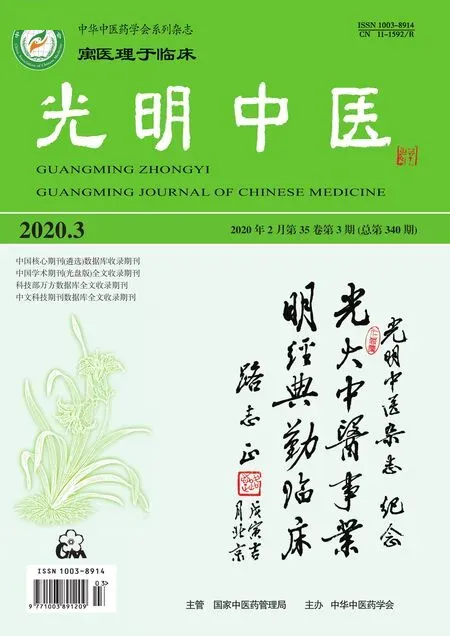基于腸腦互調學說探討針灸治療失眠的應用
李 杰 杜 華 魏海霞 劉文超
失眠是神經內科常見病、多發病。中醫稱之為“不寐”。臨床表現主要為:難以入睡、睡后易醒、多夢、睡眠深度不夠,甚至徹夜難眠等。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生活壓力增大,人們的精神壓力逐漸加大,長期處于緊張狀態,得不到放松,使失眠的發病率逐漸上升,嚴重影響生活質量和日常工作。有文獻報道[1]:我國人群中45.4%的人存在睡眠障礙的問題,并且與抑郁或焦慮性心理障礙成正比。失眠及其相關性疾病也在逐年增加。睡眠醫學作為生命科學的一門重要邊緣學科,已經得到了世界的廣泛關注,《Science》主編預言:睡眠及其基礎研究,將成為21世紀神經科學的兩個至關重要的領域之一[2]。“胃不和則臥不安”,歷代醫家研究認為胃腸是人的第二大腦。本文基于腸腦互調學說探討針灸治療失眠患者的作用。
1 腸腦學說
20世紀,腦腸肽的發現成為醫學生物界為之一振的亮點。1931年在腦和腸內同時發現Pomder物質,顛覆了神經肽物質只存在腦中,胃腸道不存在神經肽物質的觀念。由于P物質在腸神經叢和黏膜下神經叢中的含量很高,因此對胃腸道平滑肌有較強的刺激作用。由此人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腦腸肽(Brain-gut peptide),指的是一些既存在于胃腸道也存在于腦組織的活性物質,因為他們的化學結構均屬聚的多肽(polypeptide),所以將這些具有雙重分布的肽類稱為腦腸肽[3]。近些年來國外有些醫學家認為腸道的神經元環路就是一個獨立的大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解剖和細胞生物學系Dr.Gershon MD提出第二腦學說,人類除大腦外,還有第二大腦,又稱腸腦或腹腦,它處理人體的大部分消化功能[4]。特別是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功能研究的不斷進展,中樞和外周各級神經元、神經網絡、神經遞質、受體以及腦-腸肽、腸神經系統和神經-內分析-免疫網絡研究的新發現不斷提出,使醫學界對腸-腦學說有了全新的認識和深刻理解。
2 腸腦學說對失眠的影響
失眠并非是一個獨立的疾病,胃、腸器官等消化系統分布有豐富的自主神經纖維,心理應激與生理反應之間通過自主神經、激素、神經遞質等中介物質溝通調節胃腸功能[5]。病因較多,生理-心理因素、遺傳基因、自身素質、環境條件、社會人際關系、精神刺激、軀體疾患、精神疾病等都可引起,這些均能導致腦內睡眠中樞部位及功能發生異常,或由此導致神經生化改變,促使睡眠結構和進程出現紊亂。胃腸道由中樞神經系統(CNS)、腸神經系統(ENS)和自主神經系統(ANS)共同支配。腸和腦通過ANS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來進行雙向調節,調節胃腸道功能的重要部位是大腦邊緣系統,主要是針對恐怖回避、社交、學習能力等方面進行調節,在情緒調節方面也有關鍵作用,情緒及其相連的心理活動均由邊緣系統進行調節。另調節人體睡眠-覺醒周期、生物節律的松果體素也在腸腦內雙重分布,同時對胃腸道的消化蠕動有重要的調節作用。
歷代醫家開始越來越關注胃腸道疾病與失眠的關聯性,之前認為只有在腦內才會存在的肽類物質被發現在胃腸道中呈雙重分布,與睡眠密切相關的5-羥色胺、血管活性腸肽、膽囊收縮素等,揭示了“胃不和則臥不安”的機制[5]。
《素問·逆調論》言:“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逆,胃氣不得順從而下,故不得平臥。 另一種解釋是指由于胃腸道功能失常而出現不能熟睡、多夢等病癥。胃主通降,“其氣亦下行”,其“道”乃通降之道,飲食不節,腸胃受損,宿食停滯,痰火上擾,使胃氣不和,不得從其道,而導致“臥不安”。目前,腸腦互調對失眠的研究還較薄弱,系統深入研究其相關性,為臨床指導失眠的治療提供新思路。
3 針灸療法對失眠的作用
針灸作為中醫特色療法,其治療失眠效果顯著,并且產生的不良反應少,花費的費用較低。通過中醫辨證,審證求因,辨證施治,調節身體陰陽及臟腑氣血平衡,調暢氣機,使體內陰陽氣血調和,肝氣調達,疏泄協調,氣血充盈,使心有所養,神有所安,睡眠自然就得到了改善。在現今社會,在人們越來越注意養生保健的情況下,針灸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愛。現代學者非常重視運用“胃不和則臥不安”理論來調理脾胃以安神。脾胃為后天之本,津液生化之源,精微物質充足,濡養髓海清竅,神奇充足,機體敏捷,針刺的選穴組主要有天樞、中脘、足三里、神庭、百會等。針刺方法有頭針、腹針、臍針等。李黃彤等[6]采用薄氏腹針,選用中脘、下脘、氣海、關元、雙滑肉門、外陵等,治療失眠患者94例,有效率達到85.48%;葉天申等[7]采用引氣歸元方法選穴下脘、中脘、關元、氣海等,療效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黃石璽[8]采用“脾胃十針”由金針王樂亭的“老十針”變化而來,選用胃之募穴、八會穴之腑會中脘,陽明經的合穴足三里,大腸之募穴天樞,起到和胃健脾、通降腑氣,升降氣機,斡旋上下,每療程5~10次,失眠諸癥皆除,夜夜安眠,效佳。王照浩老中醫認為失眠的病機為陰陽失調、陽盛陰衰,五臟功能紊亂,治療上從整體入手,通調陰陽,采用體針配伍,陰陽經并取,達到調整五臟、宣通氣血、寧心安神[9]。
4 從腸腦互調學說探討針灸治療失眠
在腸腦內雙重分布的神經遞質對調節人體睡眠-覺醒周期有著重要在作用,與睡眠密切相關的5-羥色胺、血管活性腸肽、膽囊收縮素等,去甲腎上腺素的含量增多會增加興奮性,減少總的睡眠時間。很多細胞因子也都參與了睡眠-覺醒的調節例如腫瘤壞死因子、白細胞介素-13等,也是調節睡眠的重要物質[10]。鄭利星[11]常用含有5-羥色胺類藥物的鎮靜催眠藥物,可縮短入睡的時間,增加總睡眠時間,減少覺醒的頻率。 尹嶺等[12]采用fMRI-BOLD/FDG-PET腦功能成像方法,觀察針刺右側足三里穴,發現可引起視丘腦下部、同側室旁核和雙側顳葉以及腦干的葡萄糖代謝及腦血流增加。王嫣等[13]通過用溫針灸治療失眠大鼠的三陰交、百會、神門穴,測定其腦干內5-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及鹽酸多巴胺的含量,結果表明溫針灸可通過提高5-羥色胺的含量、降低去甲腎上腺素及鹽酸多巴胺的含量從而改善睡眠。觀察電針“足三里”對失眠大鼠的胃電及腦腸肽的影響,結果表明,電針“足三里”可以使胃電活動增強,同時胃活動的增強與有關的腦腸肽含量增多有同步效應[14]。
5 結語
古人提出“胃不和則臥不安”,表明在古代已開始注重從脾胃方面論治失眠。現代的“腦腸肽”“腹腦”學說及相關的實驗研究也為此提供了理論依據。基于腸腦互調學說,在失眠針灸治療中,辨證選穴,兼顧調和脾胃,氣血化生有源,脾胃升降有序,營衛巡行有度,陰平陽秘,則可達到安神靜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