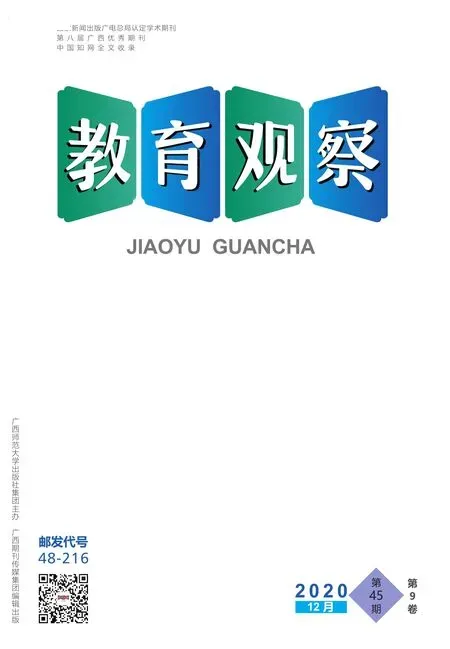地方高校慕課學習者在線學習的問題及對策
——基于教育系統論的研究
鄧鳳池
(廣西財經學院國際交流處,廣西南寧,530007)
一、研究背景
井噴式發展的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慕課)被認為是教育信息化的典型技術,正推動著教育系統的變革。美國Coursera平臺學習者數量2019年增長800萬,達到4500萬。美國edX平臺學習者數量2019年增長600萬,達到2400萬。英國Future Learn平臺學習者數量2019年增長130萬,達到1000萬。[1]截至2019年8月底,中國上線慕課數量增長到1.5萬門,學習人數上漲至2.7億人次。
2020年春季學期,為阻斷新冠肺炎疫情向校園蔓延,確保師生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全國高校工作者及學生響應“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的號召進行線上教學。但是,對地方高校學生訪談的結果顯示,學生實際學習效果并不理想。調查結果顯示,在線學習者遇到的三大問題為不知選擇哪門課程、無處請教和放棄完成課程。要解決在線學習者的問題,除了大多數研究者從學生的角度進行關注和探索,教育系統論中其他參與主體,即本校教師和管理層的聯動參與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從本校教師和管理層的角度出發,提出相應對策,以解決在線學習者的問題,最大限度地發揮慕課平臺的教育作用。
二、系統論概念的厘定
學者趙文華對系統論歸納出如下幾個理解要點[2]:(1)系統總是由兩個以上相互聯系和彼此影響的部分構成的集合體;(2)系統總是具有一定的界限,既把系統與環境區分開來,又促使系統與環境不斷地進行能量、信息與物質的交換;(3)系統雖然是由相對獨立的各個部分組成的,但卻是具有一定功能和特性的有機整體。
(一)教育系統論的概念
伯頓·R.克拉克(Burton R. Clark)于1983年出版的《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是用系統觀點研究高等教育的典范。[3]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高等教育界也逐漸把系統論觀點引入高等教育管理領域,極大地促進了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學化。教育系統論是教育學與系統論相結合的產物。
教育系統在與外在環境發生接觸與交換的過程中,能自動產生一種自組織現象,即系統的各個主體都能夠隨著外部環境的影響和刺激,共同做出調整,形成相互協同的內部穩定狀態。即使不存在強烈的外在沖擊,高校這一教育系統內部的各主體也能夠憑借相互之間的作用產生均衡。這種均衡的狀態既不容易被外界打破,也不容易由內部某一主體的單一力量改變。因此,要解決慕課學習中出現的問題,不能僅靠學生單方面的努力,還需要系統中的其他主體,即教師隊伍和管理層的合力,才能解決問題。
(二)教育系統論中三大主體的關系
外在的環境和技術的根本發展要求教育系統參與主體紛紛進行自適應的調整。當尋求解決教育系統的主體之一——學生的問題時,還應考慮教育系統中的其他主體——管理層及教師的聯動與共通,要看清內在聯系和利用外在作用力,做到全局發展,統籌建立具有適應性與發展力強的教育系統。
從教育系統理論來看,學校是開放的自組織自適應系統,學生、教師隊伍和管理層會同時面臨外部環境的影響和刺激。三者雖然都是教育系統的內部主體,但不是閉環的關系。本研究認為三個參與主體處于一個開放體系之中,相互制約和影響,如圖1所示。外部環境對學生主體的影響不是全部直面沖擊式的,而是處于遠離外部環境影響的中心區,大部分還是在學校和教師的半包圍下。作為學校內部的其他主體,教師和管理層承擔著對學生進行引導、監督、調整和保護等責任,幫助學生抵御外部環境的直接沖擊。

圖1 教育系統參與主體與外部環境的關系
三、在線學習中學生遇到的三大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量的慕課資源向大學生瞬間開放,原本還是純線下教學或以線下教學為主、線上教學輔助的混合式教學模式被迫轉為線上教學和慕課自主學習的模式。相比于本校教師的線上教學模式,線下教學具有課堂點名、同學互助、教師及時提問和解答等優勢,慕課的自主學習凸顯劣勢。本研究及時跟進并調查了學生利用慕課進行學習的情況,發現存在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一)不知道選擇哪門課
面對慕課,學生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不知道選擇哪門課。慕課的優點之一是囊括了全國領先甚至世界一流的網絡課程,但這個優點如果不能正確利用就會變成缺點。當學生登錄慕課平臺選課的時候,同一門課出自不同的名校,選擇頗多且課程質量有保證。不過,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教師往往把慕課平臺理解為實現學生自由選擇的課程市場,意在鍛煉學生根據自身的需求和水平進行選擇的能力,引導或者強調以學生自身的學習求知興趣為出發點,避免為學生選課提供強制性和干預性的建議。這種好的出發點在實際應用中會遇到困難。對于那些還沒有系統學習過這門課程的學生,由于缺少了解,不知道各大名校的同一門慕課各有哪些側重點,更不知道哪所名校的慕課適合自己的學情。他們最后簡單地選擇名氣最大的學校的課程,這樣滿足了好奇心卻很難滿足求知欲。這種無指導的課程選擇與地方高校學生的學情不匹配,學生跟不上教學進度,帶著求知欲探索名課,卻產生了更多的疑惑。一位接受調查的學生反饋:“我一開始很興奮,我居然可以聽清華大學的老師的課。但沒開始幾分鐘就跟不上了,感覺老師講課很跳躍,很多聽不懂。”可見,學生選擇了與自己學情不符的課程,事倍功半。
(二)無處請教的苦惱
在學習慕課的過程中,學生會遇到不懂的問題,可由于他們往往是獨自挑選的課程,與其他同學的選擇很可能不一樣,因此向其他同學請教與交流的機會就會被切斷。慕課的主講教師又不能保證回復所有學生的所有問題,或者是借助媒體網絡的交互功能進行答疑,很難達到線下面對面傳授、探討的效果。最后往往是學生找不到合適的對象答疑解惑,不懂的問題繼續不懂,從而形成了學習無助的困境。一位接受調查的學生說:“因為在家上課,所以我們沒有和教授這門課程的本校老師見過面。我不熟悉慕課的老師,不想也不敢問問題。”學生的膽怯心理、慕課教師的責任心、慕課平臺的技術水平等都只是表面的原因,無處請教的苦惱歸根結底是學生不認為與慕課教師存在真切的師生關系,慕課脫離了本校的教師,學生與教師之間的紐帶被切斷了。真正與學生存在師生關系的是學生所在高校的教師,而不是慕課平臺上的教師,因此,后者對學生沒有每問必答的義務,且慕課學生眾多,實際操作上也做不到每問必答,反而是本校教師有義務回答學生的提問。而且,不同層級的高校,學生的學習水平也不同,我們無法要求普通學校的學生完全理解重點大學的教師授課知識點、知識面和知識深度。
(三)不能堅持完成課程學習
調查發現,所有的學生都在慕課平臺上聽過課,但能夠認真完成一門課程的學生其實很少。雖有學生認為上文中提到的兩大困難都沒有給自己造成困擾,但他們也不能認真完成一門課程的學習。一大半的學生學習中途就放棄認真上課了,一小半的學生能夠堅持學習,但課后作業和考試應付了事。多數學生反映,他們為了完成學校安排的任務,把慕課視頻打開放在身邊,調成靜音,然后就做別的事情去了。一位接受調查的學生分析道:“其實課程還是很好的,我能學到很多東西。但我在家學習的效率是很難維持的,一段時間好,一段時間差。”這說明無論慕課設計得多么精彩,如果沒有本校教師的監督和學校營造的學習氛圍,學生僅憑自身的自制力是很難認真完成慕課學習的。
盡管不少慕課平臺為了防止這種現象,安排了課程中的做題環節,學生只有把題目做對了才能繼續聽課,但學生之間可能會相互串通,泄露答案,因此,做題并不能確保達到使學生認真聽課的目的。大學生的自制力尚在培養階段,寄希望于靠自覺、靠技術監督,以此代替本校教師在同一間教室對學生的監督和指導,在實踐上存在漏洞,很難達到使學生學有所得的效果。
四、從本校教師和管理層的角度解決問題
針對在線學習者學習中遇到的三大問題,本研究從教育系統論的角度出發,聯動本校教師和管理層合力解決學生的問題,提出如下對策:(1)教師做好慕課課前、課中和課后的指引和監測工作。(2)管理層建設適合地方高校特色和學情的資源庫,從戰略上支持技術輔助學校的發展,為慕課平臺與地方高校學生的對接提供思路。
(一)本校教師的支持
需要承認的是,學生已有的知識結構、理解能力不足以支撐自己在慕課上選課的能力,最主要的問題他們是不知道選擇哪門課。[4]在網絡時代,“知道從哪里學(know where)”變得比“知道什么(know what)”和“知道怎么做(know how)”更為重要。學生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教師的介入,而且需要教師指引學生打開哪一扇知識的大門。學習的核心要素已經不是沉浸在某一個知識點本身,而是知識管道的打開和知識聯系的建立。[5]對教師而言,學習材料的組織、選擇和實施需要從教學實踐出發,從導學目標、導學內容、認知風格等方面進行整體考慮,避免出現信息過量、學習者無法有效接收等問題,教師可為學習者提供良好的知識網絡流程圖。針對學生學習慕課失效的問題,本研究提出教師的幫助途徑如下:(1)教師扮演慕課推薦者的角色,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根據學生的學習水平、學習階段甄選合適的慕課資源,助力學生勞有所獲、學有所得。(2)教學交互以線下進行為主。現有的慕課與學生的交互停留在內容單一和較淺的層次上,暫時不能期待用互聯網技術來徹底解決,還需要本校教師進行深入、充分的交互,輔助學生求知解惑,定期以固定形式向學生征求問題,而不是坐等學生前來提問。(3)作業測試可監測學生完成學習任務的積極性,完成作業是學習知識的直接體現。教師可通過布置和檢查作業,發現學生在慕課學習中尚未熟練掌握的知識,查漏補缺,彌補學生自學慕課時尚未發現的不足。
(二)管理層層面的支持
與國外不同,中國慕課平臺建設呈現出高校自主建設、校企聯合建設、企業獨立建設等多元性的特征。[6]例如:以清華大學的“學堂在線”為代表的高校獨立建設和運營的組織模式,以北京大學和阿里巴巴聯合打造的“華文慕課”為代表的校企聯合的組織模式,以上海市60所高校加盟建立的“上海高校課程資源共享平臺”為代表的高校聯合的組織模式,以44所“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建立的“東西部高校共享聯盟平臺”為代表的區域聯盟的組織模式,以網易的“網易云課程”為代表的企業獨立建設和運營的組織模式。
現階段,國內越來越多的教育機構認為,有必要從戰略層面支持慕課的平臺建設,相關的政策也由純慕課平臺向慕課轉型和線下教學模式混合發力。但地方高校管理層的行動力還非常有限,其主要措施僅僅是引進已有的優質慕課資源平臺,少有高校主動組建和打造具備自身特色和符合學生學情的資源平臺。地方高校的管理層應提供必要的政策、規劃、資源、課程設計等方面支持,這也是確保學生混合式學習能夠取得成功的保障。[7]機構層面對混合式教學的戰略支持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成效,而且能夠幫助機構實現增加資源獲取渠道,保證教學的靈活性,提高效益。
地方高校管理層支持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慕課資源共享池,屬于智慧化校園建設的范疇,也是學校教育系統在信息化背景下的適應與調整。在現階段,可以理解地方性高校不能獨立承擔慕課平臺的建設任務,但不排除同類型、同級別的高校組建聯盟,把資源共享池的入口建立起來,以鏈接到各平臺海量慕課。該資源共享池的慕課不是單純的又一個慕課資源平臺,而是基于地方高校特色及學生學情的適用性平臺,可以實現地方高校與慕課平臺的有效對接。
五、結語
本研究歸納了地方高校學生學習慕課的過程中遇到的三大問題,并提出了對策:要把慕課學習放進高校教育系統的整體進行分析,把高校視為一個系統,從參與教育系統的教師和管理層的角度出發,共同解決學生在線學習的問題。教師由“投喂”的角色轉變為參與和協助慕課落實到自己課堂中的角色。教師應采用甄別慕課資源、線下交互答疑解惑、課后作業夯實知識的方法助力學生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穩步發展。地方高校管理層應進行頂層設計,擬定規劃,制定制度,著力建設符合地方高校自身特點的資源共享池。要讓地方高校管理層參與進來,支持教育信息化,也要讓教師不再游離于學生和慕課之外,而是成為參與者與引導者,協助學生學習。因此,教師和管理層協同工作是解決學生問題的外圍支持,確保了內部問題解決的多管齊下,保障了教育系統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