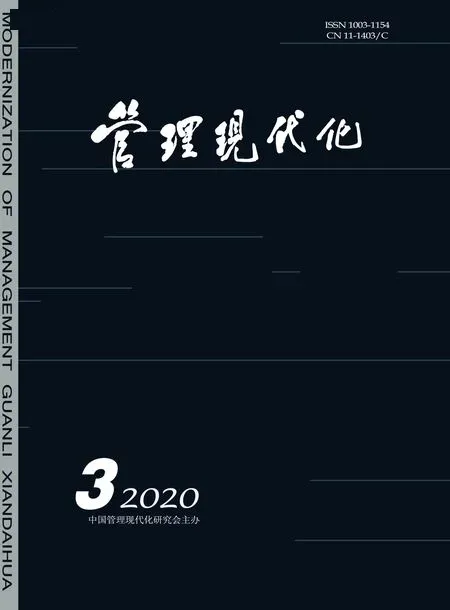新時期海綿城市建設融資問題研究
□ 李冠雄 賀 洋
(北京大學 光華管理學院, 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走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而“海綿城市”正是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城市水環境系統設計領域的具體化表達。“海綿城市”是指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吸水、蓄水、滲水、凈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并加以利用。海綿城市的建設可以有效緩解暴雨天氣對城市排水的影響,有效應對徑流污染及水資源缺乏等問題。
從中外對比上看,“海綿城市”在國外特指一套城市地面透水、滲水的技術標準,以透水材料的設計和運用為主,目的在于實現灰色基礎設施向綠色基礎設施的轉變[1]。而在中國,“海綿城市”的概念是一個系統化的工程,包括透水材料的鋪裝、人工濕地、生態洼地、雨水收集再利用以及排水設施的建設,是新時期我國新型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應用范圍上看,國外的雨洪管理措施主要針對社區、廣場、道路等小范圍區域,而我國則針對整個城市區域,與新型城鎮化密切關聯,更加強調系統性,規劃和建設的難度也更大[2]。
本文通過分析我國海綿城市建設現狀,研究綠色發展理念下海綿城市建設的融資問題。當前我國經濟已步入新常態發展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推進。我國海綿城市的建設作為新常態下新型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供給質量,促進資源整合,因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具體舉措。本文的研究將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分析的宏觀背景,以更全面、系統的探究海綿城市的建設風險與管理機制。研究新時期海綿城市建設問題不僅對短期內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同時對于長期內探索我國新型城市生態文明建設模式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海綿城市建設的發展歷程
(一)提出歷程
我國“海綿城市”的提出是一個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推動過程。2013年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提升城市排水系統時要優先考慮把有限的雨水留下來,優先考慮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設自然存積、 自然滲透、 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2015年4月海綿城市建設首批試點城市公布,遷安、白城、鎮江、嘉興等16個城市入選;2016年4月第二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公布,福州、珠海、寧波、玉溪等14個城市入選。在2017年5月由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公布的首部國家級市政基礎設施規劃《全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十三五”規劃》中,也已明確把海綿城市相關指標作為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考核標準。
中央高層的大力推動,將“海綿城市”由一個學術概念快速轉變成了實際行動,果斷回應了“環境污染、水源短缺、內澇擁堵”等困擾居民生活的“城市病”。具體進程可概括為“中央表態—部委行動—地方試點”三個層次,這也呼應了后續接連出臺的 “超預期”政策紅利,如財政部、國家開發銀行等均出臺支持政策。由此,一套獨具中國特色的涵蓋了從頂層設計到基層行動規劃的海綿城市建設方案初具雛形。
在首批試點申報過程中,有130個城市制定了海綿城市建設方案,其中34個城市進入初選名單,最終16個城市獲得試點立項。首批16個試點城市分布在16個不同省、直轄市,而兩批30個試點城市則分布在26個不同的省、直轄市。這意味著有的省份在兩次評審中均有城市入選試點名單。目前擁有兩個國家級試點的省份分別為浙江(嘉興、寧波)、福建(廈門、福州)、山東(濟南、青島)、廣東(珠海、深圳)。沒有試點的省級行政區除港、澳、臺之外,還有新疆、西藏、內蒙古、山西、黑龍江。整體上看,首批試點城市自身申報基礎更好一些,即天生具有較多的“海綿基因”;而第二批試點城市經濟實力更強。在2015年的GDP排名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位居前四,山西、遼寧增速最慢,黑龍江排名中下。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否獲評國家級試點城市除了與自身“基因”有關外,也會受到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這也反映了決策層對試點城市的定位,即選擇基礎條件較好的城市先行先試,探索、積累出可以復制、推廣的經驗后,再向全國推行。同時,也應注意到在試點城市申報中暫時落后的省份,可能在未來表現出較強的“反超”意識,帶來更多的投資機遇。
(二)頂層設計邏輯分析
“海綿城市”作為一項自上而下推行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理念,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頂層設計”先行的特征。然而,由于我國不同地區在自然環境、發展水平、城市規劃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推動海綿城市前行的“頂層設計”本身也處于不斷的摸索中。除“海綿城市”之外,當前新興城鎮化的其他抓手,如“智慧城市”、“特色小鎮”、“地下綜合管廊”等,也均或多或少地呈現出類似特征。
在2014年12月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水利部聯合發布的《關于開展中央財政支持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提出“對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將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
可見,海綿城市從推行之初,中央就確定了主要依托PPP模式這一大方向。然而,對于仍處于發展變化期的PPP這一“新事物”如何與海綿城市這一“新理念”相融合,也同樣處于摸索變化的階段,這從2015年與2016年《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申報指南》(以下簡稱“指南”)的差別中可以看出。從變化過程來看,“頂層設計”的思路日漸清晰,一方面得益于針對海綿理念的研究日趨深入所帶來的內生性優化,另一方面則得益于首批試點城市探索過程中所積累的外部實踐經驗。從結果來看,“頂層設計”始終保持著謹慎客觀的包容性姿態。“頂層設計”始終未強行規定要采取PPP模式,或設定某一比例紅線,或鼓勵地方不斷提升PPP比例。最終的落腳點在于“有利于實現海綿城市項目建設運營維護全生命周期高效管理”,“模式的創新”是唯一的鼓勵方向。
三、海綿城市建設融資現狀
海綿城市的建設需要巨額的資金,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PPP模式成為各地海綿城市項目的主要實施模式。根據財政部PPP項目庫公布的信息,財政部PPP項目庫中共有海綿城市項目55個,投資總額達到了1142億元。項目平均投資額19.84億元,最大投資額為243億元,最小為3416萬元。其中,處于識別階段的32個,處于準備階段的7個,處于采購階段的有11個,而河北遷安、江蘇鎮江、湖南吉首、四川岳池四地共有5個海綿城市項目已進入到執行階段。上述項目中,最短的合作期限是10年,最長的為30年,平均長度為17年。政府付費(占53%)和可行性缺口補貼(占44%)為主要回報方式,使用者付費僅占4%。常見的運作方式包括DBFO(設計—建造—融資—運營)、BOT(建設—運營—移交)、ROT(改建—運營—移交)等。
從項目區域分布看,PPP項目庫中海綿城市項目分布于安徽、甘肅、貴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江蘇、江西、內蒙古、寧夏、山東、陜西、四川、云南、浙江、重慶等19個省級行政區。其中,山東省推出的海綿城市項目數量獨占鰲頭,共17個。但從總投資額來看,云南省位居第一,為298.75億元。雖然長期來看效益顯著,但短期內相關項目的過快扎堆上馬,導致交通長時間極度擁堵,而關鍵性工程推進過慢,又會引發民眾對海綿城市建設效果的質疑。可見,不僅海綿城市的建設運營是一門藝術,實施進度的把握也需要高超的藝術水平,尤其要注意與其他市政工程施工進度的“協調”。
四、海綿城市的融資難點分析
當前,海綿城市建設的難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PPP創新融資模式的運用,二是融資規模較大,三是項目建設邊界不清晰。
(一)PPP創新融資模式的運用
1.海綿城市是PPP模式與項目系統的結合。海綿城市是一個系統工程,包含很多子項目。單個子項目的完成并不意味著項目整體達標,項目整體達標也不代表每個子項目都合格。一個好的海綿城市項目不僅要求項目整體達標,各子項目也要達標。這就涉及到激勵約束機制的設計,而這一類績效考核機制的設計并無可借鑒的經驗。
2.海綿城市是PPP模式與新型城市管理方式的結合。海綿城市涉及的行業有建筑、道路、橋梁、水利工程、園林綠化等,而這些行業均有相應的政府部門主管。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深入推進,各分管部門各管一塊的城市管理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新型城市管理的要求。
3.海綿城市建設背景下PPP創新模式的運用,需要考慮多重目標。一是海綿城市PPP項目要置身于本地自然環境,充分借助區域自然資源稟賦達成建設目標,在全國統一的考核目標下,需要充分發揮具有地方特色的實現路徑。二是海綿城市PPP項目要置身于本地城鎮化建設全局。借助海綿城市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包括舊城改造、老舊小區改造等,針對本地的城市病對癥下藥,精準發力。三是海綿城市PPP項目要置身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經濟全局,積極借助海綿城市建設,探索區域經濟振興與長久發展的可實現路徑。
(二)融資規模巨大
海綿城市作為城市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其建設必然涉及巨大的融資規模[3]。海綿城市建設的融資規模最終決定于自身的“質”與“量”。海綿城市建設作為典型的生態公共產品,其“質”與“量”的核心在于以人為本。因而本文的測算選擇以城鄉人均指標作為核心變量。
本文以人均存量為基礎,對城市全部基礎設施融資需求做測算,進而以排水、園林綠化領域的融資需求作為海綿城市融資規模的狹義測算口徑,以排水、園林綠化、環境領域的融資需求作為廣義測算口徑[4]。在測算時,設定如下前提:(1)測算的基礎設施具體包括交通、環境、能源(燃氣、供熱)、水系統(排水)、綠地、環衛等領域;(2)基礎設施投資以2017年分領域人均投資額為測算標準;(3)未來新增年度投資為新增城鎮常住人口人均投資額的加總。
測算結果顯示,截至2030年,基礎設施融資需求為45.89萬億元。分項看,交通基礎設施占比最高,為62.09%;其次是環境領域,占比18.96%。園林綠化、排水、集中供熱、市容環境衛生和燃氣,分別占比7.60%、5.20%、2.32%、1.97%和1.86%。具體看,海綿城市狹義融資需求為5.88萬億元;廣義融資需求為14.58萬億元。
(三)項目建設邊界不清晰
1.海綿城市中“建筑與小區”類項目涉及到公用建筑與非公建筑[5]。作為政府主推的工程,非公建筑產權主體并無實施海綿化改造的動機,同時因產權問題,政府也無權強迫其進行海綿化改造,更不說將其納入PPP項目包交由社會資本方統一運營管理。
2.海綿城市運營的績效考核離不開相應的檢測類項目。一方面,檢測類項目若由社會資本方投資,則會出現社會資本方同時作為“運動員”和“裁判員”出現在同一個項目中,檢測的真實性很難保證;另一方面,若由政府方投資,可以解決“運動員—裁判員”問題,但由于海綿城市項目的系統復雜程度遠超一般項目,政府方可能因為不了解項目系統細節而導致“監測真空”或“無效檢測”的出現。因而,該類項目是否納入PPP項目包需視項目具體情況及政府與社會資本方訴求而定。
五、對策與建議
由上文分析,針對海綿城市建設難點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頂層設計突出綜合性。海綿城市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摒棄傳統的項目管理思維,而轉向系統集成管理思維。同時,還應注重海綿城市的地域特色,應在建設模式中融入地方文化特色和地域環境特色,避免海綿城市千篇一律。
第二,培育海綿城市建設的多元化參與主體[6]。海綿城市作為系統集成度高、操作難度大、前后向關聯復雜的系統化工程,單一的建設主體往往難以達成建設目標。新時期海綿城市的建設不僅要“融資”,需要大規模的融資投入,還要“融智”,即需要相應的創新技術方案,同時還需要專業的運營主體,提升整個海綿系統的運營效率。
第三,創新普惠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通過稅收等政策支持鼓勵市政債投資者本地化、居民化,住民對當地信息更加了解,可以對地方政府發債構成民意上的約束;創新針對中、低收入的理財產品,適度打破合格投資者限制,并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適度的“剛性兌付”,增強金融普惠,創設各階層民眾分享經濟增長紅利的有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