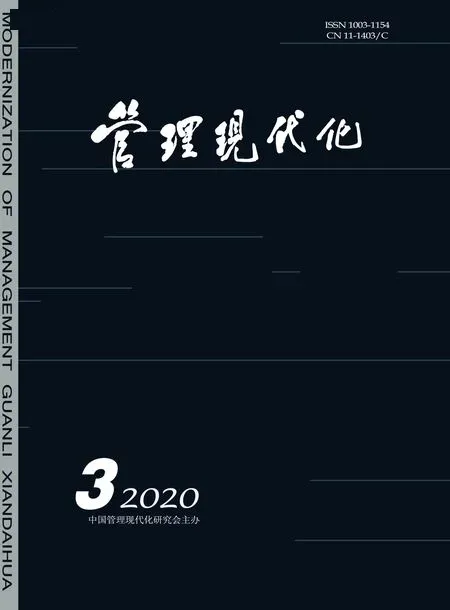當(dāng)前中國(guó)城市群發(fā)展水平差異評(píng)估
——基于七個(gè)國(guó)家級(jí)城市群地級(jí)及以上城市2018年數(shù)據(jù)的測(cè)算
□ 楊智雄 翟 磊
(南開(kāi)大學(xué) 周恩來(lái)政府管理學(xué)院, 天津 300350)
一般意義上,城市群是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是推動(dòng)新型城鎮(zhèn)化的空間載體,不同城市群發(fā)展方向各有側(cè)重[1-2]。近些年,實(shí)務(wù)界和學(xué)術(shù)界逐漸意識(shí)到城市群建設(shè)的重要性,2016年“十三五”規(guī)劃中明確指出要重視“城市群建設(shè)發(fā)展”,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ì)議強(qiáng)調(diào)要“加快重大戰(zhàn)略實(shí)施步伐,提升城市群功能”[3],中國(guó)加快了以城市群為載體的區(qū)域協(xié)同發(fā)展步伐。
學(xué)界已經(jīng)意識(shí)到要因地制宜發(fā)展城市群,針對(duì)多城市群發(fā)展水平的相關(guān)指標(biāo)評(píng)價(jià)體系主要圍繞經(jīng)濟(jì)發(fā)展[4]、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環(huán)境規(guī)制[5]三個(gè)領(lǐng)域,并嘗試對(duì)城市群進(jìn)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層次的分級(jí)[6]。但既有研究仍在幾個(gè)方面存在不足:一是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的邏輯層次是自上而下的,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將城市群作為單一整體進(jìn)行測(cè)量,忽略了組成成分的影響;二是單一評(píng)價(jià),尤其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評(píng)價(jià)較多,缺乏城市群整體綜合發(fā)展水平的分析。需要建立較為科學(xué)的指標(biāo)體系,比較不同地區(qū)城市群整體發(fā)展水平及彼此間差異。
一、城市群總體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體系構(gòu)建與研究方法
(一)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體系構(gòu)建
對(duì)城市群發(fā)展進(jìn)行整體評(píng)價(jià)需要考慮其目標(biāo)和功能。結(jié)合各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發(fā)現(xiàn)[12],城市群發(fā)展目標(biāo)和功能定位可被歸納為三個(gè)方面:除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相關(guān)指標(biāo)、提升公共服務(wù)相關(guān)指標(biāo)以外,還包括完善社會(huì)治理,因此將這個(gè)三個(gè)指標(biāo)作為一級(jí)指標(biāo)大約可以囊括全部發(fā)展水平的評(píng)價(jià)內(nèi)容,通過(guò)汲取已有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相關(guān)指標(biāo)的內(nèi)容,按照三個(gè)一級(jí)指標(biāo)的框架進(jìn)行細(xì)化,按照主、客觀兩種思路進(jìn)行收集,通過(guò)對(duì)初次建立的指標(biāo)體系的兩輪篩選(數(shù)據(jù)可得性篩選和專(zhuān)家評(píng)估),構(gòu)建出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如表1。
(二)研究方法
采用多層模型分析的方式,遵循從城市單元到城市群總體的自下而上的邏輯,將分析層次劃分為三層,即指標(biāo)層(城市內(nèi)部情況)、城市層、城市群層,層層遞進(jìn),城市群整體發(fā)展水平的評(píng)價(jià)以城市發(fā)展評(píng)價(jià)體系為基礎(chǔ)。
這一評(píng)價(jià)機(jī)制的核心在于確定城市發(fā)展各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在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的基礎(chǔ)上,嘗試結(jié)合主觀賦權(quán)法評(píng)判的專(zhuān)業(yè)性和客觀賦權(quán)法優(yōu)點(diǎn),使用主客觀相結(jié)合的綜合賦權(quán)法。求出指標(biāo)權(quán)重,并經(jīng)擬合度驗(yàn)證,得出的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見(jiàn)表1。
在指標(biāo)權(quán)重確定的情況下,測(cè)量城市發(fā)展水平得分(City Development-level Score,CDLS)的公式為:
(1)
其中,ω1k表示每個(gè)一級(jí)指標(biāo)對(duì)應(yīng)的權(quán)重,F-l_i(First-level Indicator)表示對(duì)應(yīng)的一級(jí)指標(biāo)得分;ω2k表示每個(gè)一級(jí)指標(biāo)對(duì)應(yīng)的權(quán)重,S-l_i(Second-level Indicator)表示對(duì)應(yīng)的二級(jí)指標(biāo)得分。
通過(guò)對(duì)城市群內(nèi)部不同城市賦值(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中明確規(guī)定的中心城市賦值為3分, 非中心城市的

表1 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及權(quán)重
計(jì)劃單列市和省會(huì)城市賦值為2分,其他地級(jí)市賦值為1分)重新進(jìn)行加權(quán),可以得出城市群發(fā)展水平得分(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level Score,UADLS),公式如下:
(2)

二、評(píng)估對(duì)象及數(shù)據(jù)來(lái)源
為了保證研究的可操作性和代表性,結(jié)合數(shù)據(jù)情況進(jìn)行篩選,最終分析對(duì)象為長(zhǎng)三角城市群、哈長(zhǎng)城市群、長(zhǎng)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guān)中平原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qū)7個(gè)國(guó)家級(jí)城市群。
文中所選取的各指標(biāo)原始數(shù)據(jù)來(lái)源于《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guó)城市統(tǒng)計(jì)年鑒》、各省市統(tǒng)計(jì)年鑒以及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主觀數(shù)據(jù)通過(guò)發(fā)放網(wǎng)絡(luò)問(wèn)卷的方式進(jìn)行,共回收問(wèn)卷4000份,其中有效問(wèn)卷3804份,單個(gè)樣本城市的問(wèn)卷量在30份以上。
三、城市群發(fā)展水平評(píng)估結(jié)果分析
(一)城市群類(lèi)型差異表現(xiàn)
利用式(2)對(duì)各樣本城市群的總體得分進(jìn)行統(tǒng)計(jì)見(jiàn)圖1。

圖1 樣本城市群發(fā)展水平指數(shù)得分圖
不被類(lèi)型化的現(xiàn)象描述難以探究深層特征,故采用誤差平方和方法確定數(shù)據(jù)自身真實(shí)聚類(lèi)組數(shù)為3組。通過(guò)K-means法將樣本城市群按照三組進(jìn)行聚類(lèi),各類(lèi)包含城市群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城市群聚類(lèi)結(jié)果
將同類(lèi)城市群城市合并,按照公式重新合成權(quán)重計(jì)算,得出三類(lèi)樣本城市群一級(jí)指標(biāo)雷達(dá)圖,見(jiàn)圖2。

圖2 三類(lèi)城市群一級(jí)指標(biāo)得分雷達(dá)圖
從一級(jí)指標(biāo)雷達(dá)圖上看,三類(lèi)城市群構(gòu)成形狀相似,近乎形成內(nèi)嵌的“同心三角形”,長(zhǎng)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qū)各項(xiàng)得分較高,處于最外層,第二類(lèi)樣本城市群發(fā)展階段次之,處于中間層,而第三類(lèi)樣本城市群則位于“近同心三角形”的最內(nèi)部。三類(lèi)樣本城市群各指標(biāo)得分依次降低,呈現(xiàn)出明顯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配的梯次差距。
(二)類(lèi)型城市群差異原因分析
為了更進(jìn)一步分析類(lèi)型城市群發(fā)展水平的差異和原因,對(duì)三類(lèi)城市群一級(jí)指標(biāo)進(jìn)行了相關(guān)分析,結(jié)果見(jiàn)表3、4、5。

表3 第一類(lèi)樣本城市群一級(jí)指標(biāo)相關(guān)性分析

表4 第二類(lèi)樣本城市群一級(jí)指標(biāo)相關(guān)性分析

表5 第三類(lèi)樣本城市群一級(jí)指標(biāo)相關(guān)性分析
通過(guò)分析,可以得出三個(gè)較為明顯的結(jié)論:一是很大程度上,三類(lèi)城市群的差距由經(jīng)濟(jì)水平?jīng)Q定,由于三類(lèi)城市群內(nèi)部城市處于不同的經(jīng)濟(jì)階段,因此呈現(xiàn)出梯次的發(fā)展格局;二是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獨(dú)立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這種特殊現(xiàn)象尤其體現(xiàn)在“滯后型”城市群中,可以大致判斷這是在財(cái)政轉(zhuǎn)移支付的支持下,在政府近些年政策的影響下,通過(guò)推動(dòng)基本公共服務(wù)標(biāo)準(zhǔn)化、均等化,在區(qū)域差距仍存在的背景下提升了落后地區(qū)服務(wù)供給水平;三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duì)社會(huì)治理程度的影響具有一般性,既掣肘社會(huì)管理的水平,也制約社會(huì)發(fā)育的程度。由于“混合型”城市群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水平和社會(huì)管理水平得分偏低,通過(guò)對(duì)這兩個(gè)變量進(jìn)行相關(guān)分析,發(fā)現(xiàn)二者呈顯著正相關(guān),可以認(rèn)為由于在二類(lèi)城市群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育較差,人口季節(jié)性流動(dòng)強(qiáng),增大了社會(huì)管理的壓力。同時(shí),由于居民自身收入水平不高,社會(huì)自組織能力和居民的參與意識(shí)都受到客觀環(huán)境的抑制,二三類(lèi)城市群的社會(huì)治理水平都呈梯次下降。
四、結(jié) 論
國(guó)家級(jí)城市群之間呈明顯的“梯次格局”,可劃分為三種類(lèi)型:(1)以第一類(lèi)樣本城市群為典型的“先發(fā)型”城市群,內(nèi)部城市多分布在東南沿海發(fā)達(dá)地帶,多已進(jìn)入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后期,整體發(fā)展水平較高且均衡。(2)以第二類(lèi)樣本城市群為典型的“混合型”城市群,典型特點(diǎn)是內(nèi)部城市發(fā)展階段不同,呈現(xiàn)出“一強(qiáng)多弱”或者“少?gòu)?qiáng)多弱”的混合態(tài)勢(shì)。(3)以第三類(lèi)樣本城市群為典型的“滯后型”城市群,典型特點(diǎn)是區(qū)域整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相較落后。指標(biāo)得分整體較低,同時(shí)呈現(xiàn)出公共服務(wù)供給水平優(yōu)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huì)管理水平的現(xiàn)象。
在“滯后型”城市群中,服務(wù)供給水平并不顯著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關(guān),這是“以標(biāo)準(zhǔn)化促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目標(biāo)效能的體現(xiàn),同時(shí)通過(guò)問(wèn)卷中“當(dāng)?shù)厣畹男腋8性u(píng)價(jià)”指標(biāo),測(cè)量發(fā)現(xiàn)其與基本公共服務(wù)水平在三類(lèi)城市群中都呈顯著正相關(guān)(Pearson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742,顯著性水平為0.03),說(shuō)明公共服務(wù)水平的提升能顯著提升獲得感。這一發(fā)現(xiàn)就為短期提升經(jīng)濟(jì)落后地區(qū)公民“獲得感”提供了一種可能,即通過(guò)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水平和質(zhì)量,“以服務(wù)平衡差距”。□
- 管理現(xiàn)代化的其它文章
- 品牌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價(jià)值承諾實(shí)現(xiàn)路徑研究
——基于價(jià)值共創(chuàng)視角 - 中國(guó)必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分享經(jīng)濟(jì)對(duì)我國(guó)GDP影響的統(tǒng)計(jì)分析研究
- 我國(guó)沿邊自貿(mào)區(qū)政策切入點(diǎn)的國(guó)內(nèi)外經(jīng)驗(yàn)與啟示
- 基于創(chuàng)新型制造企業(yè)的科技創(chuàng)新平臺(tái)建設(shè)探析
- 互聯(lián)網(wǎng)知識(shí)付費(fèi)平臺(tái)商業(yè)模式的構(gòu)建路徑
——賦能視角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