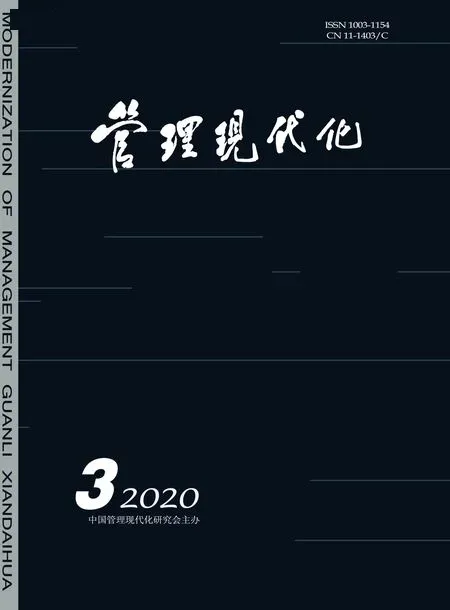中國必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崔俊富 陳金偉 崔 偉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 江蘇 南京 211106; 2.山東女子學院 經濟學院, 山東 濟南 250300;3.南京審計大學 經濟學院, 江蘇 南京 211815; 4北京師范大學 未來教育高精尖創新中心, 北京 100875)
201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接近10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1%,按照2019年平均匯率,折合14.4萬億美元,年末總人口14億人,據此測算,人均1.03萬美元[1]。
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除了總量的提升,也有了質的突破。絕大部分人認為中國仍將保持較高發展速度,最終成為高收入國家,但是,國際上仍有部分人認為,雖然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中國還是無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本文將對中國為什么必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行討論。
一、“中等收入陷阱”由來
(一)世界經濟體分類
世界銀行根據國民收入將世界各個經濟體分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上收入、高收入4個組別。其中,發展中國家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發達國家為高收入。目前經濟體分類標準已經成為研究世界經濟體發展水平、發展差別、發展趨勢的重要工具,也成為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歐盟、OECD確定援助標準,美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都參考經濟體分類標準。自發布以來,隨著國民收入的變化,分組標準、經濟體數量也隨之有所變化。1987—2018年,低收入標準由480美元提高到1025美元,中低收入標準由481~1940美元提高到1026~3995美元,中高收入標準由1941~6000美元提高到3996~12375美元,高收入標準由600美元以上提高到12375美元以上;低收入經濟體由49個減少到31個,中低收入經濟體由45個增加到47個,中高收入經濟體由27個增加到6個,高收入經濟體由41個增加到8個[2]。

表1 世界經濟體分類情況[2]
(二)“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各經濟體的發展情況,2006年世界銀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在邁向高等收入經濟體過程中,無法有效擺脫現有發展模式,經濟發展出現停滯和反復,人均國民收入無法達到高等收入水平”[3]。2007年世界銀行對該概念進一步進行了闡述,“中等收入國家容易受到低收入國家低人力成本競爭和高收入國家高創新競爭,雙重擠壓下經濟發展放緩并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4]。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比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更加困難[5]。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自提出以來引發了廣泛的討論,部分學者并不認同該提法,甚至認為該提法是偽命題。江時學[5-6]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較為狹窄,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國民收入能否達到一定水平作為標準,容易令人誤入歧途。王紹光[7]認為,“陷阱”具有自發延續、自我增強、難以突破等特點,貧困、低收入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陷阱”,而對于中等收入階段,“陷阱”并不一定適用。一個證據是現有的高收入國家盡管在中等收入階段停留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可能長達百年,例如比利時、荷蘭、英國、智利、烏拉圭在中低收入停留時間分別為107、128、108、101、124年,但是最終都能進入高收入階段。另一個證據是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加速趨勢,中低收入期間的年均增長率為1.9%,中高收入期間的年均增長率為3.1%,提高了1.2個百分點,相對應的在中低收入階段停留時間平均為80年,中高收入階段停留時間平均為16年,縮短了64年[8]。

表2 部分經濟體發展情況[8]
注:LM、UM、H分別表示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LMT和UMT分別表示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階段停留的時間;LMG和UMG分別表示在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階段的年均增長率;平均值為簡單算術平均數。
但是,大多數學者還是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重要現實意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狀況。德懷特·帕金斯[9]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世界性的發展難題。黃繼煒等[10]、吳崇伯等[11]、熊琦[12]研究了東盟部分國家的發展情況,發現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家不同程度的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郭濂[13]、高京平等[14]研究了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的發展情況,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現代化道路中的“發展病”。
表2數據顯示:匈牙利(1925)、哥倫比亞(1946)、墨西哥(1942)等國家相繼進入中低收入階段,至今未跨入高收入階段[8]。
二、部分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不同經濟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所不同,歸納來看沒有及時實現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緩慢、政治社會局勢動蕩、社會福利失衡是主要因素。
(一)產業升級困難
近代拉丁美洲、東南亞國家先后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上呈現一定程度的依賴、盲從。從經濟結構上看,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拉丁美洲、東南亞國家是西方國家的原材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因而獨立初期各國產業層次普遍較低,在發展的初期可以憑借豐富的資源、較低的成本實現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但是這種發展模式過度依賴于資源、成本,一旦資源枯竭、成本上升,必然受到影響。當發展到一定階段,進入中等收入之后,原有的優勢,尤其是低成本優勢逐漸消失,為了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實現產業結構的逐步升級。而這些國家,由于工業基礎薄弱、產業體系不健全、過早地去工業化等一系列問題嚴重阻礙了產業升級,進而影響了經濟發展速度。
(二)科技創新不足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最長久、最有效的推動力,科技創新匱乏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拉丁美洲開發較晚,資源豐富,資源依賴性特色濃厚,創新積極性較弱。《經濟學人》舉了一個生動傳神的例子:“阿根廷沒有提升食品附加值的想法,今天仍然是以燒烤頂級牛肉作為主要烹調方法”[15]。巴西、委內瑞拉等國也有豐富的鐵礦、石油資源,開采礦石、石油比創新更加為當地人所接受。東南亞國家原有基礎薄弱,沉重的負擔及重視程度不夠導致科研投入較少,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科研投入占GDP比重分別僅為0.63%(2006)、0.21%(2007)、0.11%(2007)和0.08%(2009),遠低于歐盟28國1.7%(2007)和OECD2.2%(2007)的平均水平[10]。
(三)政治社會動蕩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歷史階段給拉丁美洲、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社會建設帶來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作為新擺脫殖民統治國家,各國普遍嘗試建立一個強力政府,來彰顯民族獨立,卻某種程度上伴隨了嚴重的濫權腐敗;另一方面,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體制不一定能夠符合自身發展特點,引發了一系列的政治社會動蕩。19世紀初拉丁美洲各國相繼獨立,20世紀中期東南亞國家相繼獨立,之后普遍經歷了軍人、文人交替統治的局面,動亂、分裂常有發生。更為極端的是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等中東國家,這些國家在20世紀中后期憑借豐富的石油資源,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比較富裕,近期以來,戰爭頻繁給這些國家的經濟帶來毀滅性打擊,戰火之中不可能發展經濟,這些國家迅速從中高收入國家跌落至低收入國家。
(四)社會福利失衡
良好的社會福利是發展的重要保證,但是過高的社會福利會帶來沉重的負擔,拉美國家的發展戰略選擇往往受到高額社會福利的左右,高額的社會福利不僅沒有激勵社會公眾“干事創業”,反而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羈絆因素。
拉美國家普遍貧富差距過大,2003年左右,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南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5以上,部分國家甚至超過了0.6,最窮的1%人口占有社會財富不到2%,遠遠超過警戒水平。過大的社會不平等壓力使得政府在再分配中走向“民粹主義”,導致社會支出不斷攀升,不可持續,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必將難以為繼[13]。以石油富國委內瑞拉為例,石油為委內瑞拉帶來了巨額財政收入,委內瑞拉將石油收入投入到社會福利中,民眾短期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是長期是難以為繼的。隨著國際油價的下降,石油收入大幅度下降,委內瑞拉經濟危機不可避免,2013—2018年委內瑞拉GDP下降了47.8%[16]。
三、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正處于中高收入階段,已經接近高收入水平,按照現有趨勢中國將在未來一段時期跨入高收入國家。但是目前國際上仍有部分人唱衰中國,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同樣面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不過也有自身的特色與優勢,中國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經濟結構合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圖1),GDP總量由1978年的3678.7億元,增長到219年的990865億元,增長了接近270倍[1]。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速有所回落,但是仍維持了6%以上的較高速度,中國并未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所出現的經濟發展停滯,甚至負增長局面,按照現有趨勢,中國在幾年之后就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結構合理,三產比例為7.1:39.0:53.9,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4.2:36.1:59.7(2018)。第三產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超過5%,貢獻率接近6%,同時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也發揮了良好的支撐作用。第一產業提供了中國經濟發展必要的農產品,2018年人均糧食、棉花、油料、豬牛羊肉產品分別比1978年增長47.9%、91.3%、349.1%、414.3%[17]。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出現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去工業化趨勢,反而工業體系更加完整強大,第二產業增加值達386165億元,增長5.7%,在電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技術領域已經處于世界前列[1]。

圖1 1978—2019年中國GDP總量及增速情況[17]
(二)科技創新活躍
中國一貫重視科技創新,在科技投入、載體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科技創新成果豐碩。從研發經費支出來看(圖2),1995年中國研發經費支出僅348.7億元,占GDP比重僅為0.6%,2018年研發經費支出已增長到接近2萬億元,增長了50多倍,占GDP比重提高到2.2%,提高了1.6個百分點。

圖2 1995—2018年研發經費支出情況[17]
從國際比較上看,20世紀90年代,中國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與OECD國家、歐盟28國差距比較大,到2018年中國已經超過歐盟28國的平均水平,接近OECD國家平均水平[17]。
從載體建設上看,以高校為例,相繼開展了“211工程”、“985工程”、“雙一流工程”等戰略規劃,高校的科研水平大幅度提升,2003—2011年清華大學的學術研究排名基本在200名左右徘徊,2019年已位列世界第43位[18]。
從人才培養上看,中國每1萬人在校大學生數量由1990年的326人,提升到2018年的2658人,增長了7倍。從科技創新成果上看,專利授權數由1985年的300件增長到2018年的244.7萬件,增長了800多倍[17]。
(三)政治社會穩定
文景之治、漢武盛世、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中國歷史上每一次代表性的經濟大發展都需要安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作保證,人民才能安心地發展生產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中央的堅定領導下,我們堅定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穩定,為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各方面發展活力,消除各方面發展障礙。一方面建設有為政府,中國政府作為中國發展的服務者、管理者,經過積極探索,目前處理各方面事務更加穩定、成熟,能夠充分履行義務,全面發揮職能,大大增強了經濟轉型和社會調整的張力。另一方面建設有效市場,建立健全多種所有制、財政稅收、外貿金融等各項規章制度,有力保障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19]。
(四)文化自信保障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最深沉的力量,中華文明泱泱5 000年傳承至今,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構成了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勤勞、最勇敢的民族之一。中華文化推崇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個人提升,倡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發展理想,而不是裹足不前、安于現狀。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無論是面臨何種情況,中國人民始終秉承中華文化,努力進行創新生產,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下,這種勤勞、勇敢的意志品質必然會爆發巨大的能量。當前中國人民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不斷增強文化自信,以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作保障,必將勇往直前地進行現代化建設。
四、結 語
對于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的長期平穩發展是核心目標,只有經濟長期平穩發展才能保證充分就業、才能增強物價波動的承受空間、才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時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墨西哥等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相比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國具有經濟結構合理、科技創新活躍、政治社會穩定、文化自信保障等條件,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