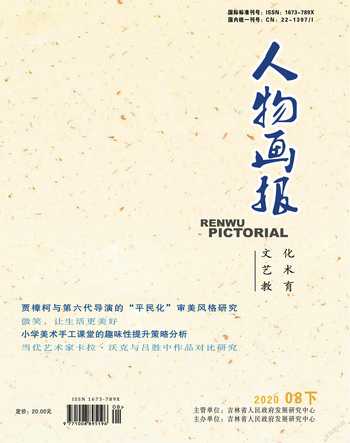賈樟柯與第六代導演的“平民化”審美風格研究
詹仰
摘? 要:以賈樟柯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已經成為中國電影行業不可忽視的一股的全新的力量。他們的電影作品屢屢獲獎,其影片更多關注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講述那些有追求有情感卻迷失在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故事,影片中所表現出來的“平民化”審美風格給中國電影市場注入了新活力,本文首先對六代導演“平民化”審美風格產生的現實基礎和成因進行了分析,然后對以賈樟柯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特質進行探索,最后就“平民化”的審美風格及對紀實美學的新突破進行了研究。
關鍵詞:賈樟柯;第六代導演;“平民化”審美風格;研究
第六代導演的作品沒有華麗的表現手法,也不關乎沉重的歷史故事,他們站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視角,表現現實生活,樸素的表達人文主義情懷,沉著的表現小人物的快樂和堅韌的生活態度,體現一種與現實對話的紀實美學,記錄現實是六代導演作品的準則,總結第六代導演的作品中的特點,分析其作品中的人文主義和平民風格,探索六代導演的電影作品規律,能夠有效的把握電影產業的發展方向,對于豐富電影紀實美學的內容,弘揚樸素的人文主義精神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第六代導演“平民化”審美風格產生的現實基礎和成因
首先是第六代導演所處的時代背景。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進程,給中國帶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完成了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達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性突破,為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改革紅利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大幅度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再為了溫飽而傷神,并逐漸開始尋求精神層次的消費,種種變化進一步促進了文化娛樂事業的飛速發展,其中就包括了電影行業,電影行業能夠豐富人們的精神需求,同時也能夠創造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其次,改革開放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也造就了一批被時代和社會拋棄的群體。改革開放的發展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社會的變革和日新月異的發展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讓人眼花繚亂,更多人面對社會的變革驚慌失措,他們即將要退出時代的舞臺,為了不被時代和社會所拋棄,他們頂住強烈的失落感涌入城市,在新的環境下重新尋找夢想,一部分人快速的適應了時代發展的腳步,摘掉了貧窮的帽子,但是更多的人不知何去何從,只能在城市里過著底層的生活,為了生活而自食其力,成為在城市的邊緣頑強生存的弱勢群體。雖說這些都是時代發展不可避免的過程,但也反映了社會的真實面貌,電影作為現代化過程中的一項偉大的藝術,不正是要反映這些真實的社會生活和平凡普通的面貌嗎?
最后,第五代導演在電影行業取得的輝煌成就,給六代導演帶來了沉重的壓力,他們只能另辟蹊徑,尋找不一樣的素材融入到電影當中。第五代導演在摒棄傳統變革求新的同時,極大地豐富了電影表現形式的電影語言,通過象征隱喻和抒情刻畫強烈沉重的人文理念,對中國電影帶來了前所未見的震撼和變革,他們渴望實現自身的突破,讓自己的電影作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在表現歷史、展現社會風貌的過程中努力與世界接軌。在這樣的情況下,第六代導演挖掘和塑造社會底層的平民故事,在關注現實和民生問題的環境中迎合了新時期的電影市場和廣大的中下層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他們頂住五代導演帶來的巨大壓力,最終在電影行業脫穎而出,給觀眾帶來了不一樣的,更加貼近生活的電影作品[1]。
二、以賈樟柯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的特質
第六代導演的思想成長到成熟在八九十年代,他們有著自己的經歷和生活,更多的從摸爬滾打中積累經驗,走出了自己的風格。其一,思想文化的多樣化導致了更多成長中的困惑,他們處在文化思想轉型時期,更多地表現為迷惘和躁動的青春,他們在踏上電影之路之前已經對生活有了自己的體驗,這就為他們的電影理念突破五代導演的束縛奠定了基礎,他們更多的關注,像自己一樣的縣城少年為什么不能出現在銀幕上,去追求夢想和理想的生活,他們更傾向于表現自己和身邊的故事,講述平民化的藝術,于是第六代導演打著人文關懷的旗號走上了自己的電影之路。
其二,命運多舛的拍攝過程讓六代導演頑強生長。相對于五代導演的生逢其時,六代導演則只能在沒有資金支持的前提下野蠻生長,這也造就了六代導演的短片拍攝經歷,例如導演賈樟柯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整部短片中演員和制作人員都是自己的同學,而其后續的作品《小武》,拍攝成本低,制作規模小,在講述一個處于社會底層的小偷經歷的友情、親情、愛情的故事的同時,也展現了中國北方小縣城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狀態,通過其鏡頭,我們能夠感受到第六代導演寒酸和落魄的環境和條件,所以他們只能選擇紀實的風格來表現個體的行為,甚至由于電影所表現的現實風格,涉及到一些非主流的文化道德,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封殺,他們導演制片的道路艱難而曲折,但更是這樣才體現出了電影文化的多樣性和可能性[2]。
三、對紀實美學的新突破——“平民化”審美風格
第六代導演在創作初期更多的是變現自己的生活體驗,電影作品更多的將是身邊的故事。從90年代開始,他們將視角轉向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例如《小山回家》《小武》和《十七歲的單車》等影片開始表現社會的現狀,關注的更多是為生存而忙碌奔波的個體,表現出平民化的審美傾向。以平民的視角審視主角身邊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寫真實的人生,記載普通民眾的生存境遇,記錄當代中國的變革和那些被遺忘在角落的邊緣群體,倡導樸素的人文精神,塑造那些在現實社會中努力生存卻被現實打擊得體無完膚的“小人物”形象,從真誠的寫實手法到極端的現實主義表現,往往給人內心的觸碰和感染,讓人們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從冷酷的紀實風格中感受溫情和一顆對待生活火熱的心,對普通人表達的最高的敬意,折射出當代社會最普遍的社會群體的生活,反映一些社會問題,實現了紀實美學的新突破[3]。
四、結語
綜上所述,第六代導演的電影摒棄了浮躁和功利,更多的表現真摯的情感和樸素的生活,他們為電影行業帶來了朝氣,帶領我們在影片中尋找那些珍貴的的、久違的美好,讓我們感受精神上的共鳴,獲得溫暖而真實的體驗。
參考文獻:
[1]李玟, 牛綠林. 第六代導演的電影藝術實踐[J]. 東南傳播, 2018, 000(006):46-47.
[2]陳旭光. “新力量”導演與第六代導演比較論——兼及“新力量”導演走向世界的思考[J]. 電影藝術, 2019, 386(03):65-71.
[3]梁瑾. 論賈樟柯電影的紀實美學風格——以《三峽好人》為例[J]. 文藝生活:藝術中國, 2019, 000(006):P.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