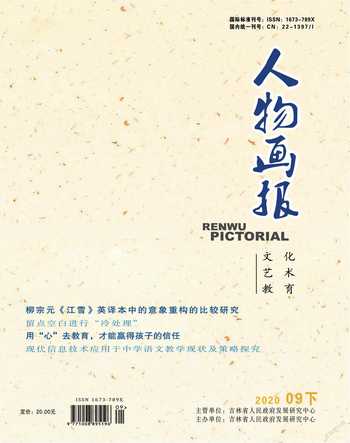柳宗元《江雪》英譯本中的意象重構的比較研究




摘 ?要:詩歌翻譯是源語詩歌在譯語文化中的重構,而詩歌意境的重構離不開意象的重構。為了更好地傳遞源語詩歌的“意味”, 譯者和詩歌的意象傳遞是影響詩歌翻譯的重要因素。《江雪》四個不同譯本的對比,揭示了不同譯者對意象的文化內涵傳遞和個性化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意象;詩歌英譯;《江雪》;柳宗元
柳宗元著名的山水詩《江雪》的英譯共有將近三十種譯本,體現了柳宗元的山水詩在以英語為目的語的文化中的傳播。胡文仲1引用了愛德華·泰勒1871年提出的文化定義,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 詩歌翻譯,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傳播途徑,有利于傳遞人類遺產、傳承人類文化。張廣法2提到《江雪》的外籍譯者有十一人,分別是威廉·弗萊徹(W. J. B. Fletcher) ,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英尼斯·赫丹(Innes Herdan)、約翰·諾弗爾(John Norval)、大衛·辛頓((David Hinton)、杰羅姆·西頓((J. P. Seaton)、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雯姆·杰尼斯(Soame Jenyns)、伯頓·華茲生(Burton Watson)、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等。文本將選取四個譯文進行比較,歸納和總結不同譯者對詩歌意象的翻譯和重構。
一、詩歌意象及其翻譯
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強調意象的含蓄和意味,講求象征性和暗示性。同時中國詩歌意象講究意與象的完美融合,即主體和客體的融合。陳植鄂3指出,“意象是以詞語為載體的詩歌藝術的基本符號”。而西方的意象與中國傳統詩歌意象有相似之處。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4曾經指出“意象是能在同一時刻激發思想和感情上的繁復共鳴的東西”,(“An image in that which presents an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complex in an instant of time”),體現的也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詩歌意象的重構離不開譯者對源語詩歌意象的理解與把握,也離不開譯語讀者對于譯本的理解。
二、詩歌意象的重構: 《江雪》三個英譯本之比較
最早翻譯《江雪》的外籍漢學家是W.J.B. Fletcher(威廉·弗萊徹),之后又出現了眾多的英譯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大衛·辛頓((David Hinton)、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葉維廉(Wai-lim Yip)等。后面三個譯本都屬于現當代的譯文。譯文分析如下:
第一行:千山鳥飛絕
譯者 譯文
Fletcher “The birds have flown away from every hill.” 5
David Hinton “A thousand peaks: no more birds in flight.” 6
Gary Snyder “These thousand peaks cut off the flight of birds”7
Wai-lim Yip “A thousand mountains—no bird’s flight.”8
在柳宗元的第一行詩歌中,“山”和 “鳥”是兩個中國傳統原型意象。弗萊徹將山翻譯成了“hill”, 辛頓和施耐德翻譯成了“peaks”, 而葉維廉則將“山”譯成了“mountain”。在翻譯原型意象時,譯者的意識形態對與譯文的產生起著關鍵的作用。 “hill”、“peak”和“mountain”在英語文化中傳遞的文化內涵是不同的。 “Hill”是小山,與柳宗元所處的地理位置“永州”是貼合的,他創作《江雪》的流放之地永州更多的是“hill”,當然柳宗元此處是否真的指他當時的創作地點也是未知的,因為漢語詩歌的意向美就在于它的不確定性,譯得太準確,反而失去了漢語詩歌的意境。辛頓和施耐德采用了“peaks”(山峰)作為目的語的意象,因為他們更多地考慮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按照英語的邏輯,只有太高的山峰,才會沒有鳥兒的痕跡,也體現了柳宗元在流放之際對于“高處不勝寒”的朝廷的復雜情感。葉威廉在譯本中使用了“mountains”同樣也是來源于他對于原文本的理解。由此可見,譯者對于源語詩歌的認知是影響意象重構的關鍵因素。第一行中還有一個意象“鳥”。四個譯本都翻譯成了“bird”,說明了漢語文化與英語文化在“鳥”的原型意象的高度契合,都象征著“自由”、“無拘無束”以及“鳥兒滑向天空的方向”。同時譯文中對于“千”和“絕”的翻譯也是各有千秋的。“千”在古代漢語中象征著“多”,所以弗萊徹直接用了名詞復數的形式表現“多”的概念,而之后的三個譯本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保留了“千”(thousand)的意象,體現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而在翻譯“絕”的意象時,弗萊徹和施耐德用了“away 和 off”構成的兩個肯定句,而辛頓和葉威廉采用的是兩個否定句。
第二行:萬徑人蹤滅
譯者 譯文
Fletcher “Along each empty path no footprint seen.”9
David Hinton “Ten thousand paths: all trace of people gone.”10
Gary Snyder “On all the trails, human tracks are gone.”11
Wai-lim Yip “A million paths—no man’s trace.”12
在第二行中, “徑”和“蹤”是兩個傳統的中國文化原型意象。三個譯文將“徑”譯成了“path”,而施耐德“徑”譯成了“trails”,其中“trails”尤其指的是山林中少有人走而形成的不清晰的足跡。“蹤”被翻譯成了“footprint”、 “trace” 和 “track”。為了體現 “滅”這一變化,辛頓和施耐德使用了“gone”來重構“蹤跡”的變化。對于“萬”這一原型意象,只有辛頓采用了直譯的方式,譯成了“ten thousand”,葉威廉采用改寫的方式,將“ten thousand”譯為“a million”, 適應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施耐德將譯文中“萬”的意象省略了,以求更通順、更流暢的譯文。
第三行:孤舟蓑笠翁
譯者 譯文
Fletcher “In his lone skiff his bamboo garments screen,”13
David Hinton “In a lone boat, rain cloak and a hat of reeds,”14
Gary Snyder “A single boat—coat—hat—an old man!”15
Wai-lim Yip “Single boat. Bamboo-leaved cape. An old man.”16
第三行中的“孤舟”和“蓑笠”是中國文化中常見的兩個意象。弗萊徹和辛頓將“孤舟”翻譯成了“lone skiff”和“lone boat”,引起了讀者情感上的共鳴。施耐德和葉威廉則采用了客觀描繪的方法將“孤舟”翻譯成了“single boat”,更容易喚起目的語讀者的想象。除了施耐德將“蓑笠”的意象抹掉了以外,其他的三位譯者都用了直譯的方法將其翻譯成“bamboo garments”、“rain cloak and a hat of reeds”、“Bamboo-leaved cape”,其中辛頓的譯文是最符合原文的。
第四行:獨釣寒江雪
譯者 譯文
Fletcher “One aged fisher from the snowstorm chill.”17
David Hinton “an old man’s fishing the cold river snow.”18
Gary Snyder “Alone ? ?fishing ? ?chill ? ?river ? ?snow.”19
Wai-lim Yip “Fishing by himself: ice river. Snow.”20
第四行 “獨釣寒江雪”是這首詩的高潮,體現的是柳宗元作為一名偉大的政治家,雖在流放途中,依然堅守政治追求的精神。其中的原型意象有“獨”、“釣”、“寒江”、“雪”等。其中,弗萊徹將重心放在了“寒冷的雪”(chill the snowstorm)上,省略了“江”的意象; 辛頓采用直譯的方式重構了以上四個原型意象,如“an, fishing, cold river, snow”; 施耐德也通過直譯的方式將詩歌的意境很好地展現了出來;葉威廉的譯本通過名詞成分并舉的散文形式,凸顯了詩歌的繪畫意味,重構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
三、結語
唐代政治家、哲學家、散文家、詩人柳宗元的《江雪》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是有跡可循的。許多國內和國外的譯者試圖用英語在英語文化中復制他的詩歌,獲得了較大的成功。盡管詩歌翻譯遇到了語言、文化、韻律等各方面的障礙,然而無數譯者試圖突破各種障礙,重構源語詩歌的意象和意境,盡管英語無法很好地傳遞古代漢語的音樂性和含蓄性,然而這四位譯者基于他們個人對詩歌的認知,對《江雪》進行了重構,賦予了中國古典詩歌 “穿越國界”的契機,也為詩歌翻譯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參考文獻:
[1]胡文仲. 超越文化的屏障: 胡文仲比較文化論集[M].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4:9.
[2]張廣法,文軍.柳宗元“江雪”英譯策略體系描寫研究[J].外國語言文學,2019,36(06):611.
[3]Pound, Ezra. How to read. New York Herald. Reprinted in T.S.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C].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4,1928.15-40.
[4]陳植鄂.詩歌意象論一微觀詩史初探[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64.
[5][9][12][16]Fletcher, William John Bainbrigge. 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23:151.
[6[10][14][18]Hinton, David.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172.
[7][11][15][19]Mair, Victor H. 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106-107.
[8][12][16][20]Ye Wai-lim,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 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234.
作者簡介:羅瓊(1981-),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基金項目: 2017年湖南省哲學社科基金外語聯合項目《傳播學視閾下柳宗元作品英譯研究》(湘社科辦(2017)17號:17WLH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