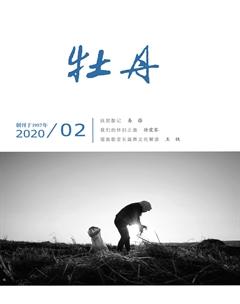淺析20世紀四五十年代梁倫的舞劇創作特征
梁倫是中國著名舞蹈編導家、舞蹈理論家、舞蹈教育家。在新中國舞劇的發展史上,梁倫與吳曉邦、戴愛蓮等開拓者一樣,為新中國舞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中國舞蹈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本文通過分析20世紀四五十年代梁倫的舞劇創作特征,為讀者呈現他在舞劇創作上的走向,剖析他的舞劇創作觀點,進而厘清梁倫在20世紀對新中國舞劇的發展方向起到的作用。
一、梁倫的創作背景介紹
(一)創作啟蒙
1941年,梁倫考入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編導專業。20世紀40年代中期,梁倫步入舞蹈藝術大門。當“新舞蹈”的開拓者吳曉邦的舞蹈創作成熟,并在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任職并授課教學時,梁倫恰好就讀于此。1943年,吳曉邦創作了舞劇《寶塔與牌坊》,梁倫參與其中。這部為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舞蹈班量身打造的舞劇,時至今日已成了中國舞劇創作歷史中的代表作。
這次參演使得梁倫打開了中國舞劇的大門。通過《寶塔與牌坊》,他感受到了舞劇藝術的魅力。這門新興的藝術與戲劇一樣,都可以揭示深刻的真理,不同之處是舞劇運用了舞蹈這一能打動人心的藝術形式。對于梁倫來說,吳曉邦的舞蹈,影響他創作了大量現實主義題材的舞劇和舞蹈作品。到后來,他又向英國舞蹈家戴萊夫人學習芭蕾舞,通過吸收、借鑒外國舞劇,用中國的體態來表演中國的舞劇。正是這一時期的“容納百家”,為梁倫打下了深厚的戲劇及舞蹈基礎,使他日后走上了燦爛的舞蹈生涯。
(二)“中國歌舞劇藝社”時期的創作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進一步鎮壓民主運動,為了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演劇五隊、七隊被迫撤離到香港,并成立了“中國歌舞劇藝社”,梁倫就在其中。而后又出國赴南洋一帶展開活動。本著“向廣大僑胞宣傳祖國的文化藝術,把新的藝術種子,傳播到廣大的僑胞,特別是青年的僑胞中去”的思想指南,梁倫到了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作巡回演出。在異國他鄉的三年,梁倫配合“中國歌舞劇藝社”,致力于“宣傳愛國主義,宣傳抗日,向廣大僑胞宣傳祖國的舞蹈藝術”,演出了眾多富有生活氣息、強烈時代感和民族氣息的新作品,并自己創造了大量如:諷刺和批判封建婚姻的獨幕喜劇《駝子回門》,反映新疆少數民族的歌舞《馬車夫之戀》,以及喻義中國人民即將迎來解放的《天快亮了》等優秀作品,為舞蹈藝術創作打開了一片廣闊的天地。在之后時間里,梁倫的《保衛世界和平》《乘風破浪解放海南》《珍珠》《牛郎織女》等轟動一時的作品,先后呈現在世人眼前。
二、梁倫的舞劇創作手法
(一)深入生活,走進民間
梁倫很早就意識到搜集、學習民族民間舞蹈對作品創作大有裨益。他認為,要探尋新舞蹈的民族形式,必須要從民間舞蹈當中吸取養分,這關系著新舞蹈藝術是否可以獲得廣大群眾的歡迎。
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文藝工作者應該解決的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在會上明確指出,文藝工作首先要為工農兵、為廣大群眾服務。因此,要把立足轉移到工農兵立場上。由此,對當時處于水深火熱的中華民族,舞蹈創作者們用現實主義舞蹈作品發出自己的吶喊。梁倫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下,開展藝術實踐,并不斷創作出反映當時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的舞劇作品。
他創作的舞劇《乘風破浪解放海南》,是謳歌人民武裝力量的“戰士舞劇”。這部由華南文工團為歡迎解放海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凱旋創作出的歌舞劇,以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渡過瓊州海峽,一舉解放海南島為原型,展現了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渡海作戰時英勇、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舞劇中“渡海作戰” “海上練兵”等片段,從新的生活形象中提煉出來,創新了舞劇中的舞蹈語匯,為“戰士舞劇”的發展創新提供了可行性和發展依據。
(二)揭露現實,貼近大眾
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主戰場之一,文藝界始終抗爭在反法的第一線,用藝術的形式在精神上給予苦難的人民以鼓舞和寬慰。現實表現主義的現代性新舞蹈藝術作為當時的新生藝術形式,它與戲劇、音樂緊密結合,用寫實、暗喻、諷刺等多種方式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各類進步演出活動也催生了一批抗戰題材的表現主義作品。在梁倫這一時期的舞劇作品中,人們很容易發現其現實表現主義的創作方式。
在不斷的學習和自我完善中,梁倫形成了自己的現實主義舞劇創作風格。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他的舞劇創作初衷是對當前現實的思考和批判。他與同伴胡均根據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途中,不愿意做亡國奴的百姓們,被日軍瘋狂進攻和轟炸的真實事件創作出《饑餓的人民》,將切身的感受加注于作品中,在當時引起大眾的共鳴。他的另一部作品《花轎臨門》,受到小說家蕭紅《呼蘭河傳》的啟發,諷刺了封建主義的反動和官僚的腐敗。舞劇運用閩南音樂作為基調,運用鬧劇式的喜劇貼近大眾的接受程度,使其符合大眾的觀賞心理,為舞劇在群眾中生根發芽起到了鋪墊作用。就是這樣貼近生活、貼近大眾的舞劇作品,在精神上慰藉中國的勞苦大眾,使舞劇的群眾基礎越來越扎實,舞劇的發展也在梁倫和吳曉邦、戴愛蓮等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下,漸漸由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
三、梁倫的舞劇創作特征
(一)思想性
1.舞蹈要服務于大眾
“舞蹈要服務于大眾”是梁倫舞蹈創作思想的大方向。毛澤東在延安座談會的講話不僅對梁倫的舞劇指出一條道路,也成為當時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指南。在他創作的《乘風破浪解放海南》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舞蹈創作的服務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和工農兵,舞劇創作思想就是體現解放軍的生活,從原則上體現出他創作舞劇的思想性:反映人們當代生活,融合時代精神,呼應自然、回歸自由。而這些思想更加真實、全面地反映了人們的生活,使得舞蹈作品與人們實際生活更貼合。
2.舞劇要用情表達
在闡述美學觀點時,梁倫曾說:“舞從情中生,舞蹈以情動人,由此產生深刻的美感。”舞劇的情感表達展現的是編導的意圖。他還認為,編導創作舞蹈、舞劇作品是為了向觀眾傳達自己的思想,這種思想屬于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但在傳達的過程中,往往是通過感情的抒發來達成。觀眾欣賞舞劇,首先是受到情緒感染,產生情感共鳴,然后才提升為理性認識。因此,在舞劇中他的創作皆以情感人,《天快亮了》用情感表達勞苦大眾對于新中國的期盼,《乘風破浪解放海南》用情感表達對于解放軍戰士的敬意,《花轎臨門》用情感表達人民對于封建、官僚主義的痛恨……他認為,無論舞劇講述的是怎樣的現實,但情感的流露是一定要借助現實的情節展現出來,這才不失為一部好的舞劇。
3.舞劇要關注戲劇性
在“舞”與“劇”的關系上,梁倫對舞劇中戲劇要素的重視與他對舞劇藝術綜合性的肯定是聯系在一起的。在他看來,舞蹈、音樂、戲劇、美術這四種舞劇創作中的要素必須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又統一為一個整體,舞劇編導對這四方面的構思應當圍繞著舞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進行。在明確這一前提的基礎上,舞劇創作必須重視戲劇性,因為充分發揮舞劇中的戲劇要素是擴大舞劇表現力的手段、加深舞劇感人力量的辦法之一。進一步說,舞劇作品中的“舞”與“劇”必須緊密結合在一起。他認為,舞劇中的舞蹈場面必須與劇中人物行為發展相聯系,為舞蹈而舞蹈、與劇情游離的舞段是不可取的。
(二)時代性
梁倫的現實主義舞劇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在于他創作的舞劇主題具有時代意義,體現了時代精神。于平曾這樣評價:“20世紀40年代的‘新舞劇活動,吳曉邦主要致力于將國外現代舞蹈的表現技法與中國的現實生活相結合,從而深刻地反映民眾的生活;戴愛蓮則主要致力于深入中國民間采擷民眾生活中的舞蹈,從而使民眾生活的某個方面得到直接呈現;梁倫似乎‘兼學吳戴,深入民間采擷民眾生活中的舞蹈并以此作為反映民眾生活的舞蹈語言。”從抨擊黑暗、憧憬光明到體現戰士斗志昂揚精神的舞蹈,梁倫的舞劇都走在時代創作的前沿,創作的作品主題不脫離群眾生活和實際,用舞劇的方式替廣大人民發聲。
(三)藝術性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除了要解決好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和學習問題外,他還指出:“……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前進。”這一講話為舞劇工作者們指明了創作方向,舞劇作品的編創元素要取材于生活,但在展現方式上要高于生活,這樣舞劇編創才具有藝術性。梁倫在創作中受到吳曉邦以及延安座談會的影響,不斷突破、創新,他所嘗試創作的作品突出典型性、帶有普遍性。無論是舞劇《花轎臨門》《天快亮了》,還是后來的《乘風破浪解放海南》《保衛世界和平》,創作素材都源于大眾,但在呈現方式上富有獨特的藝術性。
(延邊大學)
作者簡介:王彥蘇(1995-),女,河南鄭州人,碩士,研究方向:音樂與舞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