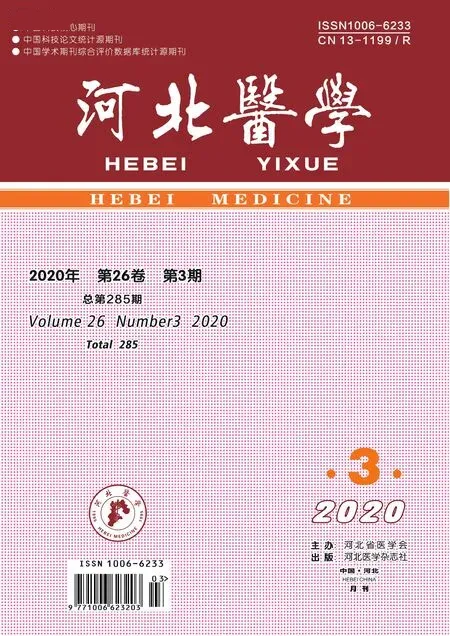角膜塑形鏡配戴后偏心對青少年近視患者視覺質量的影響及與并發(fā)癥的相關性研究
趙連凱
(遼寧省丹東市第一醫(yī)院, 遼寧 丹東 118000)
角膜塑形鏡能夠通過佩戴眼睛的方式改變角膜的暫時性形態(tài),以手術之外的方式改變近視眼睛的形態(tài),從而矯正近視,是臨床研究證明能夠控制青少年近視的有效治療方案[1,2]。而在佩戴后存在視覺質量改善不高以及各種并發(fā)癥的現象,包括視覺模糊、眩光等。有研究發(fā)現,偏心距離與視覺質量以及并發(fā)癥有密切的相關性[3]。本次研究通過對青少年近視患者角膜塑形鏡資料的回顧性分析,探討偏心距離與視覺質量以及并發(fā)癥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研究患者選擇范圍為2017年2月至2018年9月在我院眼科門診治療的近視患者,均選擇角膜塑形鏡治療近視。納入標準:①年齡范圍為6至18歲;②入組前沒有佩戴過角膜塑形鏡;③沒有眼部與全身性疾病;④均為右眼單眼近視,最佳矯正視力高于0.0;⑤近3周內沒有服用類固醇類藥物;⑥等效球鏡度(SE)在-6.75至-0.75D之間;⑦順規(guī)散光低于1.25D,逆規(guī)散光低于0.75,散光度在50%球鏡度以下;⑧資料完整的患者。排除標準:①存在眼部外傷史的患者;②合并眼部腫瘤的患者;③合并白內障、青光眼等其他眼部疾病的患者;④合并類風濕性關節(jié)炎的患者;⑤斜視的患者。本次研究患者共選取120例,其中男68例,女52例,年齡6至17歲,平均(10.15±2.23)歲,等效球鏡度-5.83至-0.97D,平均-(3.41±0.87)D。
1.2治療方法:在佩戴角膜塑形鏡之前,需要對入組患者的視力、眼壓、角膜地形圖以及角膜曲率進行檢測,排除角膜塑形鏡佩戴的禁忌癥。以檢測結果為依據完成鏡片的選擇,在佩戴鏡片30min后開始評價配鏡適合度,在確定鏡片的選擇方案后完成眼光,最終確認鏡片的處方。所有入組患者選擇的角膜塑形鏡均為夜間佩戴類型,每晚佩戴角膜塑形鏡的時間超過8h。
1.3觀察指標:對每個患者的右眼檢測角膜地形圖,檢測次數為3次,選擇成像效果最好的圖像。確定光學治療區(qū)域中心的過程中,首先選擇角膜地形圖的相關分析軟件,模擬橢圓區(qū)域并確定其中心,作為光學治療的額中心點。在佩戴塑形鏡前、佩戴后7d、3個月、6個月、1年測定偏心距離、中央角膜厚度、角膜曲率、角膜表面規(guī)則性指數(SRI)、角膜表面不對稱指數(SAI)、淚液分泌量、淚膜破裂時間(BUT)。所有指標均檢測3次,以平均值為最終結果。在開始治療后對患者保持每個月的復診隨訪,隨訪保持時間為1年,讓患者對隨訪期間出現的眩光、重影等并發(fā)癥情況進行記錄,以統(tǒng)計隨訪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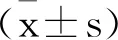
2 結 果
2.1偏心距離檢測結果:本次研究入組患者的偏心距離檢測結果,見表1。入組患者在各個時間點的偏心距離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所有患者的總偏心距離中位數為0.55mm,以0.55mm的偏心距離為依據進行分組,偏心距離在0.55mm以上的患者65例,作為高偏心組,偏心距離在0.55以下的患者55例為低偏心組。

表1 入組患者偏心距離檢測結果
2.2兩組患者治療前后淚膜功能指標比較:兩組治療前的BUT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佩戴后各時間點的BUT指標均相比治療前明顯降低(P<0.05),高偏心組患者治療后的BUT指標均相比低偏心組明顯降低(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不同時間點的BUT指標比較
2.3兩組治療前的基礎淚液分泌量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佩戴后各時間點的淚液分泌量指標均相比治療前明顯減少(P<0.05),高偏心組患者治療后的淚液分泌量指標均相比低偏心組明顯減少(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不同時間的基礎淚液分泌量指標比較
2.4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角膜形態(tài)指標比較:兩組治療前的中央角膜厚度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佩戴后各時間點的中央角膜厚度指標均相比治療前明顯減少(P<0.05),高偏心組患者治療后的中央角膜厚度指標均相比低偏心組明顯增加(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不同時間的中央角膜厚度指標比較
2.5兩組治療前的角膜曲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佩戴后各時間點的角膜曲率指標均相比治療前明顯降低(P<0.05),高偏心組患者治療后的角膜曲率指標均相比低偏心組明顯升高(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不同時間的角膜曲率指標比較
2.6兩組治療前的SAI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佩戴后各時間點的SAI指標均相比治療前明顯升高(P<0.05),高偏心組患者治療后的SAI指標均相比低偏心組明顯升高(P<0.05),見表6。
2.7兩組治療前的基礎淚液分泌量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佩戴后各時間點的淚液分泌量指標均相比治療前明顯升高(P<0.05),高偏心組患者治療后的淚液分泌量指標均相比低偏心組明顯升高(P<0.05),見表7。

表6 兩組患者不同時間的SAI指標比較

表7 兩組患者不同時間的SRI指標比較
2.8兩組患者的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比較:高偏心組患者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為27.69%(18/65),其中眩光15例、重影3例,低偏心組患者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為7.27%(4/55),其中眩光3例、重影1例,高偏心組患者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明顯高于低偏心組(χ2=15.273,P=<0.01)。
2.9所有患者并發(fā)癥的相關因素分析:以并發(fā)癥發(fā)生情況為因變量,以年齡、性別、散光、等效球鏡度、普通眼鏡佩戴史、偏心距離等為自變量,多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8與表9。偏心距離為患者角膜塑形鏡佩戴后并發(fā)癥的高危險因素(P<0.05),同,見表8。

表8 并發(fā)癥指標的多因素分析
3 討 論
角膜塑形鏡配合光學治療是當前青少年近視的重要治療方案,已經有很多臨床研究證實這一方案對于視覺功能改善有良好的效果。而在光學治療過程中治療區(qū)域的偏心問題是無法避免的,對于偏心與視覺質量以及安全性的研究還不夠完善。已經有部分臨床研究證實,偏心問題與視覺功能以及安全風險都有較為密切的關系[4]。
本次臨床研究的結果顯示,在角膜塑形鏡治療過程中,偏心距離并沒有隨著時間的延長而發(fā)生明顯的改變,與其他臨床研究結果較為相近[5]。表明,偏心問題在角膜塑形鏡佩戴過程初期就存在,與佩戴時間不存在明顯的關系。而佩戴1年內的基礎淚液量以及淚膜破裂時間統(tǒng)計顯示,在治療7d、3個月、6個月、12個月后,所有患者的指標均明顯減少,而高度偏心患者的淚液量與淚膜破裂時間減少更加明顯,表明角膜塑形鏡佩戴后患者的淚膜功能會受到明顯的影響,而偏心距離較大的患者淚膜功能的影響更加嚴重。在相關性分析結果中,偏心距離與淚膜功能指標表現為負相關的關系。有學者認為,該現象是由于在佩戴塑形鏡的過程中,眼淚流動方式發(fā)生改變,從而導致淚膜穩(wěn)定性的改變[6]。以此為基礎推測,偏心距離的增加,佩戴塑形鏡后角膜形態(tài)的改變更加明顯,從而導致淚膜功能指標的改變。
SRI是角膜表面規(guī)則性指數,數值越高則角膜的表面形態(tài)規(guī)則程度越低。SAI為角膜表面對稱性指數,數值越高則角膜的表面形態(tài)對稱程度越低。本次臨床研究的結果中,在佩戴角膜塑形鏡后,患者SAI與SRI均明顯升高,而偏心距離較大的患者兩個指數升高更加嚴重。表明佩戴塑形鏡會對角膜表面形態(tài)產生較大的影響,偏心距離較大的患者,角膜表面規(guī)則性與對稱性越低。在相關性分析的結果中,偏心距離與SRI以及SAI均表現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該結果與其他臨床研究的結果較為相近[7]。在中央角膜厚度以及角膜曲率的統(tǒng)計結果中,佩戴塑形鏡后患者的中央角膜厚度以及角膜曲率均明顯降低,而偏心距離較大患者的指標降低相比偏心距離較小的患者較為輕微。
隨訪過程中,偏心距離較大的患者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明顯升高,表明偏心距離會明顯影響到角膜塑形鏡佩戴患者的并發(fā)癥。而在單因素以及多因素回歸分析的結果中,年齡、性別、散光、等效球鏡度、普通眼鏡佩戴史均與并發(fā)癥沒有明顯的相關性,而偏心距離與并發(fā)癥有明顯的相關性,證實偏心距離是患者佩戴過程中并發(fā)癥發(fā)生的主要影響因素。
綜上所述,角膜塑形鏡治療青少年近視的過程中,偏心距離會影響患者的視覺功能,導致淚膜穩(wěn)定性的明顯下降,同時角膜形態(tài)也會受到明顯的影響,而偏心距離為并發(fā)癥發(fā)生的重要危險因素,需要在臨床中給予足夠的重視,減少偏心距離以改善臨床預后并提高安全性。本次研究的研究時間較短,缺乏對于患者長期視覺功能以及并發(fā)癥的統(tǒng)計,需要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