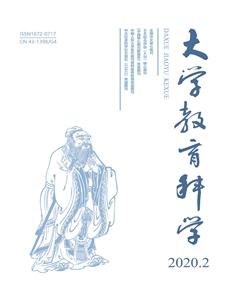雙學士學位、聯合學士學位等概念正義
摘要: 輔修學士學位、雙學士學位、聯合學士學位三種學士學位類型的提出,對推動復合型人才培養、促進教育資源共享、滿足學生個性化與多樣化的學術興趣有積極意義。然而,從學理和域外經驗看,《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管理辦法》對這三種學位類型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頗。輔修不同于學位,亦不授予學位,“輔修學士學位”雜糅了“輔修”“主修”與“學位”三個概念,容易帶來誤解。雙學士學位不同于雙學士學位復合型人才培養項目,后者窄化了前者,導致雙學士學位的覆蓋面大大縮小。聯合學士學位不止限于國內、國際和校際之間,還包括學校內部更具結構性、具有特定名稱的學士學位類型。
關鍵詞:輔修學士學位;雙學士學位;聯合學士學位;《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管理辦法》;學位制度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0)02-0083-07
基金項目: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2015年度一般項目“美國研究型大學‘個人專業運行機制研究”(15YBA146)。
2019年7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發了《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1]。《辦法》的一大亮點是,提出可授予輔修學士學位、雙學士學位、聯合學士學位三種類型學士學位并對授予要求分別作出了規定,解決了長期以來我國高校自行其是而缺乏政策依據的問題[2](P36-40)。毫無疑問,政策變革將有助于推動復合型人才培養、促進教育資源共享、更好地滿足學生個性化與多樣化的學術興趣。遺憾的是,《辦法》對以上三者的理解似乎存在一定的偏頗,因此很有必要對其概念進行專門探討。由于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源于西方特別是歐美,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美國的相關實踐經驗進行比較和分析。
一、輔修或學位≠“輔修學士學位”
《辦法》第十四條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概念“輔修學士學位”。關于其受眾,國務院學位辦負責人在相關回答中指出:“對于全日制學生在本校自主選擇讀多個學位的,可以采取輔修學士學位方式。”[3]如何看待這一提法?這需要對其中涉及的概念逐一進行分析。
(一)輔修及其要求
所謂輔修,對應的英文“Minor”有兩個相關解釋:一是某學院或大學學生聚焦的第二學科領域,或選擇了一個第二聚焦領域的學生[4]。前者國內又稱為輔修或副修專業。二是作為一所學院或大學的學生選擇或擁有一個第二聚焦領域[4]。由此可見,“輔修”的核心內涵是第二聚焦領域。所謂第二,是與主修(Major)的第一(基本)相對的。為了取得畢業文憑、獲得學士學位,學生至少要選擇并完成一個主修。所謂聚焦領域,即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確定一個重點或聚焦點并在該領域完成一定數量的課程學習,達到深入掌握某個知識領域的效果[5]。簡而言之,就是指課程體系圍繞某個領域呈現一定的聚焦或集中。
從性質而言,輔修一般不是大學的硬性要求,而是大學提供的拓展與深化主修的機會。從學術要求來看,無論是課程數量,還是學習時間投入,輔修的要求都比主修要少。具體來說,輔修的課程修讀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按課程門數來要求。如麻省理工學院的輔修由5~7門課程組成,典型的項目包括6門課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文理學院的輔修至少要達到5門課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輔修通常需要在某個特定的學習領域選修6~8門課程。有的大學沒有明確規定輔修的課程門數,而是根據主修所要求的課程數量進行確定,如賓夕法尼亞大學規定一個輔修通常需要完成與其領域相同的主修課程數量的一半。二是按學分數來規定。輔修學分數通常約為主修學分數的一半。比如華盛頓大學的主修至少要求50個學分,而大多數輔修只要求25~35學分[6](P136)。
從結果來看,學生完成輔修后,學校一般并不會授予學位,甚至不會單獨發放輔修證書。如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華盛頓大學學生的輔修會體現在成績單上,而不會出現在畢業文憑上[6](P138)。然而,我國《辦法》規定:“輔修學士學位在主修學士學位證書中予以注明,不單獨發放學位證書。”這或許是因為美國學生完成的是“輔修”,而我國學生完成的是原本的主修之外的“其他本科專業”。因為漢語的多義性,“輔修學士學位”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誤解:完成美國意義上的輔修(Minor),獲得中美共同意義上的學位(Degree)。
令人擔憂的是,近期發布的《教育部關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第12條“推進輔修專業制度改革”中提出“促進復合型人才培養,逐步推行輔修專業制度,支持學有余力的全日制本科學生輔修其它本科專業”,同時還提出“輔修專業應參照同專業的人才培養要求,確定輔修課程體系、學分標準和學士學位授予標準”[7]。這無疑更進一步混淆了輔修與主修在修讀要求及結果上的差別。
(二)學位及其要求
所謂學位,是指“授予個人的一種學術稱號或學術性榮譽稱號,表示其受教育的程度或在某一學科領域里已達到的水平,或是表彰其在某一領域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8]。一般來說,學位“必須以高等教育的相應層次的教育作為基礎或對象。兩者類似名與實的關系,學位既不可能脫離相應層次的教育,也不可能自身直接成為培養人的活動”[9]。由此可見,學位以教育為基礎和前提。通過教育,被授予學位者獲得了滿足學位授予標準的相應知識、能力和學術成果。
進一步來說,人們獲得學位的教育基礎和前提就是主修。他們只有完成主修的所有要求,方能獲得相應的學位。對雙學位而言,受教育者獲得兩個學位的基礎是修讀兩個主修,且兩個主修所在的學科門類或指向的學位名稱不能相同,兩者并不存在主次或主輔(副)之分。而對于輔修學生來說,因為他在某個聚焦領域只完成了少量課程,所以無法獲得學位。
由上可見,輔修、學位與“輔修學士學位”并非一回事。輔修不同于學位,輔修完成后亦不授予學位。盡管“輔修學士學位”的提法為“學有余力的學生輔修其他本科專業”[1]后獲得的學士學位提供了政策上的統一稱呼,但卻雜糅了主修、輔修和學位這三個概念,存在不夠精準的問題,極易帶來誤解。從國外經驗來看,根據筆者目前所見的資料,美國大學也沒有“輔修學士學位”這個概念。在美國的語境中,輔修即是輔修,學位即是學位,二者不會雜糅在一起。可以說,“輔修學士學位”是我國學位主管部門給出的一個特殊概念。
(三)輔修學士學位”概念何以產生
為什么我國將“輔修”與“學位”兩個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這可能是處理長期以來我國高校自行授予雙學位而國家又沒有明確制定相關政策的事后辦法。
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高校開始實行“雙學位”制度,至今已將近40年[10]。然而,根據教育部此前在官網上對網友“關于第二學位和雙學位的咨詢”的答復,在“教育部現行文件中,沒有關于雙學位的提法或相關文件”,“國家目前沒有實行所謂的‘雙學位制度”,“我國對雙學位教育暫無明確政策”,也“尚沒有適用于‘雙學位的相應政策”。也就是說,雙學位教育此前一直是各個高校自行開展的,它們自行授予的雙學位證書不被國家承認。這也是我國高校的雙學位被稱為“民間版雙學位”的原因所在[2](P36-40)。
“民間版雙學位”的一個尷尬之處是,因為學生原有的、國家承認的學位證書是單獨發放的,所以高校頒發的雙學士學位證書在學生原有學位基礎上再增加一個校定的不被國家認可的另外一個學位,嚴格來說并不是兩個學位。例如,很多高校該證書名稱為“雙學士學位證書”,內容卻多為“在***第二專業(雙學位專業)完成了培養方案規定的課程(***年制本科學習計劃),成績合格。經審核,符合學士學位授予條件,授予***學學士學位”。“輔修學士學位”概念的提出,可以避免這種名不副實的問題,也可以給予學生另外修讀的一個或以上學位以國家制度上的認可。“目前,我國實行的還是國家學位制度,不是學校學位制度。所有的學位必須是國家承認才算數。”[11]這就決定了在當前無法推行學校學位制度的情況下,學位獲得國家承認是一條必由之路。
二、雙學士學位≠雙學士學位復合型 ? 人才培養項目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具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普通高等學校,可在本校全日制本科學生中設立雙學士學位復合型人才培養項目。”這是國家第一次從專門政策層面賦予“雙學士學位”的合法性,然而在實踐中僅僅設立和實施雙學士學位復合型人才培養項目(以下簡稱“雙學士學位項目”)卻嚴重窄化了雙學位的覆蓋面。同時,項目“所依托的學科專業應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亦存在要求過高的問題。
(一)雙學士學位
雙學位(Dual/Double Degree)與單一學位(a Single Degree)相對應,是指學生修完兩個主修后,可獲得兩個獨立的學位。對雙學士學位而言,就是指學生在攻讀一個主修、預計獲得一個學士學位的同時,攻讀另一個主修并將獲得另一個學士學位。其中,前者為取得畢業文憑、獲得學位的必要要求,可稱之為“基本的主修”,而后者則是學生出于個人的學術興趣或未來的發展需要所做的額外選擇,可稱之為“額外的主修”[2](P36-40)。
從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經驗看,這兩個主修和兩個學位非學校所指定,而是學生的自主選擇。校方給予的限制往往是,兩個學位的名稱不能相同,或兩個學位要分屬于不同的院系[2](P36-40)。盡管有這種限制,但學生跨學科、跨院系選擇另一個主修、攻讀第二個學位的自由度仍然比較大,原因主要在于最終導向某一學位或者某一個學院所擁有的主修或項目有很多。比如,普林斯頓大學2013年共有文科學士和工學士兩種本科學位,其中前者對應的有29個學習項目,后者對應的有6個學習項目[6](P156)。這么一來,學生就有174種雙學位的修讀選擇。
(二)“雙學士學位項目”
根據《辦法》,“雙學士學位項目”須由專家進行論證,應有專門的人才培養方案,經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表決通過、學校黨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同意,并報省級學位委員會審批通過后,通過高考招收學生。由此可見,不同于美國雙學位依托的主修或項目可由學生根據規則自由組合,我國的“雙學士學位項目”是特定的,即組合的若干項目已經事先由學校設計、通過并由省級學位主管部門批準;是結構性更強的,而不是學生完全憑自身興趣所進行的松散聯合。
這很明顯受到一直以來教育目的項目化、課程化傳統的影響[2](P36-40)。長期以來,我國高校要實現相應的教育目的,往往借助于相應的專門機構、專業或項目、課程的設置。其中,專業或項目是人才培養的基本單位或組織形式。要落實不同于以往的雙學位教育,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單獨設立一套專門的“雙學士學位項目”并制訂相應的教學計劃、選派專門的師資等,而不是去思考如何將雙學位教育與各個高校原有的專業教育相融合。這無疑將導致我國的雙學位教育與若干專業掛鉤。也就是說,學生只有就讀這些依托專業,才能最終獲得雙學位,而不是像美國研究型大學那樣,同一個學位可以有多個相關主修,學生能以這些現有的主修為依托去攻讀雙學位(后者僅是前者修習所獲的結果)。“雙學士學位項目”雖然增加了學生的選擇,可以促進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然而因為其自成體系而沒有與各校現有的專業相打通,覆蓋面無疑將非常有限,復合型人才培養項目的生成性也將大受限制。
綜上可見,《辦法》中提出的“雙學士學位項目”并不是一般的雙學位(項目),而更相當于美國的協同雙學位項目。美國開展協同雙學位項目的高校以賓夕法尼亞大學為代表。協同雙學位項目其實是為學生提供一個跨學科學習機會。通過它,學生可以完成一個專門的課程體系并從賓夕法尼亞大學四個本科學院中的兩個學院獲得兩個學位[6](P159)。其中,沃頓商學院的協同雙學位項目僅有4個,由該院與文理學院、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法學院等其他三個本科學院合作提供[6](P159)。
對比發現,協同雙學位項目與雙學位(項目)的相同點包括:涉及兩個主修或學習領域,而且最終都獲得兩個學位;組織載體都涉及兩個不同的學院。究其區別,在于雙學位(項目)不提供專門的課程或沒有限定的學習課程。學生可以完成兩個不同學系的傳統課程,獲得兩個不同的學位[6](P144)。如此一來,雙學位(項目)的選擇余地就遠遠大于協同雙學位項目,因為只要選擇的兩個主修符合雙學位的規定條件,學生可以進行任意組合,而協同雙學位項目則由大學事先設計好,數量也很有限。
(三)“雙學士學位項目”所依托的學科專業應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
《辦法》規定,“雙學士學位項目”必須堅持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所依托的學科專業應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且分屬兩個不同的學科門類。
這個要求不可謂不高,實際上也將“雙學士學位項目”限定為那些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2018年,我國共有普通高校2 663所(含獨立學院265所),其中本科院校1 245所[12]。然而截至2018年9月,全國有博士點的高校僅有344所,大多數高校博士點在10個以下[13]。如此算來,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數僅占本科高校總數的27.63%。由此可見,這一條規定無形中將我國大多數本科高校排除在外,也使得這些高校的本科生無緣“雙學士學位項目”。這很明顯是不公平的。從雙學士學位到“雙學士學位項目”再到具備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才可申辦該項目,雙學位教育的相關范圍無疑在一步步縮小。
那么,“雙學士學位項目”依托的學科專業是不是非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不可?實際上,從“雙學士學位項目”的本質來看,它是雙學位的一種特殊類型,最基本的要求是涉及的兩個學科專業都要具備學士學位授予權。當學士學位授權點的人才培養質量能夠保證的時候,要求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無異于多余。相反地,當學士學位授權點的人才培養質量無法保證的時候,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亦無濟于事。在我國高校普遍重科研、輕教學的背景下,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并不必然就表示其學士學位授權點的人才培養質量更高。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很多一流研究型大學也沒有明確要求雙學位依托的學科專業必須具備博士學位授予權。
三、聯合學士學位≠普通高校之間授予聯合學士學位
《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具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普通高等學校之間,可授予全日制本科畢業生聯合學士學位。”然而,聯合學士學位不止限于國內、國際和校際之間,還包括學校內部更具結構性、具有特定名稱的學士學位類型。
(一)聯合學位的三種類型
從目前所見的資料看,聯合學位(Joint/Combined Degree)包括三種情況,覆蓋了高校之間和高校內部兩種類型:
一是指通過兩所或兩所以上高校合作培養所授予的學位,其中涉及的高校可以是一個國家的,也可以是不同國家的。這種類型的聯合學位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開設的課程是由若干所高校聯合開發或認可的;第二,參與聯合學位培養的學生到合作方院校完成部分學位課程;第三,學生花較長時間在合作方院校學習;第四,學生在合作方院校學習的期限和通過的考試得到完全、自動承認;第五,合作院校的教授到對方院校教學,參與課程制定,參加聯合招生與考試委員會;第六,修完全部課程后,學生獲得參與合作院校授予的國家學位,或者獲得由合作院校聯合頒發的“證書”或“文憑”[14]。這種情況以歐洲較為常見。很明顯,我國《辦法》中提到的“普通高等學校之間授予聯合學士學位”傾向于這種類型。
二是指“學生同時學習兩個學位的課程”,“學校在課程設置方面專門進行設計安排,考慮到學生畢業求職和將來的發展,將兩個學位的學習很好地組織、結合起來,還提供一些交叉學科的課程”[15],學生畢業時可以同時得到兩個學位。這種情況以美國較為常見。比如,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聯合學位”由文理學院與工程學院聯合提供,為期五年,學生最終可獲得兩個學位,其中一個為文理方面的文科學士或理科學士,一個為某個工程領域的理科學士[6](P143)。再如,密歇根大學的聯合學位依托由文理學院和其他學院合作提供的聯合學位項目,完成該項目的學生可以分別在兩個院系獲得學位,其中本科聯合學位項目有5個[6](P160)。這種類型的聯合學位項目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協同雙學位項目非常相似:涉及兩個主修專業或學習領域;學生最終都獲得兩個學位;組織載體都涉及兩個不同的學院;兩者都是既定的,課程體系在結構上也更強調整合而不像雙學位(項目)那么松散,因此課程總數也較雙學位(項目)少。
三是學生聯合兩個不同領域的學習,最終可獲得一個聯合的學位。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可聯合一個人文學科領域(共19個領域)與一個工程或科學領域的學習并獲取“人文與工程”理科學士學位或“人文與科學”理科學士學位[6](P143)。這種情況較為少見。
(二)聯合學位與雙學位
從三種類型來看,聯合學位特別是其中的第二種類型和雙學位尤其是協同雙學位存在一定的交叉。
不同于攻讀雙學位的學生可以根據一定的限制性條件自主選擇學位依托的主修,協同雙學位和聯合學位(類型二)的提供院系、聯合的主修專業或領域范圍及其最終獲得的兩個學位一般都是既定的:在提供院系方面,協同雙學位或聯合學位項目涉及的兩個學院都是不同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協同雙學位項目由沃頓商學院與另外三個本科學院中的一個合作提供,密歇根大學的聯合學位項目則由文理學院與另一個學院合作提供;在主修專業或領域范圍方面,每個項目所聯合的兩個部分亦不同,這一點從賓夕法尼亞大學協同雙學位項目的名稱上就可以明顯看出來,例如“生命科學與管理項目”、“管理與技術項目”等。至于密歇根大學的聯合學位項目,盡管很多從名稱上看是一個專業或領域,但實際上都涉及到文理學院人文科學與其他學院的某個專業或領域方面的學習。比如,“工程”本科聯合學位項目是為那些希望同時在工程學院的技術性學習與文理學院的物理和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發展深度理解的學生所設計[6](P163)。
兩者除了存在交叉和重復以外,聯合學位還有雙學位所不具備的含義,主要即前文所說的第一種類型。可見,為了避免與“雙學士學位項目”相混淆,我國《辦法》將聯合學士學位限定為“普通高等學校之間授予聯合學士學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普通高校之間授予聯合學士學位的意義
在我國,聯合學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要限于中外聯合辦學項目,即我國高校與其他國家高校聯合舉辦的學位項目,而國內高校之間鮮有聯合學位。
《辦法》提出我國普通高校之間授予聯合學士學位,無疑將擴大聯合學位在本土的外延,豐富聯合學位類型;推進跨校聯合人才培養,加強國內高校之間的合作與聯系;推動不同高校之間發揮各自優勢,協同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促進國內尤其是同一區域內的優質教育資源共享,增進教育公平。
四、對三種學士學位類型的改革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辦好我國高校,辦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個核心點。貫徹總書記指示,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必須進一步強化本科教育的基礎地位,完善制度設計,形成高水平的本科人才培養體系[3]。然而,本科教育制度設計包括高水平的本科人才培養體系設計的一個前提是對相應的概念有準確的理解。唯有如此,才能帶來正確的教育實踐操作方式。正如德國教育理論家沃爾夫岡·布列欽卡所說:“沒有準確的概念,明晰的思想和文字也就無從談起。”[16]基于前文的分析,筆者嘗試提出以下建議:
(一)“輔修學士學位”:區分輔修與主修的內涵與結果,落實高校學位授予自主權
前文已述,根據美國經驗或我國很多高校長期以來的實踐,輔修不等于主修,只有主修方能獲得學位。然而,《意見》提出“輔修專業應參照同專業的人才培養要求,確定輔修課程體系、學分標準和學士學位授予標準”。隨著實踐的推進,這種對輔修與主修內涵與結果的混淆將會不斷強化。
《辦法》中提及的“輔修學士學位”實際上是要求不甚嚴格的雙學位或多學位,比如只規定“輔修學士學位應與主修學士學位歸屬不同的本科專業大類”,而沒有規定必須分屬不同的學科門類。進一步來說,“輔修學士學位”并不是一種特殊的學位類型,只不過是學生在攻讀原有的主修、獲得一個學位之外,另外攻讀一個或一個以上主修、獲得一個或一個以上學位而已,這兩個或多個學位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有關部門之所以在學位名稱前冠之以“輔修”,還是受我國固有的主修、輔修觀念的慣性影響。對于學位而言,實際上并沒有主、輔修之分。
《辦法》將學位細分為輔修學士學位、雙學士學位、普通高等學校之間授予的聯合學士學位,從而在實踐中對學位進行了區分,特別是前兩者將雙學位呈現為學生可自由組合的和學校提前設計的兩種形式。實際上,學位是根據事先規定的學位授予要求以及學生受教育后所達到的水平而授予的[17](P69-74)。因此,與其提出“輔修學士學位”這個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不如淡化主、輔修的觀念,規定學生在校期間可以多個主修為基礎攻讀多個學位,且賦予高校更大的學位授予權,保障高校開設多個主修、授予學生多個學位的權利。
(二)“雙學士學位”:從專門項目到開放選擇,從博士學位授權點高校到學士學位授權點高校
當下,重視并通過制度設計滿足學生個性化和多樣化的學術興趣和發展需要已成為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趨勢[17](P69-74)。然而,如果專門設計某個學位項目,限定只有該項目的學生才能獲得該學位,或者限定該項目必為具備博士學位授權點的高校才有資格舉辦,那就將大多數學生排除在外,這不僅有失公平,也導致其受益面極其有限。
因此,我國的“雙學士學位”應改變“小眾價值觀”[18],拓展受眾群體。一要從專門項目轉變為開放選擇。即從教育教學資源共享、課程教學之間打通的角度出發,讓雙學位融到正常的教學中去,而不是單獨成為一個系統[19]。學生可以根據攻讀雙學位的規則,在本校范圍內自由選擇依托的主修。二要從具有博士學位授權點的高校拓展到所有具有學士學位授權點的高校。相比提高學位層次,嚴格學士學位授權點審批和考核、保證本科人才培養質量才是根本。從未來發展而言,“雙學士學位項目”應像《辦法》中對聯合學士學位所作的規定一樣,“所依托的專業應是……具有學士學位授權的專業”。
(三)“聯合學士學位”:從校際之間到校內校際并重
雖然有學者將“聯合學位”定義為“學生在兩所或多所跨境合作機構學習,在完成合作機構共同規定的學業要求后,由合作機構共同為其授予單一學位的證書活動”[20],但從前文來看,聯合學位并不限于校際之間。事實上,不僅高校之間需要協同育人,而且高校內部更要首先考慮如何多學科育人。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高校的學科數量在不斷增加,當初的單科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大部分已經發展為學科較為齊全的大學。然而,當前我國高校學科之間往往各自為陣,甚至學科壁壘森嚴。因此,從學科間的聯系特別是從多學科資源轉化為人才培養資源的角度而言,我國很多高校還無法稱之為名副其實的綜合性大學。對此,如能將聯合學士學位的外延拓展到校內校際兩種類型,尤其是積極開發第三種類型的聯合學位,無疑有利于加強高校內部學科之間的關聯,促進多學科交叉、共生。
五、結語
我國近代高等教育是一個“舶來品”。百余年里,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學歐美——學蘇聯——再學歐美的幾個發展階段[21]。作為起源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制度,學位包括雙學位、聯合學位落地于我國必先要經過一個“消化”后再發展的過程,否則“橘生淮南謂之橘,植于淮北謂之枳”[22]。盡管學位制度應彰顯“中國特色”[23],但我們在借鑒相關概念推進實踐時首先應把握其精神實質。慶幸的是,《辦法》規定:“為平穩過渡,設置三年過渡期。過渡期期間,各單位按原有政策執行,有條件的可按《辦法》執行。過渡期結束后,2022年所有單位按《辦法》執行。”因此,面對《辦法》中對三種學士學位類型的理解偏頗,教育學界和國家相關主管部門可在這個過渡期內,進一步對涉及的相關概念及其操作方式進行研究,以期更加貼近于原義。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管理辦法[EB/OL].(2019-07-09)[2019-10-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1907/t20190726_392378.html.
[2] 張曉報,陳慧青.我國高校雙學位教育的困境與出路[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7(11).
[3] 曹建.完善本科人才培養機制 提升學士學位授予質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就《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管理辦法》答記者問[EB/OL].(2019-07-26)[2019-10-18].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1907/t20190726_392376.html.
[4] Wiktionary.Minor[EB/OL].(2019-09-28)[2019-10-
18].https://en.wiktionary.org/wiki/minor#English.
[5] 張曉報.美國研究型大學跨學科專業教育的實踐及啟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9(05):92-103.
[6] 張曉報.美國研究型大學跨學科人才培養模式研究[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7] 教育部.教育部關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EB/OL].(2019-09-29)[2019-10-2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11_402759.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8] 秦惠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大辭典[Z].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1994:3.
[9] 葉紹梁.學位的概念及其與研究生教育關系的辨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99(05):65-70.
[10] 李莉.我國大學輔修與雙學位制改革的回顧與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09(01):60-62.
[11] 盧義杰.民間版雙學位走到政策十字路口[N].中國青年報,2012-10-15(07).
[12]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年度發布[EB/OL].(2019-02-26)[2019-10-18].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19/50340/sfcl/201902/t20190226_371173.html.
[13] 青塔.備受關注的博士學位點,各大高校都有多少個?[EB/OL].(2018-09-07)[2019-10-18].https://www.cingta.com/detail/6738.
[14] 楊輝,許明.聯合學位:歐洲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趨勢[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4(01):52-55.
[15] 葉桂芹,張良平.聯合學位:培養復合型人才的新模式[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2(05):77-80.
[16] [德]沃爾夫岡·布列欽卡.教育科學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議[M].胡勁松,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
[17] 張曉報.清華大學本科榮譽學位透視[J].高校教育管理,2017(05).
[18] 別敦榮.一流大學本科教學的性質、特征及建設路徑[J].中國高教研究,2016(08):7-12.
[19] 鄔大光.本科教育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改革[N].科學時報,2008-08-19(08) .
[20] 李海生.研究生教育國際合作學位項目類型探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3(12):47-53.
[21] 鄔大光.跟跑與領跑: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道路選擇[N].中南大學報,2018-01-16(02).
[22] 仇鵬飛.跨國碩士雙學位項目與聯合學位項目的模式、特征及實施建議[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01):49-54.
[23] 譚光興,馮鈺平.中國學位制度變遷的邏輯——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J].大學教育科學,2019(05):22-27.
Analysis of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Joint Bachelor's Degree and Minor Bachelors Degree
ZHANG Xiao-bao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ree types of bachelor's degree, minor bachelor's degree,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and joint bachelor's degree,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shar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atisfying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and diverse academic interest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heory and foreign experienc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authorization and award of bachelor's degree” show some bias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degree. A minor bachelors degree is considered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degree, and it does not confer as a degree. The concepts of "minor", "major" and "degree" are mixed in minor bachelors degree, which is easy to be misunderstood.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is different from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compound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which has narrowed its scope resulting in the reduced coverage of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Joint bachelors degrees are not limited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university programs, but also include more structured and designated types of bachelor degrees betwee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minor bachelor's degree; double bachelor's degree; joint bachelor's degre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authorization and award of bachelor's degree”; academic degree system
(責任編輯 ?黃建新)
收稿日期:2019-10-30
作者簡介:張曉報(1987-),男,安徽霍邱人,教育學博士,湖南科技大學教育學院講師,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員,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理論、高等教育管理、比較高等教育研究;湘潭,4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