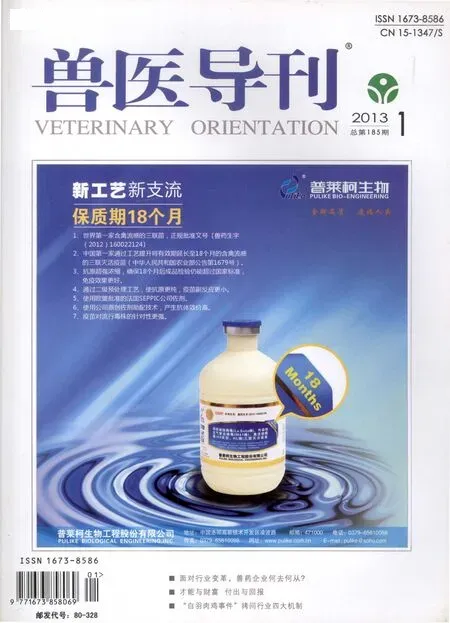自制酸奶技術
肖仁榮, 張玉文, 李友良
(1.重慶市南川區畜牧獸醫局,重慶南川 408400;2.北京小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北京朝陽100029; 3.湖北省黃梅縣農業局,湖北黃梅435500 )
自制酸奶依據Q/HJY01-2007(自制酸奶)企業標準,適用于以鮮牛乳為原料,加入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嗜熱鏈球菌、保加利亞乳桿菌等發酵而制成。自制酸奶由于不添加增稠劑、防腐劑,以鮮奶釀造純天然、口味純正、活性菌量高、多口味的優勢而滿足消費者的高要求。自制酸奶打破了唯有廠家才能生產的神秘性,將其作為一項實用技術和家廚常識,普及到酸奶店和百姓家庭已成為必然。本文僅以開酸奶店自制酸奶為例做簡單介紹。
一、酸奶店開業須知
(一)門店準備可選窗口店、店中店(進入商場、學校食堂等)或專業標準店作為門店,選址以旅游區、商區、學區、大型社區的2、3類街道為佳,營業面積根據自身條件及當地衛生部門要求確定。一般標準店:操作間使用面積6 m2以上(如無滅菌間的小店可將操作間直接設計成無菌間);營業間使用面積10 m2以上。標準店使用總面積在20 ~ 50 m2為宜。
(二)材料準備
1.酸奶發酵機1臺。發酵酸奶使用(帶混料桶、溫度計、攪拌棒、過濾網)。
2.牛奶滅菌混料機1臺。如選擇奶農提供的未經滅菌的生鮮牛奶,需使用本機。
3.乳酸菌粉。發酵酸奶的專用菌種。
4.臥式、立式冷藏展柜各1臺。展示儲存成品酸奶等(也可根據自己的經營面積選擇其一)。
5.其它輔助小電器。奶昔機,豆漿機、微波爐、飲水機、電磁爐等,可根據需要自主選擇。
6.包裝物。專業廠家生產的酸奶碗、杯(一般選擇250~350 ml)等。
以上設備可咨詢北京小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到相關企業購買。
(三)可自制的酸奶品種可根據當地口味需求,自制以下風味酸奶品種:
1.原味酸奶系列:原味酸奶、大豆酸奶、酸奶酪。
2.果醬酸奶系列:藍梅、草莓、桑葚、情人果、奇異果醬等。
3.果凍酸奶系列:芒果、荔枝、獼猴桃、葡萄、夢幻果等。
4.養生酸奶系列: 蜂蜜、玉米、綠茶、蘆薈酸奶等。
5.奶昔系列:蘋果、芒果、菠蘿、草莓、藍莓等。
6.蜜豆酸奶系列:紫花豆、紅豆、白豆、黑豆、豌豆。
7.干果酸奶系列:果仁、花生、黑芝麻、葡萄干、杏仁等。
8.水果撈系列:什錦酸奶、芒果酸奶、草莓酸奶、蘋果酸奶等。
9.酸奶冰淇凌系列:蜜豆、果醬、奶果仁、果凍等。
二、自制酸奶工藝流程
工藝流程:牛奶滅菌 →降溫接種 →灌裝、發酵 →酸奶冷藏 →銷售。
(一)牛奶滅菌將新鮮牛奶通過滅菌混料機濾網、倒入機內桶中(祛除雜質)。開啟滅菌機開關,機器開始加熱煮奶→煮到80℃左右時加入砂糖攪拌→用濾網祛除上浮的奶沫→煮到90℃時關機、保持5分鐘。用隨機溫度計檢測溫度,防止牛奶煮沸溢出。第一次使用,要將設備內接觸牛奶的不銹鋼桶、攪拌棒、濾網、出奶口龍頭等清洗干凈,將10 kg左右的清水倒入機器桶內燒開,以將設備徹底消毒。
(二)降溫/接種將夾層中熱水放出、進冷水循環冷卻牛奶(或將牛奶緩慢放出到不銹鋼桶中、放冷水池中攪動降溫),牛奶降溫到43℃時、投入菌種并充分攪拌均勻。注意:如攪拌不勻會有個別杯不凝固、發酵不成功。
(三)灌裝/發酵將牛奶分配到各個小容器中,加蓋入機。開機,設定發酵時間一般是6~8 h,按啟動鍵、酸奶機開始自動發酵。注意:灌裝要在1 h內完成;發酵時間到,如果沒有凝固,可增加1~2 h 繼續發酵;發酵時間到后開機檢查,看酸奶凝固后取出,直接進入2℃~6℃冷藏箱中冷藏后熟。
(四)酸奶銷售酸奶冷藏8 h后銷售,口味最好。成品酸奶保質期:包裝容器無菌,在冰箱冷藏條件下可存放 7 d。
(五)選擇超市無菌奶制作將牛奶直接溫熱到43℃,投入砂糖、菌種,攪拌均勻后直接分裝。
三、酸奶配方及制作技巧
酸奶配方依據(GB2746-1999酸奶國家標準)執行。
(一)原味酸奶
1.配方。43℃無菌純鮮奶 + 制作總量7%的砂糖 + 適量菌種,攪拌均勻后發酵(菌種根據其說明書選擇添加量)。
2.技巧。發酵時間一般6~8 h左右(如牛奶含抗生素時間還要長)。砂糖可增加發酵速度和甜味,如做無糖酸奶可不加糖。做凝固型酸奶時,時間可直接將奶液分裝到小容器入機發酵(紙盒或塑料盒)。做攪拌型酸奶時,可直接使用盛水的大量杯入機發酵,銷售時將其攪拌均勻,倒入銷售用的容器中即可。
(二)大豆酸奶
1.配方。70%牛奶 +30%豆漿+制作總量7%的砂糖+ 適量菌種,攪拌均勻后進行發酵(根據說明書選擇菌種添加量)。
2.技巧。自制豆漿方法按全自動豆漿機說明書使用即可,要用43℃無菌純牛奶;豆漿要煮熟、煮透;越新鮮越好。
(三)花色酸奶系列原味酸奶銷售時,添加適量的蜜豆、果醬、果仁、果凍或各種水果等即成。
(四)酸奶冰淇凌系列
1.果醬酸奶冰淇凌配方。冰淇凌+酸奶+ 適量果醬。
2.蜜豆酸奶冰淇凌配方。冰淇凌+酸奶+ 適量蜜豆。
3.技巧。手工自制冰淇凌時,用1份硬冰激凌粉+3份純凈水調配攪拌均勻后,放入冰箱冷凍室冷凍。冷凍成固體狀后取出將其切成小方塊繼續存入冰箱冷凍室隨時備用。
(五)奶昔系列
1.配方。原味酸奶 200 ml、冰激凌約 50 g、果醬約 50 g、冰塊適量。
2.技巧。四種材料粉碎20秒即成。(根據個人口味決定是否放砂糖。)
(六)蔬菜、水果沙拉系列各種水果、蔬菜洗凈切好混合后備用。酸奶、白醋、檸檬汁、芥菜、橄欖油、鹽、黑胡椒各適量攪拌均勻,淋入混好的水果、蔬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