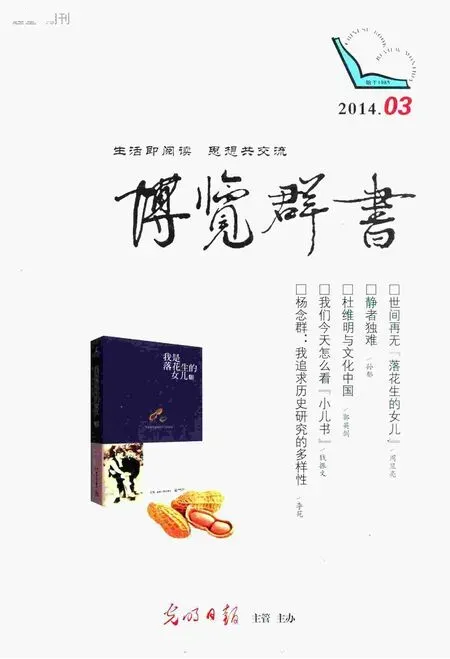他每首詩都是一個小宇宙
劉青海
受道家文藝觀的影響,李商隱的詩歌思想具有尚真、任情的藝術傾向,這體現在藝術風貌上,是其詩歌突出的“緣情”特征。
無題詩對于個人真摯愛情的藝術表現
男女愛慕之情,在《詩經》中已有樸素的表現,并成為后世愛情詩的濫觴。漢末《古詩十九首》“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對感情的描寫真摯動人,但表現的主要是夫婦之間的離別相思,而非男女之間的戀慕。此后曹植繼承楚騷的傳統,以男女之情寄寓才士不遇的懷抱,成為古詩的重要傳統,純粹的愛情描寫在詩歌中更加少見。魏晉以來,隨著文學自覺時代的來臨,詩歌標舉“緣情”,男女之情的描寫成為藝術表現的重要內容。南朝民歌及其文人擬作中大量涌現清新自然的愛情抒寫,以及傳統閨怨、宮怨詩的進一步發展。
中唐以后,愛情成為文學的重要主題,這和當時文人學習民間文學(尤其是傳奇)有關。中唐傳奇中,沈既濟《任氏傳》、李朝威《柳毅傳》、白行簡《李娃傳》、元稹《崔鶯鶯傳》、蔣防《霍小玉傳》等表現男女之情,藝術上比較成熟,吸引文人重新關注古老的愛情題材。白居易《長恨歌》中對帝妃之間上天入地的愛情之描寫,就是這種影響的產物。此外,李賀詩歌中神話和艷情的結合,大約也受到《柳毅傳》的啟發。可以說,對于男女之情的抒寫,已經成為中唐詩歌的一種風氣。而中唐愛情題材的詩,作者多以旁觀者的身份抒情,尚屬于樂府中的代言體。如白居易《長恨歌》、劉禹錫《竹枝詞》等,其詩歌中有關愛情的描寫都缺乏體驗的個人性,就抒情方式而言,仍屬于樂府代言體的范疇。李賀的愛情詩,已經開始向個人化的抒寫過渡,但受樂府的影響太明顯,大量使用神話傳說在一定程度上湮沒了愛情體驗的個人化特征,這使得其愛情詩綺艷有余,深情不足;足以聳動視聽,難以動人肺腑。
真正的愛情詩的個體化抒情應該說是李商隱奠定的。李商隱詩受李賀和六朝樂府的影響很深,集中艷情諸作,明顯受到李賀愛情詩的影響,在意緒的迷離方面甚至比李賀走得更遠,如《燕臺詩四首》《河內詩》,但尚未洗凈長吉體的痕跡,亦非其愛情詩的代表之作。集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愛情詩乃是《無題》諸作:“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正所謂“鏤心刻骨之詞,千秋情語,無出其右”。沒有真摯愛情的真實體驗,詩人是無法傳達出如此濃烈、深沉的相思之情的。這種因受現實阻礙而受盡煎熬的痛苦和備受折磨卻依然無怨無悔的執著交織在一起,給讀者以最強烈的震撼。這樣濃烈而又純粹的情感,除了愛情,更無別樣的情感可以擔當。其愛情詩的成熟之作,已經擺脫了樂府民歌的影響,在藝術表現上汲取了《詩經》和《古詩十九首》興寄無端、空際傳情的表現手法,以真情動人,奠定了中國文人愛情詩的主體風格,成為后世取用不盡的寶藏。李商隱之后,“無題”成為愛情詩的代名詞,在歷代皆有仿作。就某種意義而言,李商隱在愛情詩方面的成就和地位,可以媲美杜甫在七律方面的成就和地位。
就詩歌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李商隱的愛情詩也是對于愛情題材的一種縱向開拓。然而,李商隱的人生尤其是愛情體驗,卻是充滿了令人失意的“間阻之慨”,所以前人的藝術表現與六朝樂府民歌的手法,又遠遠無法滿足其藝術表現的需要。對于李集中大量的無題詩,清人往往傾向于認為是有寄托的,并非純粹的愛情詩。應該承認,其愛情詩中的“間阻之慨”和他在現實生活中不遇的挫折感是相通的,詩中無怨無悔的執著之情,也和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戀闕之情相似。但需要指出的是,李商隱雖然關注現實政治,有強烈的入世情懷,但他既沒有如屈原一樣抱著明確的政治理想,也不具有屈原為理想而不惜身殉的決絕,對時主也不可能像屈原對楚懷王那樣依戀徘徊,終不忍舍。這方面的態度,集中大量的政治詩和詠史詩中都有流露。他對于歷史的認識是客觀、清醒的,晚唐諸帝中他對于文宗和憲宗有好感,但更多的卻是清醒的批評。他和唐王室血緣的疏離以及他一直不遇的現實遭際也使得他不可能像屈原一樣,雖深知君主的昏庸卻仍然有戀闕之情。因此,上引無題諸作中強烈的“間阻之慨”,可以視為通于君臣朋友,但卻不能視為單為君臣朋友而發。事實上,這種阻隔的感受,在愛情中更為普遍。因為戀愛中最常見的體驗就是間隔和誤解,而且愛情會因阻隔而更加強烈。李商隱年幼喪父,“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不幸的遭遇培養出了詩人敏感脆弱又富于深情的氣質,而這樣的人“在處境窘困孤獨凄零的時候”,“急于跳入愛情的火焰中”(培根《論愛情》)。
李商隱詩歌“緣情”特征的三種表現
李商隱尚真、任情的詩歌思想,使其詩歌總體上呈現出“緣情”的特色。對李詩的盡情特征認識較早的是清代詩論家紀昀,其《玉溪生詩說》卷下屢次批評李商隱詩句“太竭情”“竭情太甚”“太激太盡”。顯然,紀昀以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來衡量李詩,認為其詩歌沒有對情感的表現加以必要的約束,有違儒家的“以禮約情”“溫柔敦厚”。因此,我們不妨略舉幾首被紀昀批評為“竭情”的詩歌,這些詩歌正體現出鮮明的“任情”傾向: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沉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愧辭。
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幾移。
(《撰彭陽公志文畢有感》)
出宿金尊掩,從公玉帳新。依依向余照,遠遠隔芳塵。
細草翻驚雁,殘花伴醉人。楊朱不用勸,只是更沾巾。
(《離席》)
春物豈相干,人生只強歡。花猶曾斂夕,酒竟不知寒。
異城東風濕,中華上象寬。此樓堪北望,輕命倚危欄。
(《北樓》)
暫憑樽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
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其一)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