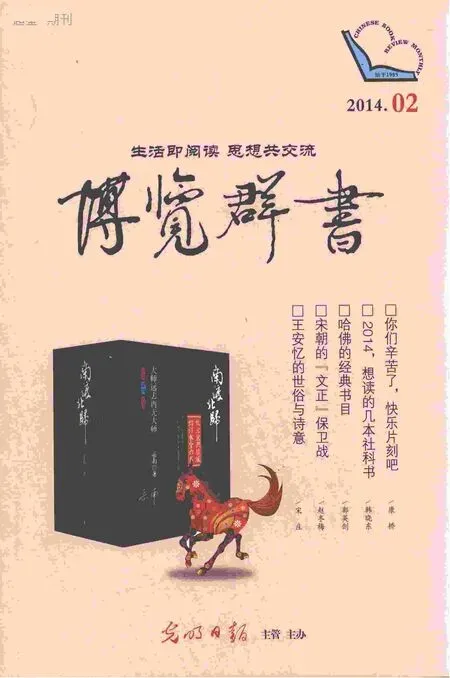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博覽群書”與獨一無二的中國
孫祁祥
從讀書到教書再到寫書,偶爾也評書——我寫過一些書序和書評,我的大半輩子都在與書籍打交道,不敢說“嗜書如命”,但對書絕對是“情有獨鐘”。這不僅僅只是因為深信“腹有詩書氣自華”;更是篤信“讀書使人生更精彩”。
我們這一代人是生長于“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那個年代的。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文革”開始。然而,靠從小給別人織毛活才勉強上過四年學的母親卻告誡我們兄妹:“讀書是有用的。”于是,盡管那個年代沒有多少書可讀;盡管上中學時,工廠實習、下鄉鍛煉、野營拉練、建校勞動、挖防空洞、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占據了我們大部分的時間,但在非常有限的文化課上,我還是非常認真地學習,始終保持著一種閱讀習慣。“文革”之后,我考上了大學,之后又上了研究生、博士生,那個時候,我感覺母親說得真是對的,讀書真的很有用,否則我上不了大學。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閱歷的豐富,我越來越認識到,讀書不應當僅僅只是為了考學、晉級、升遷。讀書的功力之大,大到能讓一個人從愚鈍變為開化,從粗俗變為高雅;大到能讓一個國家從貧窮變為富裕,從羸弱變為強大。
30多年的從教經歷,讓我體會到“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最本質的一個區別在于國民素質的不同,而國民素質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一個國家讀書人群的數量以及閱讀的目的、對知識尊重的程度、對他國優秀文化的吸納和對本國優秀文化傳承的力度來體現。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我最欣賞的讀書畫面是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地鐵上、飛機上乘客們靜靜閱讀的場景;最感到溫暖的讀書畫面是家人、朋友圍座一起,安靜閱讀的場景;最感到震撼的讀書畫面是躺在病榻上,生命即將終結的人平靜閱讀的場景。歷史上曾戰勝法國并俘虜法國皇帝的德國元帥毛奇曾經說過:“普魯士的勝利早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就決定了。”這里且不去評價國家、民族之間戰爭的是與非,僅就文化所能釋放出的能量來看,它是無法計量的軟實力。正因為如此,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才發出過“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也不肯失去一個莎士比亞”的感嘆。
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以經濟和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指揮權是硬實力;而一個國家通過其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所釋放出來的無形影響力,就是文化軟實力。歷史和未來終將證明,國家綜合實力的比拼,最終是體現在文化上的。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之初的3645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18年的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早在2010年,中國就已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中國還不是強國。因為強國的標志不僅僅只是龐大的經濟總量,還必須看這個經濟總量所反映的內容、結構以及人均水平;強國的標志也不僅僅只是經濟指標,還必須包括思想、價值觀、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軟實力”,對外所具有的強大的“吸引力”和“滲透力”。現代社會最顯著的標志之一就是將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超級競爭力、巨額利潤的背后,比拼的是高科技含量,而高科技含量蘊含的是科學素質和人文素養,后者根植于深厚的閱讀、思考習慣和質疑、創新精神。被稱為“日本現代企業之父”、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的澀澤榮一,從干實業的第一天起,就把中國儒家經典《論語》當作自己的行動指南。他號召日本人做“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的企業家。
直面中國的現實,在人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的同時,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的閱讀量總體來說較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前蘇聯作家布羅茨基曾經說過:“一個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再加上一句:“一個讀書少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成為受世人尊重的民族。”
什么時候國人把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作為一種時尚,什么時候讀書不僅僅只是為了考學,為了晉級、為了升遷,而是為了內心的平和,為了思想的深邃,為了精神的富有;什么時候讀書不是為了附庸風雅,而成為國人生活的必須,成為生命的一個部分,那么,中國人的形象就會更好,中國的國民素質就會大大提高,中國的“軟實力”就會得到極大提升,也因為如此,“強國夢”的實現才會更有根基。
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經說過:“真正偉大的民族永遠不屑于在人類當中扮演一個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頭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中國,這個有著5000年博大精深歷史文明的大國,要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需要全體國民努力汲取人類優秀的文明養分,修身養性,提升素質,以文化自信,支撐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亞太風險與保險學會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