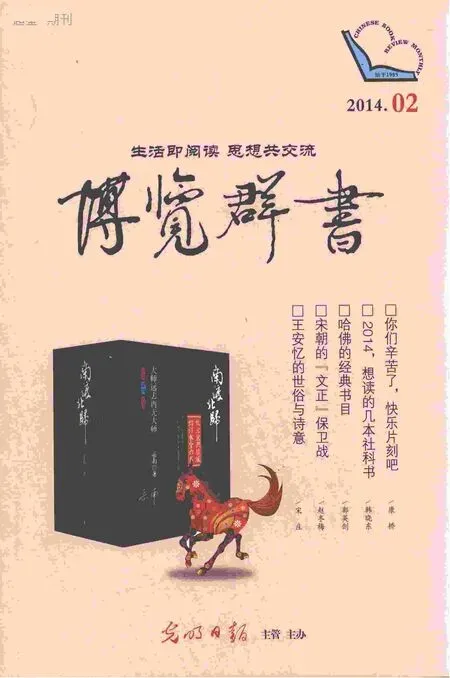清末新軍之所以“新”
周子康

兵圣孫武曾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可見一斑。但一直以來,學界在近代中國軍事史方面的研究,不如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等領域的成果那樣豐富,尤其是對于甲午戰后逐漸建立起來的新軍,并沒有給予太多重視。青年學者彭賀超的《新軍會操——中國近代軍演早期形態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版),是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作為第一本關注新軍會操的專著,該書描繪了會操的演變過程及具體情形,并試圖在宏觀上建構近代中國軍演的發展歷史。
所謂“會操”,其實就是“會合操演”或“會合大操”的簡稱,指某區域的軍隊在圍場或校場進行的狩獵式或陣式訓練,如八旗大閱、木蘭秋狝、綠營演練陣法等。與中國傳統兵學概念的“會操”不同,“新軍會操”則是指甲午戰爭以后,袁世凱、張之洞在編練新軍進程中舉行的實地對抗演習,這是清末軍事轉型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軍事演習是軍隊主要的軍事活動,其目的在于檢驗武器裝備和彈藥的可靠性,為軍官與士兵們提供近似實戰的機會,在改進各項戰術的基礎上,保持部隊的戰斗力和活力。袁世凱在奏折中說:“東西各國,不惜繁費,歲歲舉行者,誠以多一次戰役,必多一次改良,多一次會操,必多一次進步。”舉行會操演習對于軍隊建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晚清內戰中崛起的湘軍和淮軍,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效仿西方的訓練操法,大量使用新式武器。1888年成軍的北洋水師更是裝備精良,一度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論器物,洋務運動中的清軍的確不落下風,但還是因為怠于訓練而難以抵御外敵。清廷龐大的軍事力量漸漸淪為不堪一擊的紙老虎,最終于甲午一役灰飛煙滅。在沉痛的失敗面前,不少官員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袁世凱曾經批評清廷舊式軍隊是“平居而聲息不相通,應調而指臂不相使,臨敵而勝敗不相顧”。顯然,中國軍隊只有在更加現代化的軍制基礎上,注重實地對抗演習,才能真正提高戰斗力。新軍便是在這種新的軍事觀念指導下開始發展起來的。
前人有關研究往往只注重編練新軍中的“編”,即描述其軍事建制、領導機構、財政管理、招募方式、軍官及士兵等。而彭著則挖掘出了“練”的主題,即新軍會操。會操研究不僅是探知清末軍事轉型的一個“窗口”,也可為討論清末新政、社會思潮、朝局形勢等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清末新軍之所以“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實行了現代軍事學意義上的對抗演習。1905年以后,清廷在彰德、河間等地舉辦的幾次大會操,均邀請各省大員和外國武官參與觀操。清廷希望借此樹立練兵典范,以便在全國推廣經驗,同時向國內外展示軍隊新的風貌。書中提到在河間會操后,一位俄國觀操員憂心忡忡地說:“若北洋新軍由一位優秀的軍事統帥領導,那它將會成為一支值得重視的敵軍。”彼時各國觀操員都對中國軍隊 “同聲稱許”。
不同于一般性質的軍事訓練,大會操的參與人數通常在萬人之上,需要中央陸軍部統籌規劃,各省督練公所協助處理,并充分利用鐵路、新式通訊系統、軍事指揮的各種技戰術,調動兵力進行實地對抗演習。這樣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其實是對晚清國家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全面考驗。如果沒有清末新政帶來的社會進步,軍事改革是無法取得如此令人信服的成就的。
此外,新軍以及會操的出色表現也離不開每一位官兵的積極參與和社會的廣泛支持。舉行會操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這背后隱含著愛國主義與尚武精神的相互激蕩。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下,從軍打仗這類事情只被視作粗暴、野蠻之舉。然而在19世紀末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不少人提出中國積弱、軍事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尚武精神,他們主張喚醒民眾,振興武備以抵御列強的入侵。清末民初著名軍事家藍天蔚就非常強調軍隊在近代國家中的重要性,認為軍事力量是維護國家之城墻,民族驕傲之姿態,養育文明之母親。清廷也在廢除科舉與設立新式學堂的同時,增添了軍訓課。對于軍事學堂的畢業生,則一律視為秀才功名。顯然,軍人的社會地位在不斷上升,新軍士兵也比舊式軍隊顯得更富有朝氣和激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滿漢矛盾的激化和朝局的動蕩,新軍會操和軍事轉型的良好勢頭難以持續。袁世凱在河間、彰德會操中出盡風頭,招致滿族親貴的強烈忌憚。陸軍部尚書鐵良與袁世凱不惜反目,迫使他交出北洋數鎮的指揮權。光緒、慈禧離世后,剛剛上臺的攝政王載灃便以足疾為由罷免袁世凱,并大量任用宗室子弟掌控朝政大權,壓制張之洞等漢臣。與此同時,清廷還面臨著嚴重的財政赤字危機。1906年袁世凱曾因拖欠400萬兩軍餉,險些導致他親自統轄的北洋新軍發生兵變。財政狀況更為窘迫的地方新軍更是軍心動搖,頻發騷亂。種種原因導致1908年太湖秋操、1911年永平秋操都未能如期舉行。
“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句軍事學上的著名論斷,移之于史學界,同樣富有啟迪意義。新軍會操這樣大型的軍事演習活動,不可能脫離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而獨立存在,它完全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背后的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問題。然而在過去傳統史觀的敘述下,對于清末新政,尤其是袁世凱及北洋集團在此期間的崛起,總體以負面批評居多。新軍通常被描繪成清廷封建勢力用以鎮壓革命起義的工具,并孕育了后來的“北洋軍閥”。如《北洋軍閥史》一書中寫道:“袁世凱就是利用這一時機,鉆了全國編練新軍的空子,發展了北洋軍閥集團的勢力。”幾次新軍大會操只被視為袁世凱北洋集團爭權奪利的政治行為,而這一軍事活動本身的內容和影響卻無人問津。
事實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國經歷了一場歷時十余年的振興武備的改革運動。清廷試圖依靠軍隊鞏固皇權統治,士紳商民希望軍隊能維護民族利益,編練新軍成為朝野上下共同推動的重要國策。自胡燏棻于天津馬廠編練定武軍始,袁世凱、張之洞等大臣積極倡議并躬身實踐,分別在北方和南方組建武衛右軍與自強軍。新軍完全拋棄了舊軍的勇營制度,以鎮、協、標、營、隊、排的序列構成建制,分為步、馬、炮、工程、輜重五個軍種協同作戰,與世界先進軍制接軌。庚子國難后,清政府數年間組建北洋六鎮,各地也掀起了普練新軍的運動。已有的清末軍事史研究表明,這一時期的中國軍隊在編制、武器、技術、教育、訓練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徹底的改革,中國軍隊第一次得到了來自西方列強的肯定。“從軍事上來說,中國還不能保證使自己不遭受重大的打擊,可是她已經辦到一點,即假如她能夠結成統一戰線,侵略者進攻的代價必將是巨大的,這使任誰也不敢輕于嘗試。”美國著名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專家鮑威爾在其著作中如此評價道。
過去僅僅因為封建的清王朝是革命對象,或袁世凱背叛民國復辟稱帝,以及之后軍閥紛爭的局面,就對清末的一系列軍事改革和新軍的組建全盤否定,這種偏見其實不利于我們形成正確的歷史認識。羅志田教授曾撰文批評近代史研究中的“倒放電影”傾向:“中外過去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有意無意中多受19世紀末以來趨新大勢的影響,基本只給新派一邊以發言權,而很少予舊派以申述的機會,使舊派基本處于程度不同的‘失語(voiceless)狀態。” 新軍這一群體便很快在后世的評價中淪為“舊派”,籠罩在軍閥政治的惡名之下。
所以筆者認為,在清末新政十年改革期間,盡管中國依然受到列強勢力的嚴重威脅,但畢竟還是經歷了一段較為安定的時期,不似19世紀中后期那樣經常身處內憂外患的困境之中,這至少可以證明新軍的產生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即使清廷在1911年亡于辛亥革命,可那是由于其他眾多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并不意味著軍事改革的完全失敗。
(作者系上海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