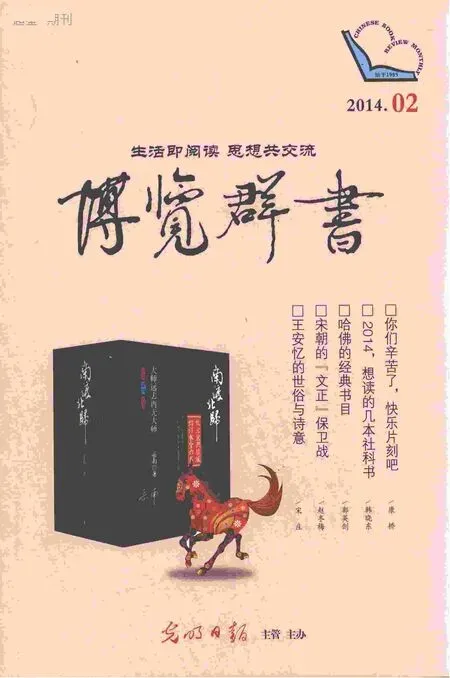民國京劇史料如“井噴”一般
傅謹
京劇自晚清年間成熟,迅速進入鼎盛時期,并且在不到半個世紀的短短時間里就風靡全國,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戲曲劇種。近兩個世紀以來,京劇在中國社會文化領域擁有特殊地位,對它的繁榮發展助力不小,福兮禍兮,不能一概而論,整體而言,對京劇的傳播助力不小,但更重要的是京劇伶人們對藝術的精心雕琢與執著追求,才成就了京劇輝煌的成就與地位。
盡管京劇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與藝術領域有毋庸置疑的地位與影響,但京劇研究的水平與京劇的藝術成就并不相稱。
京劇一直被主流學術界所漠視,當然是最直接的原因。在古典戲曲研究領域,學者們始終關注精英文人的經典化寫作,包括京劇在內的民間形態的戲曲劇種,一直被忽視甚至遭受歧視;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在努力建構俗文學的文化與學術地位時,很快就背離了當初的理念,除了古代白話小說僥幸得到較多的注意,近代以來形成的京劇和各地方戲曲劇種及各地豐富多彩的曲藝這些比小說更典型、更具實際上的民間性的俗文學形態,又不幸地成為文化史的“失蹤者”。京劇和其他地方性的戲曲、曲藝(實際上也包括民間音樂等),在學術上處于古典與現代兩大學術領域之間人為造成的真空地帶,始終難于充分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

戲曲研究從20世紀初開始向現代學術形態轉型,在晚近這一個世紀現代形態的戲曲研究進程中,京劇研究與京劇的發展傳播相比嚴重滯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關的研究資料一直缺乏系統的搜集整理。如果從劇本的層面看,相比中國古典戲劇有《元曲選》《六十種曲》等經典選本,京劇界不乏20世紀50年代整理出版的《京劇叢刊》《京劇匯編》等大型叢書;但是如果從與學術研究關系更密切的文獻資料的層面看,古代戲曲領域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等眾所周知的大規模文獻集成,京劇領域的狀況恐怕就不能不用“寒酸”二字加以形容。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京劇界的學者們基本上只有張次溪的《燕都梨園史料匯編》正續編和其他一些零散的文獻類書籍可用,相對于體量宏大、內涵復雜的京劇研究而言,這些資料當然太有限了。
2004年,中國戲曲學院開始有意識地推進京劇學的研究,既是因為意識到上述兩大問題的存在,亦是為了尋找跨越這些學術難關的道路。或許我們并不能在短期內改變主流學術界的關注焦點,要讓學界對京劇產生興趣,不僅需要京劇本身的繁榮,同時更需要有一大批能得到學界充分認可的研究成果,藉此吸引從事文學藝術研究的學者們的注意力,但所有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充分占有研究資料,又是相當數量且優秀的研究成果之誕生的前提,所以要推進京劇學研究,資料短缺的問題就顯得尤其突出。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們從一開始就把京劇研究資料的搜集、整理作為京劇學最為核心的基礎性工程,陸續編撰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獻書籍。
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初,《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及續編問世,其后又編撰出版了八卷本的《梅蘭芳全集》,現在我們推出的則是《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其實在啟動“匯編”編撰時,我最初的計劃并非如此。我原以為可以將晚清民國期間與京劇相關的文獻一網打盡,然而在實際的資料搜集與編撰過程中,才發現這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暴露了我當年對京劇文獻整體狀況的無知。知恥而后勇,我們改而計劃先出版“匯編”的清代卷,在最初完成并出版“清代卷”的十卷本的同時,又發現了部分清代文獻,因此交替著就開始繼續從事清代卷“續編”的編撰工作,因此“匯編”清代卷2011年出版,兩年后的2013年清代卷的“續編”四卷本就出版了,這就是近年來從事京劇研究的同行們經常使用的這十四卷“匯編”。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匯編”民國卷的編撰出版拖延了這么多年。雖然在“匯編”清代卷出版之前,民國卷的編撰就已經有啟動的打算,但是這一部分的編撰計劃又歷經了多次的斟酌與反復,才最終呈現為現在的樣子。
無須做對照,讀者都會注意到“匯編”的這套民國卷與清代卷的體例的差異非常明顯,我們僅僅搜錄了與京劇有關的專書。民國年間的京劇史料如井噴般增長,所以這部“匯編”的民國卷,其實已經不可能如清代卷那樣分為專書、報刊資料、日記等,清代卷里的無論哪一類,搜集整理出來都是皇皇巨著。我們之所以最終決定只限于選擇各種專書構成這部民國卷,坦率地說,當然有它們具有相對的完整性,較易著手的原因。其實,最初的內容設計是包括該時期的報刊文獻的,十多年前我們就為此做了大量的基礎準備工作,最后之所以艱難地決定舍棄,一是由于民國年間海量的京劇報刊文獻的整理工作,實在繁重到我們的團隊無力承擔的地步,另外,近年來各地報刊數據庫的開發卓有成效,大部分的報刊文章都很容易通過電子文獻檢索到,搜集整理的迫切性,反而不如書籍。與之相對,民國期間的書籍之不易保存是圖書界的共識,查詢借閱之不易,一直困擾著學界同仁,就從本書所收錄的100多種專書看,就有相當部分是各地圖書館中的珍貴藏書,其中也不乏海外收藏的孤本,搜求之艱辛,實不足為外人道,假如這些文獻能為學者們所用,其生命就有了當代延續。
現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終于完成并出版,這套書共15卷,包含了我們搜集、整理的民國年間有關京劇的100多部專書。這些著作的體量大小不一,作者身份殊異,內容涵蓋了京劇伶人的生平藝事,京劇代表劇目的歸納與介紹,京劇的歷史發展軌跡的描述和理論性的總結,特別難得的是數部有關京劇音樂方面的著作,還不免包括一些趣聞秩事。這些都是從事京劇研究的基礎材料,我們并不加經主觀的挑選,相信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取向,自然會擇其所需。希望這些書籍能在一定程度上為研究者打開京劇文獻和京劇研究的更多窗口。
當然,我們并沒有全部收入所有可搜集到的書籍,尤其是因齊如山、周明泰、王芷章等著名京劇學者的相關書籍,近年來早就在各家出版社先后正式出版過,有的還不止一兩個新版本,研究者們尋訪不難,就沒有重復出版的必要,所以我們只收入了新近發現的少數幾部著作,其他均列入存目;此外還有一些最近幾年較易找到的書籍,如徐慕云的《故都宮闈梨園秘史》《梨園影事》等,亦做同樣處理。同時還需要說明,還有相當多我們所知的和未知的京劇類的書籍未能收錄到本書里,相信在民國期間的38年時間段里,京劇相關的書籍肯定遠遠不止于這十五卷,另外還會有不少仍然塵封在公私書庫內,期待著我們再去發現。至于極少數已知的文獻未收收錄,多半出于一些很特殊的原因,其中也包括技術上的困難。就在現有的書籍里亦有類似的現象,因為在重新排版的過程中需要從原來的豎版改為橫排,原書一些包含多種標注的曲譜,很難重新處理,雖然已經盡了許多努力,實在不能按現在的書籍印行方法準確重現的,無奈也只有割舍。民國期間的京劇圖書多為輕松的大眾讀物,其中往往有很多精彩的插圖,既有名伶影像也有演出劇照,這些珍貴的視覺資料,往往包含了比文字更豐富更直觀的信息。無奈其中相當部分,即使從原書直接翻版,質量也未必能得到保證,至于經過復印后,更顯得漫漶不清,直接用在書里,恐怕會妨礙整體印刷效果,所以我們只選了很少一部分清晰的圖片,其中又主要是彩圖,放在各卷前面。
最后還要對處理這些京劇文獻的基本理念做一點簡要的說明。正如我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的“前言”里所說過的那樣,京劇特殊的文化身份決定了與之相關的文獻的特殊性,因此對該類文獻需要有與之實際狀況相符的整理處理原則。雖然按出版物的一般三分之一,在各種古籍整理和資料書籍中人名地名等專用名詞必須統一,但是對京劇和其他具有類似的民間文化性質的文獻而言,強行要求專用名詞的統一,必然會有損于文獻的原貌,并且有可能衍生出新的錯誤。就以最為簡單的人名、劇名為例,在各類京劇文獻里往往有很多同名異寫的現象,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同一人、同一劇、同樣的戲曲劇種或音樂聲腔都可能有不同寫法。如“王瑤卿”早年常寫成“王瑤青”,就很難武斷地判斷正誤;如“筱喜祿”有時寫成“小喜祿”,原本是以“小”為其藝名,改為“筱”是為了使之更似姓氏,并沒有什么對錯之分;如“程繼仙”后來改名為“程繼先”、“程艷秋”后來改名為“程硯秋”,假如在文獻里也都統一為后來的名字,研究者就無法了解他們曾經改名的歷史。如京劇聲腔中最常見的“二黃”和“二簧”,且不說兩種寫法涉及京劇源流的不同解釋,即使從“灘簧”和“攤簧”“灘黃”和“攤黃”,一種聲腔有四種寫法,甚至往往出現在同一篇文章里,更不止是正誤那么簡單;如《戰成都》在多數場合都被寫成《戰城都》,盡管這是明顯的錯字,但是假如按照我們認為正確的方法將“城都”校正為“成都”,地名的錯誤是得到糾正了,但是文獻的原貌卻就此被遮蔽了,今人如果想查詢與《戰成都》相關的史料,就會漏失大部分與該劇相關的演出信息。還有許多戲劇人物的姓名,不僅在不同劇種的同一題材劇目里有異名,在同一劇種里寫法也未必都相同。無論是歷史還是傳說中的人物,都很難或不宜貿然統一,傳說中的人物姓名原本無所謂對錯,即使是歷史名人,就算都改對了,也不免會盡失文獻原貌。這些同名異寫的現象,體現了典型的民間口傳文學重字音輕字形的特征,重在讀音無誤,對字形并不太講究。在處理此類文獻時,我們似應該尊重他們的書寫方法,不便輕易改動原文。在我看來,遇到類似現象時,忠實于文獻本身是更值得遵守的原則,它比起茫然無據地勘誤更有價值,也更有利于研究者的使用。另外,在處理相關文獻時,究竟是以影印的方式呈現文獻的原貌還是重新加以整理標點,是我們一直糾結的,影印當然比較省心省力,而且還能確保不出或少出錯誤,但我們之所以始終堅持對這些文獻做標點校對重新排版,甚至不惜承擔難免會有錯漏的風險,是由于在我看來,讓有志于從事京劇研究的學者們有方便使用的文獻集成,原本就是我組織編撰本書最重要的動機,排印的書籍比起影印的書籍利用率要高很多,這是很直觀的現實,兩相權衡,還是確定不改初衷,如清代卷及續編一樣,不憚勞心費力,希望這樣的苦心得到使用者的理解。
《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正式出版,我的京劇文獻整理工作計劃終于可告完成,但是我們所完成的這些工作,在京劇領域的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方面,只不過是個開端。未來相信還有更多后進學者繼續開拓,有更多更重要的發現,而京劇研究的蓬勃發展,正要寄望于這樣的不懈努力。
(作者系文學博士,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戲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廈門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