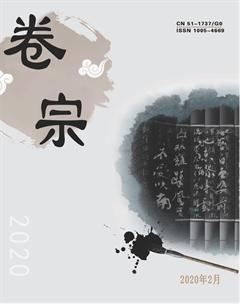科舉制度廢除前后書法教育的異同比較



摘 要:科舉制度是古代首創(chuàng)的朝廷選拔人才的制度,雛形始于隋朝大業(yè)元年,成型于唐朝,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舉行最后一科進(jìn)士考試為止,科舉制度一共經(jīng)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作為古代帝王選賢與能的重要途徑,科舉考試的選拔過程是至關(guān)重要的,而書法又是科舉考察的關(guān)鍵,因此,書法教育受到歷朝歷代的重視和約束。到1905年9月2日為止,清朝廷頒布詔令,科舉制度被廢除,加上西方學(xué)制傳入中國、鋼筆的普及等種種因素,書法逐漸擺脫了制度的影響和約束后,走向了藝術(shù)的探索之路。
關(guān)鍵詞:科舉制度;廢除;書法教育;實(shí)用性;藝術(shù)性
1 科舉制度廢除之前的書法教育
科舉制度的成型與完善都在唐代,唐代科舉考試,書法為法定考科,是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重要指標(biāo),也就是我們所講的“以書取仕”。唐代杜佑《通典》中說:“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奇,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利,文理優(yōu)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jì)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名列上中書、門下,聽制敕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1]也就是說士子文人若想獲取官職,不管是要考取進(jìn)士還是要通過吏部復(fù)試,書法都是一個(gè)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且唐代統(tǒng)治者崇尚“法度”,并提倡遵循法度,這一點(diǎn)也反映在了對于書法教育的要求上。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修弘文館對當(dāng)時(shí)朝中地位頗高的官員進(jìn)行書法培訓(xùn),授課教師都是當(dāng)時(shí)的書法大家歐陽詢、虞世南等人,最初的官辦書法培訓(xùn)機(jī)構(gòu)形成。貞觀二年(628年),又在國子監(jiān)中設(shè)立書學(xué)為專門培養(yǎng)書法人才的學(xué)校,國子監(jiān)學(xué)生“學(xué)書,日報(bào)一幅,凡書學(xué)石經(jīng)三體。”“太學(xué),四門,律學(xué),書學(xué),算學(xué)皆如國子之法,其習(xí)經(jīng)有暇者命習(xí)隸書,并《國語》、《說文》、《字
林》、《三倉》、《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xí)業(yè)……”[2]可見當(dāng)時(shí)的課程安排多以注重學(xué)生的書寫基礎(chǔ)為主,在教學(xué)內(nèi)容上遵循著由簡到難循序漸進(jìn)的過程,以標(biāo)準(zhǔn)經(jīng)文的字體為學(xué)習(xí)藍(lán)本,熟悉造字原理、字的本義等文字學(xué)方面的內(nèi)容后再進(jìn)一步擴(kuò)大文字學(xué)方面的知識(shí)。中央對書法教育的倡導(dǎo)極大促進(jìn)了全社會(huì)學(xué)習(xí)書法的風(fēng)氣,除中央學(xué)校外,地方的都督府學(xué)、州學(xué)、縣學(xué)、私塾,也都紛紛開設(shè)了專門的書法課程。除此之外,唐代時(shí)普及書法程度最高的還是要數(shù)官宦人家設(shè)辦的家庭式的私學(xué)和私塾教育。第一種是家族式的傳承教育,這種方式有效地保障了書法的延續(xù)和積累,像永興公虞世南有“子篡,孫煥,皆能繼也”;“薛稷也受益于其舅,魏叔瑜……尤邃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唐篆書之冠的李陽冰,“兄弟五人皆負(fù)詞學(xué),工于小篆”[3]等,皆是家族式傳承教育的例子,但有幸于生于官宦翰墨世家的人筆跡還在少數(shù),且私塾式教育面對面授課,不僅可以進(jìn)行語言講解還可進(jìn)行書寫的示范,因此私塾式的由老師教授書法的方式更貼近平民更為普及,也給唐代書法帶來了更廣闊的發(fā)展基礎(chǔ)。
在書法教育的內(nèi)容上,因?yàn)榭婆e制度以“楷法遒美” 為評判標(biāo)準(zhǔn),蒙童教育起就以能《千字文》為主要書寫教材,如此一來,唐代產(chǎn)生了一批名垂青史的楷書大家,唐朝建立起的楷法的“法度”從此也被歷朝歷代所用,這不僅是藝術(shù)的自律性進(jìn)入到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產(chǎn)物,也是制度之下國家的規(guī)范與提倡以及科舉制度對書寫規(guī)范的要求所產(chǎn)生的必然結(jié)果。
到了宋朝時(shí)期,科舉制度建立了完善的糊名和謄錄制,“以書取仕”的要求弱化,但科舉制度仍然存在。“院體”在宮廷中悄然成型,“院體”指的是翰林院中流行一種由臨習(xí)《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而逐漸形成的在宮廷內(nèi)風(fēng)格比較一致的書法風(fēng)格。若要追溯其源流,可追溯到唐太宗時(shí)期。李世民喜好王羲之書法,翰林、侍詔便紛紛效仿,成為翰林院的通用字體,故稱為“院體”。這種書法形式一直延續(xù)到了南宋末年,宋高宗依舊偏愛王羲之書法,故翰林院依舊流行院體書風(fēng),這與北宋時(shí)期為了博得當(dāng)世主文者的青睞竭力模仿其書體,形成的“趨時(shí)貴書”并無本質(zhì)上的不同。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書法教育規(guī)模空前擴(kuò)大,沿用唐代家學(xué)、私學(xué)等教育模式,但在書法教育上還增加了理論方面的課程,有了藝術(shù)教育的功能。宋代對書法理論的重視對宋代書風(fēng)產(chǎn)生了影響,教學(xué)方法也被后世所運(yùn)用。
到元朝,科舉考試進(jìn)入中落時(shí)期,元朝滅亡后,明王朝建立。不同于唐、宋時(shí)期的科舉制,明朝科舉制其目的是通過科舉嚴(yán)厲控制士人思想,考試范圍改為了四書、五經(jīng),沒有了時(shí)務(wù)和歷史。考試文體也變?yōu)榘斯晌模偌由铣讨炖韺W(xué)的盛行,更是給當(dāng)時(shí)的文人志士套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鎖。“藝術(shù)被專一用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真正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精神則被遏制。……文學(xué)上的臺(tái)閣體應(yīng)運(yùn)而生,此時(shí)的書壇亦然受到這種風(fēng)氣的影響。”[4]書法從此成為內(nèi)秀外柔人格的權(quán)利化工具,書法教育也因此遵循制度的要求,教習(xí)“臺(tái)閣體”以便于將來在考試選拔中受到青睞,以至于“至永樂朝,臺(tái)閣體書法盛行于朝野。”[5]科舉制發(fā)展到明朝,已然逐漸暴露了它的弊端,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也因此受到極大禁錮和束縛。
明代那種工整勻稱、平正圓的“臺(tái)閣體”,到了清代便成了勻圓規(guī)矩的“館閣體”,同樣都是要求考卷的字寫得烏黑、方正、光潔、大小一樣。統(tǒng)治者的書法審美主張直接性的決定了世人學(xué)子學(xué)書的取向,成為世人學(xué)子能否考取功名的關(guān)鍵。
“館閣體”的風(fēng)行與清朝帝王崇尚程朱理學(xué)密切相關(guān),清朝時(shí)的科舉制度承襲明制度,以程朱理學(xué)為考試的標(biāo)準(zhǔn),朱熹的書學(xué)主張更是受到了清代帝王的推崇。關(guān)于朱熹的書學(xué)主張,他在《晦庵論書》中跋《朱喻二公法帖》提到:“書學(xué)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于黃、米,而欹傾側(cè)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6]由此可見,朱熹的書學(xué)主張便是他理學(xué)主張的延伸,他不認(rèn)同宋代書家那種狂放的表達(dá)自我情感的書寫方式,提倡書家書寫時(shí)應(yīng)心態(tài)恭敬,書寫法度嚴(yán)謹(jǐn)如唐人那般。他的這種理念與當(dāng)時(shí)統(tǒng)治者的治國理念不謀而合,“從程朱理學(xué)的視角看書法,要求書法以『敬』為尚,講求端楷,認(rèn)為書法是文人修行德行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寫字不是技能,不是藝術(shù),而是修身方式,這是端楷的政治意義所在”[7]在這樣封建制度的統(tǒng)治之下,文人志士若想被看重、考取一世功名施展自己的宏圖抱負(fù),就不得不順從于體制、屈服于體制。因此“讀書應(yīng)試不僅是入仕的正途,在以農(nóng)業(yè)為本,生產(chǎn)不發(fā)達(dá)的社會(huì)中,讀書、應(yīng)試、入仕且是仕子的唯一本業(yè)。”[8]所以,孩童教育便是最有效的從根源以書治國的方式。因此,清朝廷把民間書院納入官學(xué)管理范圍以此監(jiān)管,從此以中央國子監(jiān)為首,其他官學(xué)、 地方府學(xué)、州學(xué)、縣學(xué)書院皆以朱熹的書學(xué)思想為標(biāo)桿培養(yǎng)人才。《欽定國子監(jiān)則例》書體課程條載:“凡內(nèi)外班肄業(yè)生學(xué)習(xí)書體每日數(shù)百字,皆令臨摹晉唐名帖,助教等隨時(shí)指示,毋得潦草錯(cuò)落及倩人代書”,“凡內(nèi)外班肄業(yè)生讀書習(xí)字,自立課冊,逐條登記每十日送助教等查閱,至朔望由博士呈堂。”[9]作為教育體系中的最高學(xué)府國子監(jiān)頒布條例后,由朱熹理學(xué)主導(dǎo)的書學(xué)思想便由上至下推廣至全國了。清代地方《教育志》記載:“我朝功令,凡殿試、朝考,尤重楷法。鼎甲館選,咸出其中,而可茍乎哉?先儒云‘作字端楷,亦主敬之一事。”[10]以及由朱熹的弟子程端蒙和董銖制定的《學(xué)則》為藍(lán)本修訂的《城東二先生學(xué)則》第十二條要求:“寫字必楷敬:勿草,勿傾欹。”[11]由此可見,在清朝中央集權(quán)制不斷加強(qiáng)的大背景之下,這樣規(guī)范、嚴(yán)謹(jǐn)?shù)囊蟾袷且环N統(tǒng)治者教化的方式,借助書法這一載體展示自己威嚴(yán)不可撼動(dòng)的統(tǒng)治地位,從此“館閣體”已然成為書法教育下通用的實(shí)用性書體。
乾隆以后,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和不斷衰弱,“乾嘉學(xué)派”、碑學(xué)興起使得本就孱弱不堪的帖學(xué)走向了窮途末路,明初時(shí)期溫婉柔美,典雅含蓄的書風(fēng)發(fā)展,館閣體以此為濫觴,漸漸走向平庸和刻板。科舉制度所引發(fā)的自上至下的學(xué)書浪潮嚴(yán)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一些很有才華的藝術(shù)家在書法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才能得不到應(yīng)有的發(fā)揮,約束了書法朝個(gè)性、自然方向的發(fā)展。像清代著名的思想家龔自珍,自嘉慶二十四年他先后參加了五次會(huì)試皆落榜,其原因皆是因?yàn)槠淇ú患选V恋拦饩拍辏?829年)龔自珍第六次參加會(huì)試,終于考中進(jìn)士。在殿試對策中仿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yuǎn)疏》,論新疆評定準(zhǔn)格爾叛亂后的善后治理事宜,從各個(gè)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shí)事,灑灑千余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卒于楷法不中程,不列優(yōu)等”[12]當(dāng)時(shí)主持殿試的大曹振鏞將龔自珍置于后三甲,不得入翰林,僅任內(nèi)閣中書,由此便可見得書法優(yōu)劣對世人學(xué)子的前程具有多大的影響。
館閣體烏、方、光的特點(diǎn)使得當(dāng)時(shí)的書法千篇一律,枯澀無味(見圖一、圖二),但另一方面看,清朝的館閣體在清代極大的發(fā)揮出了他的實(shí)用價(jià)值,并且對當(dāng)時(shí)書法的基礎(chǔ)教學(xué)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作用,他的流變從側(cè)面也反映出了帖學(xué)的審美變化。
到了19世紀(jì)80年代后,隨著西學(xué)東漸的影響和洋務(wù)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科舉制度正悄無聲息地發(fā)生著改變。1898年6月戊戌變法開始,應(yīng)康有為等建議,廢八股文,以時(shí)務(wù)策命題,嚴(yán)禁憑楷法優(yōu)劣定高下。在《請廢八股試貼楷法試士改用策論》中康有為曰“其楷法方、光、烏之尚,尤為費(fèi)時(shí)……今當(dāng)多難之秋,不必敝精于無用,應(yīng)請定制,并罷試帖,戒嚴(yán)考官,誤尚楷法。”[13]這一提議旨在要掃除長久以來“館閣體”造成的書法萬人書如一人書的刻板化現(xiàn)象,也為碑學(xué)的發(fā)展掃除障礙。然而戊戌變法只維持了百天便失敗了,但戊戌變法的進(jìn)步意義是史無前例的,它為科舉制度廢除后的書法變革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思想基礎(chǔ)。
2 科舉制度廢除之后的書法教育
2.1 新式學(xué)堂的興起和書法教育的改革
1903年,清朝廷頒布《奏定學(xué)堂章程》,此時(shí),科舉考試已改八股為策論,但尚未廢除。因科舉為利祿所在,人們趨之若騖,學(xué)堂式學(xué)校難以發(fā)展,因此1905年9月2日清廷詔準(zhǔn)袁世凱、張之洞所奏,立停科舉,將育人、取才合于學(xué)校一途。并令學(xué)務(wù)大臣迅速頒發(fā)各種教科書,責(zé)成各督撫實(shí)力通籌,嚴(yán)飭府廳州縣趕緊于鄉(xiāng)城各處遍設(shè)蒙小學(xué)堂。至此,在中國歷史上延續(xù)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廢除,學(xué)堂教育興起,科舉取士與學(xué)校教育實(shí)現(xiàn)了徹底分離。“更可貴的是,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李瑞清在兩江優(yōu)級師范學(xué)堂開設(shè)圖畫手工科(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藝術(shù)系),把書法正式列入藝術(shù)教育范圍,由他本人親自執(zhí)教。以此開端,后來的師范學(xué)堂,及不斷涌現(xiàn)的藝術(shù)專科學(xué)校紛紛效仿。”[14]可見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書法逐漸擺脫了制度上的束縛,除了使用性質(zhì)之外,書法逐漸顯露出了他的藝術(shù)性,并成為與繪畫、雕塑等一樣相對獨(dú)立的藝術(shù)學(xué)科。
根據(jù)1903年清朝廷頒布《奏定學(xué)堂章程》的課表(圖三、圖四)與1912年之后教育部訂定學(xué)校課程表相比較來看(圖五、圖六),1903年的朝廷對于書法教育的內(nèi)容已然與戊戌變法前的舊制不同,不再只局限于楷書、小楷這等“館閣體”書法,教授行書并將動(dòng)靜虛實(shí)等變化列入幼童需理解范圍。而且從當(dāng)時(shí)出版的學(xué)堂用的字帖來看,除了傳統(tǒng)的歐體、柳體、顏體等楷書字帖外,還有各類魏碑、隸書、篆書字帖,并且像趙之謙、李瑞清、曾熙等新派書家的字帖在學(xué)生中也受到廣泛歡迎。1913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課程標(biāo)準(zhǔn)中更是將草書列入習(xí)字范圍。但由于1912年2月才剛結(jié)束了清王朝六百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仍受到清朝書學(xué)遺風(fēng),國家依舊提倡主流書風(fēng)為書法教學(xué)的首要:“教育部公布師范學(xué)校規(guī)程第十二條中寫道,習(xí)字要旨在練習(xí)書寫、具端正敏捷之能力,并解悟高等小學(xué)校及國民學(xué)校習(xí)字教授法。習(xí)字宜授以端正字勢及執(zhí)筆運(yùn)筆之法。”[15]要求寫字端正且習(xí)字課多注重楷書,打好書寫基礎(chǔ)。但能看出當(dāng)時(shí)在教學(xué)內(nèi)容和題材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反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思維,且1913年頒布的《壬子癸丑學(xué)制》確立了女子具有同男子一樣的受教育權(quán)利,女子學(xué)堂陸續(xù)創(chuàng)辦,書法的受眾面更廣了,女書法家在科舉制度廢除后也陸續(xù)登上了歷史的舞臺(tái),為書壇注入新鮮的血液。
2.2 書寫工具的革新
20世紀(jì)初,鋼筆被引進(jìn)中國,由于鋼筆相較于毛筆而言有簡單易上手使用方便的特點(diǎn),在20世紀(jì)20年代開始逐漸受到普及。鋼筆使用便利易攜帶等獨(dú)特優(yōu)勢使得它悄然無聲便占領(lǐng)了書寫實(shí)用的領(lǐng)地,書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排擠”。在書法在喪失了自我的實(shí)用價(jià)值的這樣一個(gè)被冷落被排擠的環(huán)境之下,被迫進(jìn)入了一個(gè)需要“自我反省”、“洗禮”、“重生”的過程之中。“首先是立足于書法作為藝術(shù)的觀念立場,對過去實(shí)用加欣賞的混合機(jī)制進(jìn)行認(rèn)真的清理,強(qiáng)化它作為視覺藝術(shù)的應(yīng)有特征而淡化它原有的作為實(shí)用工具的歷史特征。”[16]在經(jīng)過這樣觀念上的“洗禮”后我們便發(fā)現(xiàn),被迫趕下實(shí)用的“神壇”表面看是書法之不幸,但實(shí)則卻是書法藝術(shù)之大幸!
在硬筆快速發(fā)展之下,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教育部訓(xùn)令各省教育廳轉(zhuǎn)飭各校注意習(xí)字:“吾國文字歷代相傳,由來已久,在中國文化上實(shí)具有高尚藝術(shù)之價(jià)值,而文字之勢力,不特流布最廣,且能旁及諸國而同化之,其功用之偉大,有如此者,而今日一般青年,往往求一時(shí)之便利,率多廢棄毛筆,習(xí)用鋼鉛,殊不知中國之筆,易于中國之紙,相互為用,而善兼收,……特此通令各廳,轉(zhuǎn)飭各屬各級學(xué)校,嗣后小學(xué)應(yīng)遵照學(xué)校課程標(biāo)準(zhǔn),注重習(xí)字,小學(xué)畢業(yè)以能寫正楷及通俗行楷為主,初中高中注重楷書及行書,均以毛筆書寫為主……”[17]可見毛筆并沒有因硬筆的發(fā)展而就此沒落,反而因和實(shí)用的捆綁減弱,觀賞性逐漸增強(qiáng),且當(dāng)時(shí)受西學(xué)影響的知識(shí)分子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等人一致認(rèn)為書法應(yīng)是一門獨(dú)立的藝術(shù)。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宗教”更是呼吁“增設(shè)書法專科”作為美育內(nèi)容之一。由此看來,硬筆的發(fā)展推動(dòng)了書法作為一門獨(dú)立的藝術(shù)的進(jìn)程。
3 總結(jié)
科舉制度作為古代選拔政治人才的體制,一千多年以來為歷朝歷代輸送了無數(shù)的能人志士,世人學(xué)子皆以此作為進(jìn)階的途徑,激發(fā)出了科舉制度極大的社會(huì)感召力和號召力。在科舉制度的庇佑之下,書法得以受到全社會(huì)的的關(guān)注,營造出了更便于書法藝術(shù)發(fā)展的環(huán)境,書法教育也因此蓬勃興起。從隋唐起,因科舉制度帶動(dòng)的書法教育發(fā)展一直延續(xù)著,至今都保有余溫。但發(fā)展至明清時(shí),因王權(quán)的集中而催生出的千篇一律的臺(tái)閣體、館閣體極大的約束了書法的自然化、藝術(shù)化的進(jìn)程,書法藝術(shù)逐漸走向了庸俗與羸弱的境遇,但我們也不得不成認(rèn),唐代的“楷法遒美”、宋代的“院體”、明代的“臺(tái)閣體”和清朝的“館閣體”對實(shí)用性書寫的意義。正因科舉制度對書寫的統(tǒng)一要求,才使得書法教育有法可依、有范本可學(xué),這對書法推廣和增強(qiáng)書寫基礎(chǔ)能力公布不可沒,在書法文化的發(fā)展上有著宏觀的積極意義。
然而事物的發(fā)展是充滿規(guī)律的、有利有弊,當(dāng)弊大于利時(shí)被消滅和代替是事物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因此,科舉制度的廢除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科舉的廢除,為碑學(xué)掃清了障礙,碑學(xué)得以受到更多學(xué)子的延續(xù),吳昌碩、李瑞清、楊守敬等近代偉大的碑學(xué)書法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靈魂在晚年得以熠熠生輝,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從此就不必在限于帖學(xué)一脈,書法教育者和學(xué)習(xí)者也不必再拘泥于科舉制度的要求,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審美取向決定自己的學(xué)習(xí)方向,書法的發(fā)展走向也更傾向于創(chuàng)新和注重個(gè)性。而且科舉制度的廢除也終結(jié)了古代落后的教育制度,新興學(xué)堂的建立和體制的革新使得人人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西學(xué)東漸思想的融入和書寫工具的革新,使得書法能夠單純作為一門獨(dú)立的觀具有賞性藝術(shù)走進(jìn)大眾的生活并被接受。
在科舉制廢除100多年后的今天,有幸的是書法的美不必再局限于方寸之間,我們得以追求自我本心所求;不幸的是,隨著科技文化的發(fā)展,書法藝術(shù)的群眾基礎(chǔ)卻變小了,對書法藝術(shù)的傳承和傳播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因此完善書法教育體系、擴(kuò)大書法藝術(shù)的受眾群體乃是我輩之責(zé)任。
參考文獻(xiàn)
[1]杜佑,《通典·選舉三·歷代制下》卷十五,上,顏品忠等校點(diǎn),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第185頁.
[2]謝世湖,唐代書法教育[J].廣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0年,第一版.
[3]張彥遠(yuǎn),法書要錄[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4年 第286.
[4][5]黃墩,《中國書法史 元明卷》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9年174頁175頁.
[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商務(wù)印書館,一九八六年,(集部)第1145冊,第701頁.
[7]陳佳,清代書法教育的審美定位[J].中國書法,2017年第8期30頁.
[8]王德昭 《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版 第66頁.
[9]《欽定國子監(jiān)則例(第三冊)》,文海出版社,2003年,第793頁.
[10]《皇清書史》,《遼海叢書》,遼沈出版社,一九八五 年,第一四〇九、一四一〇、一四六〇頁.
[1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商務(wù)印書館,一九八六年,(子部)第709冊,第461頁.
[12]龔自珍《龔自珍全集·定盦先生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18頁.
[13]翦伯贊編《戊戌變法》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頁.
[14]侯開嘉《中國書法史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4頁.
[15]舒新成《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年第705頁.
[16]《民國書法史論》陳振濂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7年 第4頁.
[17]舒新成《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年第1205頁.
作者簡介
王婧熠(1995-),女,漢族,山東淄博,研究生在讀,四川大學(xué),研究方向:美術(shù)學(xué)書法方向。
——原始社會(huì)藝術(shù)性與實(shí)用性的完美結(ji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