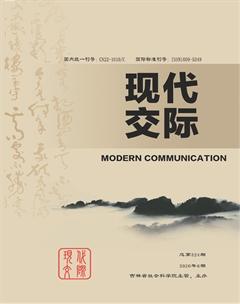口述傳記《我的前半生》著作權糾紛案淺析
摘要:《我的前半生》著作權糾紛案發生于1984年,從起訴到終審判決歷經十年,被稱為“天字第一號”著作權糾紛案。通過資料查閱還原了案件經過和結果,梳理了案件合作作品與否和作品體裁定性兩個案件分歧點,并分析了李文達工作認證和案件特殊性,同時就口述傳記執筆者的特別身份和如何避免著作權糾紛等問題進行延伸思考。
關鍵詞:著作權 合作作品 名人自傳 口述傳記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6-0052-02
《我的前半生》最初是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在東北撫順戰亂管理所服役期間,由本人口述、其弟溥杰代筆的一份自傳體悔罪材料(又稱“灰皮書”)。1960年后,中央指示公安部對其修改整理,公安部將任務委派給群眾出版社。經過共同商議,決定由群眾出版社的李文達協助溥儀完成傳記。1960年4月至5月,溥儀口述,李文達執筆記錄,整理出16章24萬字修改稿,期間李文達還曾遠赴東北收集史料。1964年3月,以愛新覺羅·溥儀署名的《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
爭端起源于1984年中意合拍的電影《末代皇帝》。意方提出需有《我的前半生》著作權享有者的同意并授權才能簽約。此時溥儀已經逝世,由遺孀李淑賢繼承著作權,由于報酬分配問題,李淑賢拒絕授權。隨后李文達以作者身份與意方簽訂合約,李淑賢得知后將其告上法庭。
一、案件結果
(一)各方意見
對于此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國家版權局、全國人大法工委均認為《我的前半生》為合作作品,著作權為溥儀和李文達共有;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認同《我的前半生》為合作作品,但認為著作權為溥儀和國家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我的前半生》著作權為溥儀獨有,死亡后由李淑賢繼承,但李文達享有適當的經濟報酬。
(二)判決結果
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溥儀是《我的前半生》一書的作者,并享有該書的著作權。李文達在該書的成書過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是與溥儀之間不存在共同創作該書的合作關系。因為李文達并非直接侵權,所以駁回李淑賢要求李文達賠禮道歉的訴訟。李淑賢服從一審判決,但李文達的法定繼承人不服從一審判決,再次上訴。1996年6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李文達方的上訴,保持原判。
二、案件分析
(一)雙方分歧
1.是否為合作作品
合作作品有兩個判定條件。第一,合作作者具有共同創作某一作品的合意,即將自己的創作成果合并為一個整體的“意圖”。第二,合作作者具有共同創作的行為。
溥儀的創作地位顯然是無可置疑的,作為傳記的主人公和主要敘事者,他提供了大部分的素材。而李文達在撰寫過程中也不是一個機械的記錄者,他做了包括收集資料、構思、校改等工作,還進行了許多主觀能動性創作,因此第二個判定條件成立。問題在于第一個條件,兩人是以合作為意向進行創作的嗎?1960年灰皮書完成的時候,群眾出版社接收到的指示是“協助”溥儀修改材料使之能夠最終出版,因此傳達給李文達的也是“協助修改”任務,而非“參與創作”。無論是群眾出版社還是溥儀本人,都未提出由兩人合作創作《我的前半生》。在書稿完成后,溥儀曾寫下“四載精勤如一日,揮毫助我書完成”的條幅贈給李文達,也說明了李文達與溥儀之間是協助關系而非合作關系,因此著作權不能由雙方共享。
2.文學性傳記還是一般自傳
這個問題看似與本案關系不大,實則決定了李文達的主觀性創作對作品是主要構成還是輔助作用。文學性傳記與自傳的區別在于敘述人稱,文學性傳記是由他人對傳主的人生故事進行文學性呈現,作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空間大;而自傳的傳主和作者則是同一人。當時各方意見出現分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是文學性傳記,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是自傳體文學作品。在本案的特殊情況中,雖然存在李文達第二方的參與,但是筆者認為《我的前半生》仍然是自傳體作品。原因在于,其以第一人稱的自傳體形式敘述了溥儀的前半生經歷,體現的是溥儀的個人意志。李文達盡管有主觀性創作,但均要符合溥儀本人意愿,發揮空間不大。
(二)李文達的工作認證
李文達雖沒有該書的著作權,但作為執筆者,仍然享有特定的經濟權利和精神權利。在《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后,首版稿酬11700余元,群眾出版社按照社內一般寫稿人員稿酬的50%支付李文達,這一比例已經是給付非主要撰寫者稿酬的最大比例,這正是出于對李文達付出大量精力的考慮。
而在精神權利方面,溥儀和中央對李文達的工作肯定也是一種精神獎勵。溥儀除了送給李文達橫幅外,還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李文達對他完成此書的巨大幫助,認證李文達的勞動付出。
(三)本案的特殊性
案件的審理前后歷經10年,驚動了三級法院,可見案件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首先是作品形式的特殊性。口述自傳的作品形式存在兩方參與者著作權的歸屬問題。這一點前文已經說明,故不再贅述。
其次是傳主身份和傳記內容的特殊性。溥儀作為中國的末代皇帝,為政治性質的社會名人;《我的前半生》反映的是溥儀在新中國時期接受思想改造并轉向黨與人民的過程,具有特別的政治意義且社會影響重大,不適宜為傳主之外的人署名。與之相對應的,該書產生的輿論評價也由溥儀一人承擔。
最后是社會影響的特殊性。社會名人的傳記創作也多由他人執筆,如果《我的前半生》著作權糾紛案判決結果改變了本書的著作權歸屬,可能引起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
三、延伸思考
(一)為了避免出現法律問題,口述傳記合作者應該提前先以書面形式確定著作權歸屬
本案的審判困難除了在于作品本身,還在于當事人雙方一開始沒有做好書面約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合作以特定人物經歷為題材完成的自傳體作品,當事人對著作權權屬有約定的,依約定;沒有約定的,著作權由該特定人物享有,執筆人或整理人對作品完成付出勞動的,著作權人可以向其支付適當的報酬。”可見,某些情況下,口述傳記的著作權可以由傳主和參與寫作人員共有,但應該有書面約定。當訴訟發生時,當事人溥儀已經去世,再做書面約定已經無從談起,其遺孀李淑賢也無法代表本人意志,因此給本案的定奪帶來很多爭議。相關出版人員都應該提高自身著作權意識,將著作權歸屬問題用書面形式確定,以免給日后造成麻煩。
(二)執筆者放棄精神權利的同時也避免承擔傳記帶來的社會輿論影響
傳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作品,體現的是特定個人的人生軌跡和意志,傳主作為獨立個體向社會輸出個人價值。傳主獨享著作權更有利于社會對傳記的認識和接受,更清楚地意識到傳記中的“我”是傳主本人。執筆者沒有著作權初看令人為之不平,但傳主獨有著作權也意味著由其獨自承擔傳記帶來的社會輿論影響,未署名的執筆者避免被波及。當然,口述傳記的執筆者扮演的是類似于幕后英雄的角色,可能放棄精神權利的情況也考驗執筆者的奉獻精神和職業責任感。
《我的前半生》著作權糾紛案作為中國著作權史上著名的大案,交織著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等元素,體現著對理性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平衡。名人口述傳記的特殊性使得著作權歸屬仍存在爭議,除了需要當事雙方的合法約定外,還要更為完善細致的法律加以規范。
參考文獻:
[1]王慶祥.《我的前半生》:溥儀、李文達著作權糾紛案揭秘[J].現代交際,2007(3):11-13.
[2]葉海濤.文學性傳記合作作品著作權之認定[J].知識產權,2003(2).
[3]李明德,許超.著作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7-128.
[4]熊晶晶.關于自傳體作品著作權的歸屬[EB/OL].(2014-12-04).http://www.fabang.com/a/20141204/688335.html.
責任編輯:孫瑤
[作者簡介]陳昕彤,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編輯出版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