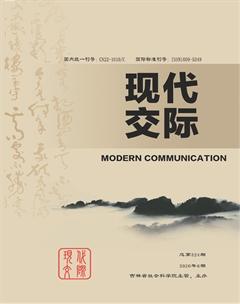生態公民的時代內涵及其培育研究
摘要:生態文明建設是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生態公民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具有豐富的時代內涵。當前我國生態公民培育存在著生態環境意識淡薄、法律意識薄弱、生態道德滑坡、生態科技知識水平滯后等問題,不利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工作的開展。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必須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為手段、全社會廣泛參與的生態公民培育中國路徑。
關鍵詞:生態公民 時代內涵 培育
中圖分類號:D621.5 X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6-0225-02
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正式納入“五位一體”建設總體布局,并在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十九大報告中也有對生態文明的重要表述:“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進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更加強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培育生態公民不僅是學理上的探討,更是對實踐發展需要的積極回應。
一、生態公民的時代內涵
為有效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國外學者開始將目光轉向關注人在解決生態問題中的作用,提出了“生態公民”的概念。生態公民理論在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了不同流派,各流派對生態公民的內涵有不同闡釋,但其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追求人類統一行動,解決生態危機。[1]在生態文明建設視域中,生態公民的含義可以理解為依法對生態環境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并參與具體生態環境事務的人。[2]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生態公民與其呈現出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具有更加豐富的時代內涵。
1.生態公民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實踐主體
生態公民對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具有自覺能動性,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實踐主體。生態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政府決策的制定和執行,尤其是環境相關政策,增加了公共政策的科學性,實現了社會與生態發展的平衡。生態公民追求利用自然為人類謀利的同時,以合理的方式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促進生態經濟的生產。生態公民能夠以人的基本需求為標準,倡導綠色生活方式,主張購買對人和自然環境無害、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產品,以生態文明的消費方式促進文明生態的形成。[3]
2.生態公民是行使生態環境權利的主體
有研究者認為,生態公民是具有環境人權意識的公民,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環境人權包括能夠獲得滿足基本需要的環境權、免于遭受環境傷害、擁有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4]為了改善生態環境,我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并不斷完善政策體系,推動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立。生態公民是行使生態環境權利的主體,具有保護生態環境的強大內生動力,能充分認識國家環境政策與公民權益的一致性,把政策法規作為個人的自主選擇,減少執行過程中的阻力,確保政策法規效力得到有效發揮。
3.生態公民是生態美德的道德主體
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法律、制度等硬約束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道德對公民的日常行為約束。當前我國生態環境的法律制度體系仍在不斷完善,因此發揮生態公民的道德主體作用就尤為重要。生態良知、生態人格、生態智慧等基本元素構成的生態美德,充分體現了生態公民的道德主體作用,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力量。
二、生態公民培育面臨的問題
我國生態公民的研究明顯晚于西方,生態公民培育尚處于起步階段,社會公眾在生態環境意識、道德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培育程度仍然偏低,是我國生態公民培育面臨的主要問題。
1.生態環境意識淡薄
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淡薄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已成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制約因素。我國公眾生態環境意識淡薄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方面:對環境保護關注度高,實際參與度低;注重環境私利,對生態公益關注度較低;注重負面環境問題的解決,忽視可持續發展等正向環境議題的開展;對環境保護態度明確,相關知識卻不足;對環境保護有較高期望,對自身的環保實踐重視不足。
2.生態法律意識薄弱
公眾的生態法律意識薄弱主要表現為:對我國的生態環境法律和政策了解不深,相關法律知識缺乏;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法律權益的意識不強,當環境權利受到侵害時,不能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自覺維護法律要求的意識不強,部分公民存在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不能自覺維護法律規定。
3.生態道德出現滑坡
現階段,我國公民生態道德滑坡主要是由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視資本的利用和發展,形成了唯我論的價值體系,而我國傳統道德體系總的“天人合一”“和諧”等價值觀被削弱。因此,環境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依靠法律政策等剛性制度約束,還需要培育公民的生態道德,樹立環境價值觀,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惡化的趨勢。
4.生態科技知識水平滯后
我國公民的生態科技知識水平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與生態公民的要求相比仍然滯后。對生態科技的研究多針對某單一問題,缺乏跨學科、跨地域的系統性研究;生態科技研發主體單一,社會和公眾參與不足;解決群眾普遍關注的環境問題方面,科技創新不足。
三、生態公民培育路徑
培育生態公民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也需要全社會公民、團體等的廣泛參與,通過一系列的社會實踐活動培育和發展生態公民。我國的國情和現實條件決定了必須構建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手段、社會廣泛參與的生態公民培育中國路徑。
1.政府主導,建立生態公民培育和服務體系平臺
政府對于社會發展承擔著設計、推進的主要責任,因此在生態公民的培育中必然要起主導作用。政府在生態公民培育過程中要做好全方位服務工作,為生態公民培育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一是廣泛開展調研,制定有較強針對性、高效實用的政府服務方案;二是建立便民、便利的生態公民培育服務體系,推動政府服務資源向下轉移;三是科學規劃,整合優化資源,建立區域性生態公民培育服務平臺。
2.優化市場配置,以經濟手段促進生態公民養成
目前,我國所實行的資源定價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費。培育生態公民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以經濟手段促進生態公民養成。一是完善資源定價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以經濟手段促進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有效刺激生態公民培育[5];二是建立排污權交易市場,實行總量控制和排污收費制度,激發市場主體減少污染排放和革新污染處理技術,為生態公民培育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
3.加強教育,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生態實踐
生態公民不是自發產生、自覺養成的,需要政府和社會采取多種措施,強化生態公民教育,培養公眾生態環境意識,鼓勵公民參與生態實踐。一是采取國民教育、社區活動、社會宣傳等多種教育形式,強化公民生態環境意識[6];二是完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保障公民的環境知情權,為公眾參與生態實踐奠定基礎;三是創新工作形式,豐富群眾參與生態環境保護渠道,鼓勵公民參與生態實踐。
參考文獻:
[1]曾晨.生態公民本土化養成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學,2018.
[2]黃愛寶.生態型政府構建與生態公民養成的互動方式[J].南京社會科學,2007(5):80.
[3]徐梓淇.論生態公民及其培育[D].上海:復旦大學,2013.
[4]楊通進.生態公民的培養是戰略任務[J].綠葉,2009(1):90.
[5]王中華,張學芳,劉明源,等.生態文明視野下生態公民養成機制研究[J].科技視界,2017(19):35-36.
[6]李娜.生態公民的意蘊及其養成路徑探析[J].理論導刊,2014(10):89-91+112.
責任編輯:楊國棟
[基金項目]2019年山東省黨校(行政學院)系統課題研究項目“生態文明視野下生態公民的內涵及其培育研究”(2019SH015)。
[作者簡介]張芬,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