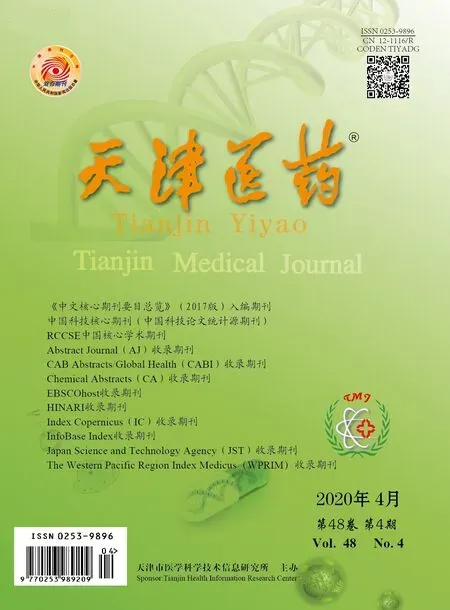甲型流感合并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膿毒癥一例
王麗靖,王曉敏
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與其他細菌共感染是造成甲型流感高致病性與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別是在老年人及兒童等易感人群中尤為突出[1-2]。對于臨床醫生高度懷疑的流感樣病例,可早期應用神經氨酸酶抑制劑治療,而不必等待病原學結果,在考慮與細菌共感染時,經驗性選擇抗菌藥物應覆蓋最常見的病原菌,如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鏈球菌等,方可使患者最大程度獲益。為提高臨床醫師對兒童重癥流感合并細菌感染的認識,以利于早期識別和提高救治成功率,現將我院收治的1例危重癥流感并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感染病例資料報告如下。
1 病例報告
患兒 女,8歲,因發熱伴精神差1 d,于2019年1月28日入我院。患兒于入院前3 d曾與高熱患者(患兒母親)密切接觸后出現發熱,體溫最高39.1℃,自訴全身無力,伴憋氣,精神及進食差,無其他伴隨癥狀。住院當天上述癥狀加重,伴口周發紺,經皮測血氧飽和度(SpO2)0.79~0.82,予大流量吸氧后可上升至0.85~0.89,收入兒童重癥監護病房(PICU)。患兒既往體健。患兒母親經對癥治療已好轉。入院時查體:體溫37.2℃,脈搏151次/min,呼吸46次/min,血壓(BP)95/60 mmHg(1 mmHg=0.133 kPa),吸氧下SpO20.85~0.88,吸入氧(FiO2)體積分數0.30。發育正常,營養好。急性病容,神志清,精神差。呼吸促,口周發紺,三凹征(+),手足暖,脈搏有力,毛細血管再充盈時間2 s。全身皮膚未見皮疹、黃染及出血點。雙肺可聞及濕性啰音,心音有力,律齊,腹軟不脹,肝脾未觸及,四肢活動自如。神經系統查體未見異常。入院當時相關實驗室檢查如下,血氣分析:酸堿度(pH)7.42,二氧化碳分壓[p(CO2)]35 mmHg,氧分壓[p(O2)]47 mmHg,全血堿剩余(BEb)-0.1 mmol/L。生化檢查:血鈉124 mmol/L,鉀3.8 mmol/L,氯89 mmol/L,尿素氮(BUN)16.7 mmol/L,肌酐(Cr)108μmol/L,乳酸脫氫酶(LDH)538 U/L,肌紅蛋白345.5 μg/L,肌鈣蛋白T 0.03μg/L,肌酸激酶(CK)2 169 U/L,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27 U/L,轉氨酶正常。痰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甲型流感病毒抗原檢測陽性,其他病原(EB病毒、支原體、腺病毒、副流感等)檢查未見異常。血白細胞介素6(IL-6)>5 000 ng/L,監測血常規、C反應蛋白(CRP)、降鈣素原(PCT)變化,見表1。住院當時留取血培養2次、痰培養2次及住院11 d胸水培養2次,均提示存在MRSA感染,藥敏結果見表2。

Tab.1 Blood routine,CRP and PCT changes during hospitalization表1 住院期間血常規、CRP、PCT變化

Tab.2 Culture results of blood,pleural effusion,sputum and drug sensitivity表2 血、胸水、痰培養及藥敏結果
影像學檢查:住院當天胸CT示雙肺散在斑片狀及結節狀密度增高影,胸膜增厚,氣管及左主支氣管壁欠光滑,見圖1 A~C。住院2、4、6 d胸X線片示雙肺炎性實變,右肺為著,其動態變化見圖2 A~C。住院11 d復查胸CT示右肺及左肺下葉炎性實變較前擴大,右肺及左肺上葉多發空腔影,左側胸膜增厚,右側胸腔積液,見圖1 D~F。住院20 d復查胸CT顯示雙肺炎性實變較前吸收,雙肺空腔影部分吸收,右側胸腔積液吸收好轉,見圖1 G~I。住院10 d復查胸腔B超示右側胸腔積液,最大液深2.8 cm,右側肺實變,先后2次進行胸腔穿刺抽液。住院14 d復查胸腔B超示右側胸腔積液,內見多量分隔及絮狀低回聲,最大液深1.6 cm,右側肺實變。心電圖示竇性心律,ST-T改變。住院1 d超聲心動圖示左室收縮功能減低,左室射血分數0.49,短軸縮短率0.24,心腔大小正常,次日復查超聲心動圖顯示好轉。
診療經過及病情轉歸:入院診斷重癥肺炎、呼吸衰竭。患者在大流量吸氧下SpO2在0.85左右,血氣分析示低氧血癥,伴有明顯的呼吸困難,住院1 h予無創呼吸機持續氣道正壓通氣(CPAP),初始參數FiO20.60,呼氣末正壓(PEEP)6 cmH2O(1 cmH2O=0.098 kPa)。結合患兒可疑流感接觸史,在冬季流感高發季節發病,迅速出現肺部彌漫性病變,低氧血癥明顯,高度可疑重癥甲型流感,故入院時即予奧司他韋口服抗病毒治療。患兒血常規示粒細胞缺乏、血小板進行性下降,CRP、PCT異常增高,胸CT示雙肺散在斑片狀及結節狀密度增高影,考慮合并細菌感染可能性較大,故予頭孢曲松及利奈唑胺靜脈滴注聯合抗感染治療。住院2 h患兒出現上消化道出血,對癥治療1 d后好轉。住院12 h昏迷,格拉斯哥(Glasgow)昏迷評分5分。住院20 h患者出現休克,BP 50/30 mmHg,尿量減少,超聲心動圖示左室收縮功能減低,心電圖可見室性早搏,心肌酶CK、CK-MB明顯增高,考慮心肌受累合并心功能衰竭,故予多巴酚丁胺強心治療,控制入量,呋塞米減輕心臟負荷,并營養心肌等治療。入院34 h患者循環穩定,尿量增加,復查超聲心動圖示心臟收縮功能逐漸恢復。住院2 d,停口服奧司他韋,予帕拉米韋靜脈滴注。住院第4天,患者神志轉清,同時血培養回報MRSA,依據藥敏結果停用頭孢曲松,繼續利奈唑胺抗感染。住院8 d,血小板恢復正常。住院10 d患者呼吸衰竭糾正,期間呼吸機參數最高設置FiO20.70,PEEP 10 cmH2O。住院11 d患者仍有發熱,復查胸部CT示病變范圍進展伴右側胸腔積液,見圖1D~F。予胸腔穿刺抽液,先后共2次,總量約500 mL。住院15 d患者體溫正常,復查CRP、PCT明顯下降。住院20 d復查肺CT顯示好轉,見圖1G~I。住院5、6、7 d各復查1次血培養均轉陰,住院12 d復查胸水培養轉陰。出院診斷:(1)甲型流感(危重癥);(2)膿毒癥(MRSA);(3)肺炎、膿胸;(4)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5)電解質紊亂。共住院23 d,病情好轉出院。隨診1個月,患兒無不適癥狀,復查肺CT基本正常。
2 討論
2.1 危重癥流感病例早期識別 本例患者臨床特點:(1)冬季流感高發季節發病,發病前有可疑流感接觸史。(2)以持續高熱、乏力、精神差等典型癥狀起病。(3)進展迅速,早期即出現呼吸衰竭,且以Ⅰ型呼吸衰竭為特點。(4)肺CT早期顯示磨玻璃浸潤影。(5)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抗原檢測陽性。(6)無菌體液(血、胸水)培養示MRSA陽性。(7)病情進展急驟,早期即出現MODS。故此患兒可確診甲型流感(危重癥)合并MRSA感染致膿毒癥。兒童是流感的高發人群以及重癥病例的高危人群,依據2018年版流感診療方案[3],本例患兒出現呼吸衰竭及MODS符合危重癥流感病例診斷標準。臨床醫生在流感高發季節應對重癥及危重癥做到早期識別,才能有效降低病死率。

Fig.1 The chest CT changes of the patient in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treatment圖1 治療過程中不同階段胸部CT變化

Fig.2 Changes in the chest X-ray during the treatment圖2 治療過程中胸X線變化
2.2 甲型流感病毒與MRSA共感染的機制 本患兒近期無住院及用藥史,入院時血液和胸水培養出相同菌株MRSA,符合社區獲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community acquired-MRSA,CAMRSA)[4]。甲型流感病毒與細菌共感染后致死率高于細菌單獨感染[5],同樣也是造成甲型流感高致病性與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合并的常見菌屬為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鏈球菌及其他鏈球菌屬細菌[6]。2009—2010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美國一項針對兒童的回顧性研究提示,PICU收治的838例確診為甲型流感H1N1亞型的患者中,21.8%存在明確細菌感染的病原學依據,其中金黃色葡萄球菌占39%,71例(8.4%)在入住PICU 72 h內合并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其中MRSA比例為48%);在既往健康的兒童中,早期合并MRSA肺炎是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7]。2014年美國一項多中心重癥監護病房(ICU)的重癥流感患者的回顧性資料顯示,在507例患者中114例(22.5%)合并細菌感染,47例(9.3%)分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是合并細菌感染的最常見病原[8]。甲型流感病毒與金黃色葡萄球菌共感染的可能機制為:(1)流感病毒侵襲呼吸道上皮細胞后,暴露細胞外分子結構和基底膜,與P-V殺白細胞素(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PVL)的金黃色葡萄球菌黏附,促使金黃色葡萄球菌過度繁殖。而CA-MRSA產生的重要外毒素是PVL,其可以導致白細胞破壞和組織壞死,與壞死性肺炎的發生有關[9]。(2)部分金黃色葡萄球菌分泌的蛋白酶可活化血凝素(hemagglutinin,HA),增強流感病毒的感染性和致病性[10]。(3)流感病毒通過STAT1信號轉導通路誘導了Ⅰ型干擾素的過度表達,抑制了17型免疫反應(包括IL-17和IL-22)介導的宿主防御功能,使其對MRSA 易感[11]。
2.3 CA-MRSA肺炎合并流感的臨床特點 CAMRSA在社區感染中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感染者多以平素身體健康的青少年為主[12]。本例患兒入院時血常規示粒細胞缺乏、血小板迅速降低,同時CRP、PCT異常增高,胸X線片示多肺葉浸潤伴有結節樣影像,均符合金黃色葡萄球菌等革蘭陽性球菌感染的特點,與PVL的破壞作用可能相關。該患兒同時具備流感和MRSA膿毒癥的臨床特點和證據,2種致病原互相協同、促進,導致病情更加危重、進展急驟,早期即出現MODS。MRSA易播散性的特點常引起壞死性肺炎,重者可危及生命[13]。與欒巍等[14]報道的16例CA-MRSA肺炎的臨床特點相似,其中8例有流感樣癥狀。結合本例患者,筆者認為當甲型流感病人合并細菌感染時,依據以上臨床特點應高度懷疑MRSA感染。
本例患兒自發病24 h內應用奧司他韋,自發病48 h確診甲型流感。對臨床醫生高度懷疑的流感樣病例,可早期應用神經氨酸酶抑制劑治療,而不必等待病原學結果,這可使患者最大程度獲益。若考慮合并細菌感染時,經驗性選擇抗菌藥物應覆蓋最常見的病原菌,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鏈球菌等。在聯合治療48 h后患兒體溫即呈下降趨勢,5 d后3次復查血培養轉陰,PCT及CRP顯著下降,臨床癥狀緩解較快,治療效果明顯。我們體會此患兒救治成功的關鍵是早期識別了流感,并認識到可能同時存在革蘭陽性球菌的混合感染,從而給予了及時、正確的針對性治療,這對于危重癥病例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