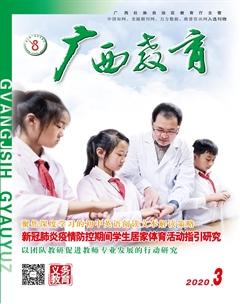廣西原創兒童繪本的困境與突圍
【摘要】本文基于廣西原創兒童繪本在探索道路上存在誤區及困境,論述以廣西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為例,突破廣西原創兒童繪本的困境策略,通過了解孩子的年齡特征、閱讀特點和閱讀興趣,立足兒童本位,有效發揮繪本在早期教育和促進兒童發展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兒童繪本 民間故事 神話傳說 廣西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20)03A-0011-03
在新時代創新需求背景下,我國原創兒童繪本市場開始立足民族傳統文化,探索兒童繪本的尋根之旅。廣西絢麗多彩又獨具特色的壯鄉文化,如富有壯族典型民族特色的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是本土兒童繪本創作的豐富的素材來源。以下,筆者試基于兒童本位,探索廣西原創兒童繪本的困境與突圍策略。
一、廣西民間故事與神話傳說兒童繪本發展概況
20世紀90年代,接力出版社曾以劉三姐的民間傳說、桂林山水傳說故事為基礎創作繪本和動漫作品,探索打開圖書市場的新型運作方式,成果有《百鳥羽衣》《斗米灘與望夫石》等繪本作品。到2004年,廣西藝術學院成立繪本工作室,開啟了繪本創作的新征程,如學院研究生師生創作項目——桂林山水傳說故事系列繪本創作研究,以桂林市陽朔縣流傳的民間故事為創作素材,運用中西方繪畫藝術的透視方法與繪畫媒材,借鑒廣西壯族民族文化元素與色彩特點,創作一系列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繪本作品,如《蓮花池》《雞籠嶺》等。
近兩年,廣西原創繪本創作呈活躍之勢。2018年,南寧市博物館與廣西霖創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聯合創作發行了以廣西壯族神話傳說為主題的少兒繪本《倫歌朝觀》系列共三冊,在社會廣受好評。2019年,廣西民族出版社聯合廣西民間工藝剪紙大師鐘昀睿,出版了《黑龍洞——桂娃故事之花山巖畫傳說》,再有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壯族神話傳說少兒繪本系列》,入選2019年“原動力”中國原創動漫出版扶持計劃等。以上皆是兒童繪本與廣西壯族文化相融合的有效嘗試和成果。
二、廣西民間故事與神話傳說兒童繪本現狀分析
廣西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融入兒童繪本創作成效突出,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下面,筆者以《倫歌朝觀》系列繪本和《黑龍洞——桂娃故事之花山巖畫傳說》繪本為例,分析廣西原創兒童繪本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困境。
(一)文化宣教大于童心
我們在創作一些廣西民族主題繪本時,對于傳播傳統文化的理解存在思維局限性,導致過度的文化宣教替代了關注兒童本身,讓尋找傳統變成照搬傳統,傳播文化變成了傳播知識。繪本《黑龍洞——桂娃故事之花山巖畫傳說》,作品通過創作“桂娃”主人公的經歷,為讀者展現了很多壯族文化元素,如吹牛角、拋繡球、敲銅鼓等,但作為作品主題的花山巖畫故事,卻只在最后幾頁草草交代,缺乏吸引力。繪本中大量壯族文化元素的呈現看似讓作品變得很豐富,實則讓這些傳統元素在反復羅列中失去文化的厚度,不僅容易造成讀者產生審美疲勞,還削弱了繪本的故事性表達,而作品本身更像是一部民俗風情繪本,“花山巖畫故事繪本”的意味次之。兒童繪本的讀者對象是3—6歲的兒童,他們對于繪本的理解是簡單而感性的,繪本內容如果只是一味地進行知識羅列和灌輸,只會讓孩子失去閱讀的興趣,我們要想通過繪本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也只能是空談。
(二)文本故事缺乏吸引力
對于兒童閱讀繪本,兒童因其有趣而讀,廣西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為文本創作的兒童繪本,其中大多進行了一定的文學加工,卻容易忽略了趣味性表達。如《倫歌朝觀》系列繪本,每一冊安排講述3至4個壯族神話故事。每個故事因為受篇幅所限,包括插圖在內僅占用10—15頁的篇幅,要在如此局促的篇幅內呈現一個精彩的神話故事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編者用平鋪直敘的方法將一個個故事“講”出來,如第一冊《布洛陀造天地》的故事在描寫布洛陀開辟天地時,僅將故事描寫為“布洛陀把鐵木豎起,用力一頂,天和地就這樣分開了”,情節描述趨于平淡,三言兩語的敘述恐怕很難給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圖片淪為文字的附庸
一本好的繪本其圖片能夠講故事,因此繪本應當是“圖×文”的關系。以廣西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創作的繪本,因文是現有的,繪者多以文配圖,缺乏對故事情節的延伸,不利于拓展孩子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倫歌朝觀》系列繪本中的圖畫參考廣西少數民族服飾中大量的傳統紋樣,極具幾何裝飾效果,但由于與文本穿插排版,略顯裝飾有余、形象難辨識,要令兒童通過讀圖明曉繪本創作之意,存在一定難度。
三、廣西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兒童繪本的創作建議
兒童繪本的目標受眾是廣大少年兒童。以廣西民間故事 和神話傳說為藍本創作兒童繪本,其首要前提是堅持兒童本位,站在兒童的角度用孩子們的眼光和心靈去創作繪本故事。
(一)尊重兒童,保持創作的“童心”
日本繪本大師松居直說:“圖畫書對幼兒沒有任何‘用途,不是拿來學習東西的,而是用來感受快樂的。”兒童天性愛玩,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創作者在進行廣西壯族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繪本創作時,應該充分尊重孩子,保有一份可貴的“童心”。
兒童繪本要保有“童心”,關鍵是創作者在觀念上要“去功能化”。換句話說,就是讓繪本從“有用”變為“無用”。繪本作為幼兒早期教育的重要書籍,同時也是傳播民族傳統文化的有效載體,是對孩子進行民族文化教育,促進兒童形成民族認同感的橋梁紐帶。從這個層面上看,繪本是“有用”的,但應避免功利化,把表象的民族元素進行羅列,去“教”給孩子,而且應該是潛移默化的,通過輕松的或是有趣的方式進行講述,也就是“無用”化的過程。如熊亮的繪本《年》,講述的是中國遠古民間神話傳說“年”的故事。文中也有放鞭炮、掛燈籠、穿新衣等常規過年的習俗,但并不贅述,僅一語帶過。接著故事進行一個趣味性的轉折:“……誰也不愿意這樣!現在,讓我們重新來過。”這樣的話語,模仿了孩子們游戲時的耍賴心思,最后故事筆鋒一轉,將戰勝“年”的辦法升華為“和”的主題,讓故事的結尾更為意味深遠。這本繪本抓住了“童心”,通過輕松趣味的方式(無用化),讓兒童理解“年”的由來(有用),同時又明白“和”的意義,給予孩子更深層次的思維啟迪。
(二)讀懂兒童,以恰當的方式講故事
3—6歲學齡前兒童的認知規律具有直觀、具體和形象等特點,他們的學習需要是建立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再構建新的認識。因此,以廣西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進行繪本創作,應與兒童的認知規律和審美情趣相結合,才能創編出適合兒童閱讀的好作品。具體做法如下。
1.注重繪本文本語言的文學性與趣味性表達
繪本語言結合了3—6歲兒童的認知特點,簡單、直接、精煉和有趣是其創作特質,讓兒童在聽繪本或是讀繪本時,都能感受到語音的節奏美與韻律美。熊亮的繪本《年》語言多用短句,且富有趣味性,如一句“他住在高高的山上,從來沒有人和他玩”,孩子可以毫不費力地理解“年”這個形象:它是一只住在高高的山上孤獨的小怪獸。周翔的《一園青菜成了精》文本編自北方童謠,趣味之余又朗朗上口,配上肆意瀟灑的中國畫蔬菜形象,讓孩子讀來哈哈大笑。
2.注重聯系現代兒童的生活經驗
3—6歲的兒童對脫離其實際生活經驗的事物和圖式理解起來有一定困難,同時壯族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多以久遠的年代為背景,故事中的人和事物跟現代生活都有很大的差別,如何才能讓兒童真正理解并接受呢?那就要以壯族傳統的“舊”背景,創作符合現代兒童生活經驗的“新”故事。如熊亮的中國繪本系列《兔兒爺》,故事的開始設計一個快遞——兔兒爺,接著以北京城為背景,以兔兒爺為引線向讀者展現了老閣樓、老街道、老胡同,到現代化高樓大廈等建筑形象,表現北京歷史文化的變遷,為讀者勾勒出一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并存的北京城。又如《年》的繪本,故事中設計打電話的情節。《武松打虎》繪本雖然取材于文學名著橋段,但是故事主角卻換成了可愛的白貓與花貓。這些設計或改編讓孩子們讀起來更有親近感,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3.注重提煉故事的精神內核
所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在本土原創繪本的創作上卻不盡然。因為執著于民族傳統化的東西,會讓讀者群體局限于本民族孩子。那些缺少相應文化體驗和認知的非本民族的讀者,在接受上就會存在難度。因此,繪本創作應立足本民族傳統,提煉存在于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中的精神內核,如愛、勇氣、自由、生與死等超越民族,甚至國界的創作母題,可以讓更多孩子能理解和接受這樣的作品。
(三)圖文并重,強化圖畫的敘事功能
松居直先生將繪本定義為“繪本=圖×文”。繪本中的圖畫存在不是單純地配合和解釋文字,而是另一條能講故事的“線”。繪本因為圖的講述,才讓故事變得更直觀、更豐滿。那么,作為廣西原創兒童繪本的創作者,如何在既有的故事文本基礎上,發揮圖畫的敘事功能呢?具體做法如下。
1.設計有認同感的形象
兒童閱讀繪本的過程,就是將自身情感投射到繪本角色的過程。越是接近兒童特征的角色,如繪本中的小朋友或小動物,就越能夠獲得孩子們的認同。如《大衛,不可以》系列繪本,那個大大的腦袋、尖尖牙齒的小朋友大衛,他常常做出各種讓人哭笑不得,又非常“小孩子”的惡作劇來,如吃飯玩食物,洗澡玩海盜游戲把水弄得到處都是,玩得滿身泥巴就往客廳里走,洗完澡光著身子跑出去玩等,孩子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太多自己的影子,自然會對這本繪本產生共鳴,愛不釋手。
2.布置圖畫中的閱讀線索
與故事文本一樣,繪本中的圖畫也是可以“講”故事,這需要創作者布置一些閱讀線索將畫與畫連貫起來,引導讀者慢慢走進故事。線索可以有很多種,有明線,也有暗線。如由法國塞吉·布羅什繪圖的繪本《我等待……》,一條“紅線”貫穿全書。通過這條線,畫家用其驚人的表現力,為我們展現一個有關成長、快樂、愛、痛苦和悲傷等豐滿的人的一生,讓人回味無窮。又如王家珠的繪本《巨人和春天》,在頁與頁的銜接上都布置了線索,每一頁都為下一頁埋下伏筆,讓故事講述變得水到渠成。
3.表現言外之意
兒童閱讀繪本,觀賞圖畫在忠于原文的基礎上,還可以探索和發展文字的“言外之意”。著名兒童繪本畫家桑達克說過:“你絕對不能完完全全如實照文本作畫,而是必須在文本之中尋找圖畫可以發揮的空間。”如日本佐野洋子的繪本《活了100萬次的貓》,其結局是“虎斑貓靜靜地、一動不動地躺倒在了白貓的身邊。他再也沒有活過來”,配圖并不是虎斑貓與白貓互相偎依躺在一起死掉的畫面,而是一幅安靜的風景畫。這幅風景畫讓故事的結局變得平靜,也讓“死”變得不再悲傷。虎斑貓死了,但這只獨特的貓活在了每個小讀者的心里,這就是圖畫的魅力。
繪本是為兒童而創作的書,創作者應當站在兒童的視角,用兒童能夠接受和喜歡的方式來講故事。廣西原創兒童繪本,已經在探索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道路上啟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不斷突破困境,為孩子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繪本作品。
【參考文獻】
[1][日]松居直.幸福的種子:親子共讀圖畫書[M].劉滌昭,譯.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8
[2]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9
[3]諸葛蔓.廣西壯族民俗文化在兒童繪本中傳承的多維探索[J].藝術科技,2019(12)
[4]鄭萬林,夏林蘋.廣西當代本土繪本藝術語言的民族化表達探究[J].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10)
[5]帥靜泉.廣西壯族民俗文化在當代繪本創作中的傳承研究[J].大眾文藝,2017(1)
注:本文系2018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廣西壯族民俗文化在兒童繪本創作中的應用研究”(課題編號:2018KY0931)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諸葛蔓(1986— ),女,廣西桂林人,講師,碩士研究生學歷,研究方向:學前美術教育。
(責編 楊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