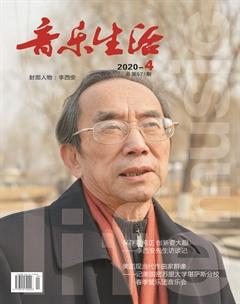地域文化視角下疍家“水上民歌”解讀與分類
陳錦霞 郭建民
一、疍家“水上民歌”解讀
千百年來,疍家人在創造了海上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創造了疍家歌謠。疍家歌謠亦稱“咸水歌”、“水上民歌”和“南海情歌”,委婉動聽的歌謠不僅再現了早年疍家人遷徙漂流的真實歷史,而且內容包羅萬象,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宗教、家庭、愛情、民俗等各方面,特色鮮明、內容廣泛、形式多樣,她是中國南海民歌中的寶貴文化遺產。
疍家人常年遷徙和海上漂流的歷史促成了“水上民歌”具有多地語言混合的鮮明特性,音調聲腔也同樣豐富多樣,演唱中可以根據不同內容采相應的音調和聲腔,其中分為喜調和悲調,聲腔分別為:水仙花、咕里梅、木耳絲、嘆家姐和古人頭。音調聲腔分類明晰、旋律婉轉動聽,極賦感染力。
分布在“兩廣”、福建、海南等地的疍家人因為生活環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音樂風格的“水上民歌”,呈現異曲同工、迥然相異的藝術特征。比如:南海熱帶海域變幻莫測的熱帶氣候,練就了海南疍家人堅忍不拔和沉著冷靜的性格,海南疍家“水上民歌”使用粵語+瓊語+疍家白話演唱,語言集三家所長、獨具地域風味,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歷史價值、社會價值和傳播價值。但是,關于疍家人創造的“水上民歌”解讀與分類,一直以來被人們忽略,造成了其概念混淆分類不清的窘況。
關于疍家“水上民歌”,史學界和音樂界說法不一,至今沒有為其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解讀和系統整合分類。究其緣由,與疍家人的漫長跨地域的流亡史、遷移史以及較為復雜的身份變遷有關;與疍家人極為復雜多樣化的族群構成有關;與疍家人居住地域分布的廣泛和分散有關系。上述原因造成了相關研究者從不同視角和維度對疍家“水上民歌”給予了迥然相異的解讀,對其分類甚至出現了“胡子眉毛一起抓”的現象。
長此以往,對于疍家“水上民歌”歷史文化、傳承傳播以及音樂產業項目開發利用等諸多方面,會造成許多不良影響。具體分析,其一,疍家“水上民歌”將沒有一個較為準確而合理且學術界一致認同的解讀和分類,造成傳播領域的諸多誤解,進而影響包括社會和學校的教育與傳播;其二,此狀態對于疍家“水上民歌”深入細致的理論研究、藝術創作、舞臺實踐極為不利,進而影響疍家“水上民歌”文化產業開發與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疍家“水上民歌”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其理論研究熱度的不斷提升,同時民歌文化產業開發與利用不斷發展,特別是處在當下海南“國際旅游度假島”、“國際自貿區建設”國家戰略逐步實施,如何進一步挖掘整理、傳承好、利用好疍家“水上民歌”這個海南地方傳統特色音樂文化遺產,認真梳理、整合和全面解讀疍家“水上民歌”,成為當下海南地方歷史文化與傳播研究的當務之急,深入挖掘整理地方傳統音樂的歷史文化、傳承、傳播地方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每一位音樂文化研究工作者共同的責任和義務。
城市現代化、工業化、信息化以及商品經濟的步步深入發展,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歷史文化的產業開發和利用具有巨大的潛力,比如:將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歷史文化研究成果編創為大型演藝項目,或編創為文學藝術、電影、電視藝術等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極具地域特色的音樂歷史和文化定夠吸引每一年前來海南三亞觀光、旅游、度假、康養人群——230萬人(仍在逐年增長)的目光,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衍生成城市旅游演藝文化產業項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另一方面來說,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文化一旦進入商品化和產業化的運行軌道,發展為城市文化演藝產業項目,必然進一步豐富和刺激海南三亞及周邊地區旅游產業演藝文化的“業態化”,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文化商品一旦進入蓬勃興起的城市演藝文化產業鏈條,必然涌進波濤洶涌的商品經濟大潮,從而引發包括海南地方的民歌表演系統、創作系統、傳播系統、教育系統及其文化消費、服務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進而衍生出與其相關的一系列文化產業系列產品。面對這樣的狀況,海南疍家“水上民歌”作為一種音樂形態,其音樂概念、審美觀念、文化意韻、文化定勢、藝術風格以及表演方式等方面,正面臨著新的歷史時期和發展機遇,同時也期待著學界給予她一個新的定位、新的闡釋和新的解讀!
至此,我們可以認為,疍家“水上民歌”,作為中國漢族民歌的一個部分,伴隨著涌動的時代大潮,伴隨著人類對生存和理想的不懈追求,伴隨著當代社會精神文明發展前進的步履,其文化的積淀和音樂成果的集結,進入到一個厚積薄發的歷史時期。
海南疍家“水上民歌”與廣東、廣西、福建等地的咸水歌一脈相承,其音樂豐富多彩且獨具海洋特色,內容浩如煙海,形式豐富多樣,作為海南疍家人口耳相傳的“水上民歌”,不僅是祖國海洋文化寶庫中閃耀奪目的奇珍異寶,也是中國南海熱帶海洋音樂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筆者在大量相關歷史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多次深入海南三亞、陵水、崖州、海口及周邊疍家人生活的海域進行深入田野考察,產生了諸多疑惑和思考,千百年來,疍家人用生命創造的“水上民歌”,其解讀和分類為什么會如此繁雜?流傳于廣東、廣西、福建和海南等地的“水上民歌”的解讀和分類各抒己見,究竟哪一個更準確?
疍家“水上民歌”廣義化的現象對于國內的大眾音樂生活有益無害,但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一種民歌表演形式的概念長期處于模糊、隨意定義的狀況,將不利于這一體裁自身的發展與傳播。比如某單位舉辦聲樂藝術培訓,社會大眾在培訓中,可以不了解歌唱表演藝術的體系,甚至可以不清楚美聲、民族、通俗每一種唱法的風格特點。但若培訓機構和教師也不知道或說不清三者的定義、風格特點及其演變的由來,在對歌唱藝術的發展和創新時就缺少了理論的支撐,在教學中將難以服眾,甚至失去大眾的信任。此種情況放在聲樂比賽中更是無法體現出比賽的學術性和公平性。
前已所述,“兩廣”、福建、海南對于疍家歌謠的解讀,至今沿襲著各地的慣性思維。因此,疍家“水上民歌”解讀和分類的理論依據是疍家人遷徙漂流的歷史敘事,以及海洋文化對“水上民歌”風格的直接影響。其一,流傳于廣東、廣西、福建與海南的疍家“水上民歌”同屬于疍家人所創造,但由于各地不同的海洋環境和氣候特點,促成了各地“水上民歌”既異曲同工又迥然相異的藝術特征。簡單粗略或者隨意地用一段話介紹各地“水上民歌”的內涵,太過草率,也無法對其風格類型全面關照;其二,根據流傳于各地疍家“水上民歌”的音樂風格,有必要將其進行系統整合與分類;其三,有必要對各地疍家“水上民歌”特征和功能進行深入論述和剖析;其四,在海南“國際旅游文化中心”建設的戰略規劃背景下,海南疍家“水上民歌”需要更深層次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其五,在“兩廣”、福建疍家“水上民歌”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的前提下,海南疍家“水上民歌”的解讀和分類將成為其研究的基礎。
根據以上五點篩選理論依據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度研究,圍繞疍家“水上民歌”產生的環境和歷史,結合音樂風格、特質及類型等,展開全面細致地整合和分類,并進行符合邏輯地全面解讀,這是疍家“水上民歌”歷史文化與傳播研究的重要前提。
十分有趣的是,海南三亞、陵水等地對于疍家“水上民歌”的解讀也不盡相同,其一,三亞定義為疍家人創作的疍歌,大概是為了區別于廣東疍家“咸水歌”(2019年三亞市申報國家“非遺”的名字,當時筆者作為指導專家曾提出不同意見);其二,陵水定直接解讀為疍家人在海上唱的疍家調;其三,部分傳承人和崖州疍家人解讀為疍家人之間相互傳唱的歌謠;其四,部分文獻資料解讀是從廣東漂流到海南的疍家人演唱的“水上民歌”、“南海情歌”、“流浪者之歌”、“疍民音樂”等。
筆者在對海南疍家“水上民歌”音樂形態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其特征和功能,整合歸納起來解讀:“海南‘水上民歌是疍家人海上生活勞動的結晶,是疍家人發自內心深處的‘海上圣詠,數量龐大的‘水上民歌講述著疍家人遷徙漂流的歷史敘事,再現了疍家人生活與民歌真情互動中的痛苦和快樂。”
二、疍家“水上民歌”分類
如果按照疍家“水上民歌”的歷史成因,結合疍家“水上民歌”音樂特征和功能進行分析和整合,借鑒和運用地域文化研究方法,對其分類的思路就變得清晰起來。
根據筆者多次田野考察和對傳承人的采訪,對搜集到疍家“水上民歌”展開研究,首先對其音樂形態進行深入細致地分析,接著根據音樂風格和表演樣式深入細致地分析比較和分類。由此筆者認為:如果簡單地沿用廣東對咸水歌的慣性思維,對待廣西、福建、海南等不同海域的“水上民歌”,無法實現細致和全面的解讀和分類,更有生搬硬套之嫌,造成“兩廣”、福建和海南等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產生的咸水歌,其音樂風格和表演樣式,產生一樣的解讀和分類,況且,如果忽略了各地“水上民歌”音樂形態和風格特征生成的地域環境、氣候特點等重要因素,疍家“水上民歌”的歷史和文化內涵,不僅難以全面解讀,“水上民歌”的風格樣式整合分類也無從入手。筆者以海南為例,“海南地處中國南海海域的最南端,屬于熱帶海洋氣候,1988年已經從廣東完全分離獨立建省,那么,海南疍家人所創造的“水上民歌”就應該有屬于自己的名字,南海熱帶海域的疍家“水上民歌”,應該有凸顯自身地域特色的理論解讀和比較合理清晰的整合歸類。”
再者,全國各地民歌,尤其是少數民族民歌大多以“原地名+民歌”來命名;比如海南黎族民歌、山西左權民歌、河南豫西民歌等。如果按照這個約定俗成的理念,就成了“海南疍家民歌”、“廣東疍家民歌”或者“廣西疍家民歌”、“廣西疍家民歌”,這樣的命名看似簡單明了,但關于廣西、福建和海南等地的咸水歌是在傳承了廣東文化基因基礎上發展并逐步自成體系的問題,無法全面概括和體現。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海域的氣候特點促成了疍家“水上民歌”音樂文化特質,加之疍民常年隨海上季風漂流,居無定所,分布極為廣泛和分散,“水上民歌”的歷史成因與元素構成復雜,因此,一以概之的解讀和分類顯然不妥。
廣西疍家音樂文化學者黃妙秋認為:疍家音樂發展過程中,由于疍家人所表達的內容越來越來越豐富,身邊故事和人物也融入其中,因此,疍家音樂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一定的劇情和人物表達的敘事與劇目形式出現,這也進一步證實了稍后疍家音樂具有敘事性藝術特征以及音樂劇目雛形的歷史成因。同時,天資聰慧的疍家歌者有時候也會根據不同演出場域、不同觀眾的審美需要,恰到好處地選擇與其相互對應的“水上民歌”類型,演唱表演中,在4~5個音調中即興發揮、靈活轉換,自如流暢,常常即興發揮成一首多段曲式結構,來表現豐富生活內容,看似簡單的“水上民歌”被疍家人演繹得多姿多彩。
為了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筆者對海南疍家“水上民歌”部分作品音樂形態的進行了進一步地深入分析和研究,結果表明:海南疍家“水上民歌”已經具有“講述故事、表達人物”等戲劇構建的基礎要素。一首動人心弦的海南疍家“水上民歌”已經發展到可以使用“多種音調(聲腔)、多段結構曲式”的表達形式。比如《哭嫁調》、《青樓悲曲》等,其中有較為完整的故事、情節以及各種人物角色,這也許正是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流傳千百年至今仍生命力旺盛的原因之一吧。
事實上,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生成和發展,首先需要對自身不斷完善并注入新鮮的內容,從而促進其表現形式的變化和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夠日臻完美并獲得大眾的認可。這再次證明用所謂的“疍家歌謠”、“咸水歌”、“疍歌”以及“疍家調”等代稱對海南疍家“水上民歌”進行的概括可以說是極其不恰當。這般簡單的命名和解讀已不能夠完全概括其“有歌、有戲、有敘事、有劇情”——即“歌中有戲、戲中有歌”的豐富內容和生動的表現形式。
為了進一步考證海南疍家“水上民歌”敘事劇目特征的佐證,筆者專程到三亞大東海海域和陵水疍家“水上民歌”傳承人家中,進行了實地考察,認真聆聽和記錄傳承人郭亞清、郭世榮、鄭石彩等演唱的海南疍家“水上民歌”與敘事曲目,比如《青樓悲曲》、《百孝為先》、《哭嫁》等,幅度長,有人物、有故事、也有簡單劇情,尤其是《哭嫁》一曲中,旋律曲折冗長、悠揚感人,有別于疍家歌謠單段體吟誦調,根據人物和劇情的需要,運用多個聲腔曲調轉換,旋律跌宕起伏豐富多彩,根據劇中人物角色需要,獨唱、對唱、小合唱多種表演形式混合,表演有說道白和人物對話,人物表情和動作符合故事和情節需要,已具有劇目特征。
據此,伴隨著海南疍家“水上民歌”的深入發掘和整理,筆者以為:“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從微觀層面看,以往將疍家“水上民歌”簡單地以‘咸水歌‘疍家調或‘疍歌的命名已不能夠完全概括其豐富的內容和風格樣式。咸水歌、水上民歌、疍家歌謠,三者從內容到形式都難以全面解讀和闡釋其中的基本屬性和文化內涵。筆者以為,在海洋文化視域下,結合疍家人遷徙漂流的歷史背景,將疍家人所創作的民歌解讀為南海“水上民歌”比較合適。根據不同樣式,歸納為三種類型:其一,疍家歌謠類——以口語化吟誦式為演唱特征,結構簡單、篇幅短小(大多為單段體結構),依據地名+疍家+歌謠來解讀;其二,水上民歌類——以演唱與表演相結合為基本特征,音樂形態、其三,劇目類:曲式結構相對復雜、表現內容相對豐富,篇幅相對較長,依據地名+疍家+水上民歌+劇目來解讀。
比如:海南疍家歌謠、水上民歌、敘事劇目;廣東疍家歌謠、水上民歌、敘事劇目;福建疍家歌謠、水上民歌、敘事劇目;和廣西疍家歌謠、水上民歌、敘事劇目等。顯而易見,這樣的分類和解讀相對簡練概括客觀合理。”
本文屬于國家大創《基于海南地方傳統文化傳承傳播:大學生疍家音樂演藝團》項目編號:201913892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