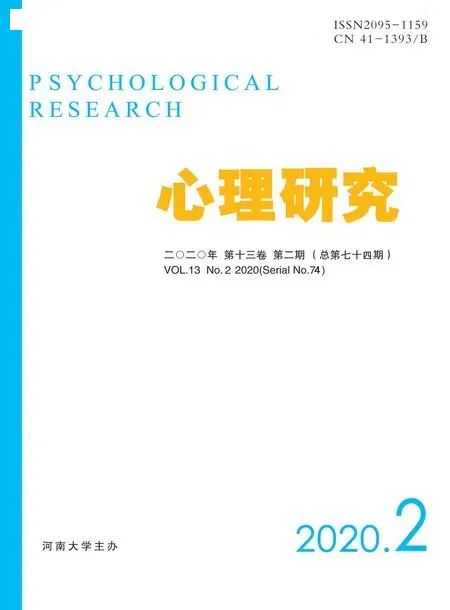移動社交媒介對受導師排斥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周 莉 王宏霞 王興超 雷 靂
(1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咨詢中心,北京100872;2 中國人民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北京100872;3 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太原030006)
作為高等教育的最高階段, 研究生教育肩負著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為國家培訓高級專業人員的任務。隨著我國當前就業的嚴峻形勢,研究生在學業、就業等方面面臨著諸多問題,隨之產生的心理問題也逐漸增多, 因此近年來學者們逐漸增加了對研究生心理狀況的關注。
國內外對人際接受拒絕的研究表明, 人際關系的質量可以預測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Rohner &Lansford, 2017)。 文書鋒和俞國良(2008)對研究生新生心理健康狀況的普查顯示, 人際敏感是研究生心理狀況問題發生率較高的因子之一。 Boyce 和Parker(1989)將人際敏感定義為一種人格特質,這種特質導致人們誤解他人的態度和行為。 人際敏感也可以指在人際關系中害怕他人可能的拒絕或批評(Bell & Freeman, 2014)。 這種人際間的不被接納,就是社會心理學領域所研究的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是指在社會互動過程中, 由于遭受某群體或個體的排斥或拒絕, 人們的歸屬需要和關系需要無法得到滿足的現象和過程。社會排斥有多種表現形式,如排斥、拒絕、孤立等等(陳晨, 楊付, 李永強, 2017;杜建政, 夏冰麗, 2008)。社會排斥的發出者可能是同伴或父母,也可能是老師。以往研究中學者們主要關注同伴排斥或父母排斥, 從老師對學生的排斥角度進行的研究較為缺乏, 但有很多關于師生關系對學生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表明, 師生關系的質量嚴重影響著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黨清秀, 李英, 張寶山, 2016; Han, Z., Fu, M., Liu, C.,& Guo, 2018)。 雖然研究生已經成年,但是學者們依然發現和導師的關系會對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產生明顯的影響, 師生關系的和諧健康是保證研究生培養質量的關鍵因素(文書鋒, 2011)。 研究生和導師的聯系頻率與研究生的抑郁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高志利, 2009)。 導師的辱虐型指導方式與研究生的沖動性行為和非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呈顯著正相關(倪士光, 楊瑞東, 董蕊, 王茹婧, 2015)。 研究生群體當中確實存在“怕導師”現象,即研究生害怕來自導師的負面評價 (魯銥, 李曄, 2014; Ma &Han, 2009; Liew, Ma, Han, & Aziz -Zadeh,2011)。我國大多數高校實行導師負責的研究生培養方式,因此研究生教育階段,研究生和其導師的關系是較為重要的一種人際關系。 如果導師忽視、拒絕、排斥學生,即發生導師排斥,那么可能導致研究生無法身心愉快地學習和生活,并產生不良的心理影響。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即使是短暫的社會拒絕經歷(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也會改變個人的自我調節能力, 從而增加不健康行為的風險(Salvy & Bowker, 2014; Vandewalle, Moens, &Braet, 2014)。 以往研究通過對遭受社會排斥的人群研究發現, 被排斥者認知過程受損(彭蘇浩, 陶丹, 冷玥, 鄧慧華, 2019),情緒糟糕、抑郁、無價值感 (Fossati, 2019), 引發 暴力行 為和自 殺 行為(Gabbiadini & Riva, 2018; Olie & Courtet,2018), 甚 至 槍 擊 (Leary, Kowalski, Smith, &Phillips, 2003)。 需要—威脅的時間模型認為遭受社會排斥的個體在最初監測到排斥時, 隨即引發個體條件反射般的痛苦。 這種痛苦會產生兩種負性情緒: 悲傷和憤怒。 在排斥初期個體往往行為反應激烈,表現出侵略性的反社會行為,如攻擊性行為。 此外長期的社會排斥還高度預測抑郁、社交焦慮、孤獨等心理困擾, 這些影響在慢性作用中都會造成個體習得性無助, 降低對自身價值評價或當前生活質量感受(陳建, 趙軼然, 陳晨, 時勘, 2018)。 大量的研究表明感知到的社會排斥不僅會引發個體的負性情緒(如抑郁、攻擊性等),影響心理健康,同時也會改變個體對生活和工作的感知與評價(如生活滿意度下降)。 研究發現,排斥與抑郁癥狀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個體感知到的排斥能顯著預測抑郁癥狀,個人感知到的排斥越多,其報告的焦慮和抑郁癥狀也越多(金童林, 張璐, 烏云特娜, 楊宏, 蘇田, 黃明明,2019; 雷玉菊, 張晨艷, 牛更楓, 童媛添, 田媛,周宗奎, 2018)。 此外,一些實驗研究、相關研究和追蹤研究均證實社會排斥經歷會誘發攻擊性(Leary,Twenge, & Quinlivan, 2006; Reiter-Scheidl et al.,2018; Twenge & Campbell, 2003),降低生活滿意度水平(陳建, 趙軼然, 陳晨, 時勘, 2018; Bastian et al., 2 014; Meagher & Marsh, 2017; Paolini et al., 2016)。 據此,提出本研究假設H1:導師排斥會對研究生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增加其抑郁和攻擊性水平,降低其生活滿意度。
移動社交媒介是社交媒介的一類, 是以移動設備為載體的傳統社交媒介及具有社交功能的專門的軟件,比如手機短信、Facebook、Twitter、微博、QQ、微信、陌陌等。 移動社交媒介伴隨其匿名性、不同步性和易得到性,還有平等性、開放性、動態性、便利性、逃避現實性和弱聯系性等顯著特點在現在的社會中非常普遍,人們使用越來越頻繁,需求也越來越強烈(王偉, 雷靂, 2015)。需要—威脅時間模型認為,在反思階段個體會采取不同方式來應對社會排斥(Ren, Wesselmann, & Williams, 2018; Williams,2009)。其中有些個體會積極尋求與其他個體及社交團體的聯系,嘗試重新建立社會連接,這種反應趨勢是由人類對歸屬感和關聯感的本能需求所決定的(Knausenberger & Echterhoff, 2018; White et al.,2016)。 當一個人體驗到孤獨和排斥,能夠創造人際關系的來源是非常重要的(Sheldon, Abad, & Hinsch, 2011)。為了重新建立起歸屬感,被排斥的個體通常會對積極的社會接觸更加感興趣 (Williams &Nida, 2011)。 在網絡時代,人們可以通過使用在線社交媒介獲得社會接觸感, 當他們覺得受到其他人的排斥后, 他們能通過參與在線社交媒介來獲得更多社會聯系, 從而緩解排斥帶來的不良影響(Sheldon, Abad, & Hinsch, 2011)。 以往一些國內外研究也發現了個體遭受排斥后移動社交媒介的使用可以幫助個體減少歸屬需要威脅, 有效減輕社會排斥的痛苦體驗(Chiou, Lee, & Liao, 2015; Lin, Li,& Qu, 2017)。在移動社交媒介如此普遍的今天,我們猜測, 研究生會通過使用移動社交媒介保持與親朋好友的聯系。那些遭到導師忽視、拒絕或者排擠的學生, 移動社交媒介可能成為其保持社交聯系的一種途徑。
此外, 一些學者關于移動社交媒介對使用者心理健康影響的看法和結論符合“增進”假設,認為互聯網的使用能夠增加人們的社會聯系, 增加人際之間的親密程度, 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Kraut,Kiesler, Boneva, & Cummings, 2002)。 Lee, Noh和Koo(2013)認為個體孤獨體驗越多,幸福感越低,自我表露越多,而社會支持能夠積極影響幸福感。也就是說孤獨感水平較高的個體,其幸福感程度較低,但他們可以通過使用社交網絡進行自我表露以得到社會支持來提高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研究生感知到社會排斥之后, 他們可能會更關注能夠帶來歸屬感和接納感的群體, 而身邊距離最近的人群并不一定是能夠提供歸屬感和聯系感的, 有了網絡技術的發展, 通過社交媒介與自己最有歸屬感的人群進行聯系,成為了一種可能。移動社交媒介就是這樣的潛在資源,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設H2:移動社交媒介可以調節導師排斥對研究生抑郁、 攻擊性與生活滿意度的不良影響。 具體假設模型見圖1。

圖1 假設模型圖
1 實驗一: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1.1 方法
1.1.1 被試
選取北京某大學二年級研究生61 名,隨機分配到排斥組31 名(男生16 人,女生15 人)和接納組30 名(男生15 人,女生15 人)。1 名排斥組男性被試由于問卷未完成而被剔除,剩余60 名有效被試。 被試年齡從22 到27 歲,平均年齡為23.67±1.03 歲。
1.1.2 研究工具
1.1.2.1 抑郁量表
研究采用Andersen(1994)的簡版流調中心抑郁量表(Shorten version of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epression Scale, CESD-10),10 個條目,4點計分,其中兩個條目為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說明抑郁水平越高。在本次調查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
1.1.2.2 攻擊性問卷
研究采用Buss-Perry(1992)攻擊問卷,該問卷從認知、情緒和行為三個維度評估個體的心理特征。原量表原來有30 個條目,由于原條目中很多行為和研究生中的實際生活差距較大, 我們選取了其中的10 個可能發生在研究生實際生活中的項目,用于測量研究生遭到導師排斥后的攻擊性。 量表采用李克特5 點評分法, 從1 到5 分別代表不可能發生到極可能發生,得分越高表示攻擊性水平越高。該量表有較好的信效度。在本次調查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
1.1.2.3 生活滿意度量表
研究采用Diener 等人(1985)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 該量表共包括5 個條目,如“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 量表采用李克特7 點評分法,從1到7 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滿意度水平越高。 Diener 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該量表在測量生活滿意度方面信效度良好。在本次調查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0。
1.1.3 研究程序
被試來到實驗室首先填寫年齡、性別、專業等人口學資料, 并告知被試實驗目的是希望通過了解人們的真實經歷開發實驗材料。 隨后參照Mead 等人(2011)以及王紫薇和涂平(2014)研究中對社會排斥的操控,采用回憶范式激活被試的導師排斥體驗。排斥組被試回憶并寫下一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印象最為深刻的或是最近發生的被導師排斥的事件, 接納組回憶被導師接納的事件。 描述內容包括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場景、導師的神情、語氣、自己的感受等;描述越詳細越好,字數不低于200 字。 然后進行排斥操控檢驗,讓被試評價此刻的排斥體驗,用數字1~7 代表,7 點計分。 最后完成抑郁量表、攻擊性問卷、生活滿意度量表的測查。
1.2 結果與分析
1.2.1 操縱的有效性檢驗
通過對兩個組被試的排斥體驗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排斥組的排斥體驗得分(2.82±1.29)顯著高于接納組(1.23±0.66),t=6.05,p<0.05。 這表明,通過回憶范式激活被試排斥體驗的操縱是有效的。
1.2.2 導師排斥組和導師接納組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差異
為了探討排斥組和接納組研究生的抑郁、 攻擊性和生活滿意度的差異,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對接納組和排斥組被試的抑郁、 攻擊性和生活滿意度進行檢驗,具體結果見表1。 通過檢驗發現:排斥組的攻擊性得分顯著高于接納組,t=2.38,p<0.05;兩組被試的生活滿意度得分達到邊緣顯著,t=1.89,p=0.06;抑郁得分沒有顯著差異,t=0.67,p=0.51。
實驗一探討了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響,選取抑郁、生活滿意度和攻擊性作為因變量指標。 結果表明,實驗室激活的導師排斥感知體驗確實能夠導致攻擊水平的提高,這與我們的假設是一致的。 但是研究結果也發現,激活排斥體驗或接納體驗后,兩組被試在抑郁和生活滿意度得分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有研究認為,當一個人體驗到孤獨和排斥,為了重新建立起歸屬感,被排斥的個體通常會對積極的社會接觸更加感興趣以尋求與其他個體及社交團體的聯系(Williams & Nida, 2011)。 那么,是否意味著在網絡時代,被導師排斥的研究生通過使用在線社交媒介來獲得更多社會聯系,從而緩解排斥帶來的不良影響呢? 基于此,在實驗一的基礎上,實驗二進一步納入移動社交媒介這一變量,考察移動社交媒介在導師排斥感知與研究生心理健康關系中的作用。
2 實驗二: 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移動社交媒介的調節作用
2.1 方法
2.1.1 被試
選取北京某大學二年級研究生104 名, 隨機分配到社交媒介組35 名、游戲組35 名、控制組34 名。6 名被試因不能回憶導師排斥事件而未完成實驗,4名被試由于問卷完成不完整被剔除,3 名被試由于猜測出實驗目的而被剔除, 剩余90 名有效被試,社交組(男生15 人,女生15 人)、游戲組(男生13 人,女生17 人)和對照組(男生16 人,女生14 人)各30名。被試年齡從22 到27 歲,平均年齡為23.69±1.07歲。

表1 排斥組和接納組心理健康量表得分
2.1.2 研究工具
2.1.2.1 抑郁量表:同實驗一。
2.1.2.2 攻擊性問卷:同實驗一。
2.1.2.3 生活滿意度量表:同實驗一。
2.1.3 研究程序
被試來到實驗室首先填寫年齡、性別、專業等人口學資料, 并告知被試實驗目的是希望通過了解人們的真實經歷開發實驗材料。 采用實驗一的回憶范式激活被試的導師排斥感知體驗, 測量被試的狀態攻擊性、抑郁、生活滿意度水平,此為前測。指導語為“請根據你此時此刻的感受填寫以下問卷”。 隨后將被試隨機分為3 組,接受不同的實驗處理。移動社交媒介組的被試(簡稱社交組)可以自由使用最常用的社交軟件(微信),時間為5 分鐘,可以任意聊天、瀏覽朋友圈等;單機游戲組的被試(簡稱游戲組)進行相同時間的手機單機游戲; 對照組被試閱讀一段中性材料,并回答相關問題,時間也為5 分鐘。 接著再次測量被試的攻擊性、抑郁、生活滿意度,指導語為“請根據你此時此刻的感受填寫以下問卷”, 此為后測。 填寫完問卷后,讓社交組被試寫下在5 分鐘內,具體做了哪些活動。 最后給予所有參與者被試費20元。
2.2 結果與分析
2.2.1 預分析
如前所述,剔除無效被試13 名,最終包含90 名有效被試,其中社交組30 名,游戲組30 名,對照組30 名。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三組被試的實驗室激活的導師排斥感知體驗分別為: 社交組3.44±1.51,游戲組3.02±1.02,對照組3.56±1.80,結果差異不顯著F(2,76)=0.90,p=0.41。 因此,實驗分組達到了隨機化的效果。
2.2.2 移動社交媒介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為了考察社交媒介在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心理健康中的影響作用,我們對研究生的抑郁、攻擊性和生活滿意度進行了前后測量。分別以抑郁得分、攻擊性得分和生活滿意度得分為因變量, 采用2 (時間:前測vs 后測)×3(分組:社交組vs 游戲組vs 對照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進行檢驗,結果見表2。

表2 研究生抑郁、攻擊性和生活滿意度的前后測得分
結果表明抑郁得分的時間主效應不顯著,F(1,174)=1.038,p =0.356; 分 組 主 效 應 不 顯 著,F(2,174)=0.208,p=0.649;交互作用顯著,F(2,174)=3.927,p<0.05。 分別從兩個方向對交互作用的效果進行分析。首先,對前后測三個組的抑郁得分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對于前測,三個組得分差異不顯著,F(2,174)=0.679,p=0.510;而對于后測,三個組差異顯著F(2,174)=3.744,p<0.05。兩兩比較結果顯示,社交組后測抑郁得分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 社交組與游戲組后測得分差異不顯著 (p=0786),游戲組與對照組后測得分差異也不顯著(p=0.157)。 其次,對每個組前后測得分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結果表明,對照組后測得分顯著高于前測(p<0.05),社交組前后測得分差異不顯著(p=0.161),游戲組前后測得分差異也不顯著(p<0.187)。
攻擊性得分的時間主效應顯著,F (1,174)=9.775,p<0.01,后測攻擊性水平顯著低于前測水平;分組主效應不顯著,F(2,174)=1.611,p=0.203;交互作用顯著,F(2,174)=3.263,p<0.05。 分別從兩個方向對交互作用的效果進行分析。首先,對前后測三個組的攻擊性得分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對于前測,三個組得分差異不顯著,F(2,174)=0.358,p=0.700; 而對于后測, 三個組差異顯著F (2,174)=3.892,p<0.05。 兩兩比較結果顯示,社交組后測攻擊性得分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游戲組后測得分也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而社交組與游戲組后測得分差異不顯著(p=0.828)。 其次,對每個組前后測得分進行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社交組和游戲組后測得分均顯著低于前測(p<0.01),對照組前后測得分差異不顯著(p=0.788)。
生活滿意度得分的時間主效應不顯著,F(1,174)=0.10,p =0.76; 分 組 主 效 應 不 顯 著,F(2,174)=1.12,p=0.33;交互作用不顯著,F(2,174)=1.84,p=0.17。
實驗二對移動社交媒介在導師排斥感知和研究生心理健康中的調節作用進行探討。結果表明,在使用移動社交媒介后, 社交組的抑郁水平并沒有顯著降低,對照組的抑郁水平卻顯著上升,但社交組的后測抑郁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在攻擊性得分上,社交組和游戲組在進行相應任務后, 其攻擊性水平都得到了顯著降低;但是對于生活滿意度,被試的前后測得分卻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兩個實驗探索導師排斥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發現導師排斥導致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并且移動社交媒介的使用可以調節導師排斥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實驗一結果表明,在實驗室情境下,回憶范式能夠有效啟動導師排斥感知體驗, 排斥組和接納組的排斥體驗有顯著差異,驗證了假設,表明采用回憶范式通過指示參與者回憶,從而重新體驗他們感到“被排斥或被忽視”的過去事件,能夠有效啟動研究生的導 師 排 斥 感 知 體 驗 (Dean, Wentworth, & Le,2019; Malik, & Obhi, 2019; Wang, & Lalwani,2019)。這種回憶范式更多地考察的是被試被排斥經歷的回憶, 是真正個體化的、 現實生活中的排斥經歷,誘導的排斥事件是與自我相關的,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獨特的意義, 因此具有較高的外部有效性(Godwin et al., 2014)。
通過回憶法所激發的導師排斥感知能夠顯著影響研究生的攻擊性,驗證了假設,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達到邊緣顯著,對抑郁沒有顯著影響。需要—威脅時間模型認為排斥在反射階段首先會產生一種直接的痛苦,在接下來的反思階段,排斥會威脅個體的一系列基本需要,如歸屬感、自尊、控制感和有意義的存在感,此時會產生相應的憤怒情緒,因此可能會導致攻擊性增強, 社會排斥被認為是最常見的攻擊性原因之一 (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7; Liu,Huo, Chen, & Song, 2018; Ren et al., 2018;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Warburton et al.,2006)。此外,研究表明社會排斥會觸發個體的“疼痛感”, 引發攻擊性反應 (Chen, DeWall, Poon, &Chen, 2012)。 在以往的實驗室實驗中,結果也表明被排斥者對排斥者和無辜旁觀者都表現出更高的攻擊 行 為 (Twenge et al., 2001; Buckley et al.,2004)。 本研究再次驗證了這一結果,發現導師排斥感知能夠顯著提高研究生的攻擊性。
社會排斥不僅危害個體的身心健康, 而且一旦被排斥的個體產生攻擊行為, 便會對社會的公共安全產生影響, 故而研究如何減少社會排斥帶來的負面影響顯得尤為重要。 實驗二在激發被試的導師排斥體驗后, 分別對三組被試進行不同的實驗處理發現,社交組被試后測的攻擊性水平顯著低于前測,游戲組后測的攻擊性水平也顯著低于前測, 而游戲組和社交組在攻擊性下降方面沒有差異。這說明,使用移動社交媒介和游戲, 都顯著緩解了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攻擊性的影響。需要—威脅時間模型認為,經歷排斥的個體在其歸屬需要受到威脅時, 他們很可能會積極尋求與其他個體及社交團體的聯系,嘗試重新建立社會聯結。Twenge 等人(2007)通過啟動范式就發現, 提醒遭到社會排斥的個體注意到自己擁有的社會聯系會降低攻擊行為 (Twenge et al.,2007)。Gardner, Pickett 和Brewer(2000)發現,遭受到社會排斥的個體會更多的回憶起與歸屬感相關的活動, 這表明社會排斥可能會增加對社會聯系的潛在來源的關注。近年來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移動社交媒介成為了人們維持社會關系的一種主要方式,根據社會重新聯結假說, 遭到社會排斥的個體會在接下來的團體任務中更努力,表現出更大的迎合性,因此被排斥個體會特別渴望與別人建立聯系來滿足歸屬需要。 一項針對國外最具有代表性的網絡社交媒體Facebook 的研究表明, 作為社會聯結來源的Facebook 可以對社會排斥個體產生積極作用,即僅僅是通過給被排斥者呈現Facebook 圖標,其攻擊性行 為 就 會 減 少 (Knowles, Haycock, & Shaikh,2015)。許多學者也關注到了網絡社交活動與社會排斥的關系, 考察了移動社交媒介的使用對社會排斥感知的影響并得出了與我們相一致的結果, 發現通過移動社交途徑來與其他個體或團體重新建立聯結, 在幫助個體從社會排斥的不良影響中恢復過來的重要作用 (Chiou, Lee, & Liao, 2015; Lin et al., 2017)。
此外, 我們還發現了電子游戲也能夠顯著緩解導師排斥感知對攻擊性的影響。 新近研究也表明電子游戲在幫助人們從排斥心理中恢復的作用(Tamplin -Wilson, Smith, Morgan, & Maras,2019)。事實上,研究表明,電子游戲能夠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 如自主需要、 能力和歸屬需要(Sailer,Hense, Mayr, & Mandl, 2017),改善玩家的社會、認 知、 情 緒 等 功 能 (Granic, Engles, & Lobel,2014),對心理健康有很大的治療作用(Horne-Moyer, Moyer, Messer, & Messer, 2014)。社會計量理論認為,個體的自尊是衡量人際關系的計量器,能激發個體采取行動,維持自己保持被接納的狀態。社會監控理論認為個體通過社會監控系統自然地監控他們周圍的社會線索(如眼神交流、面部表情),以引導個體糾正和從被排斥的經歷中恢復過來(Wesselmann et al., 2015; Picket & Gardener, 2005)。 因此, 一個排斥事件會降低個體的自尊水平從而提醒社會測量器,接納狀態已經受到威脅,這反過來激活了社會監控系統,并促使個體開始掃描他們的環境,尋找社會接納線索。 而被排斥者在電子游戲中能夠提高自尊感,抑制拒絕信息,并關注較少的負面社會信息從而恢復其情緒情感、自尊、基本需要,降低攻擊性水平等。
另外,本研究還有一個意外的結果,對照組后測的抑郁水平顯著上升, 這可能是因為激活導師排斥體驗后,對照組的被試沒有時間排解情緒,雖然只有5 分鐘時間,竟然使得抑郁明顯上升。 對照組的任務是完成中性的學習作業,內容與情緒無關,但被試需要集中注意力完成答題,類似于學業任務。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感知到導師排斥后的研究生,如果不采取某種緩解辦法,而直接進入學習狀態,對于自身的心理健康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以往研究表明不同的排斥誘導范式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排斥體驗,從而導致不同的心理結果 (Godwin et al., 2014),本研究采用回憶法啟動的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的抑郁水平不顯著,生活滿意度邊緣顯著,可能是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且研究生的掩飾性較高,難以真實回答。 通過回憶范式激發研究生的導師排斥體驗并要求他們寫下來,這個做法對于研究生來說,本身就非常敏感。雖然主試反復強調研究的保密性原則,但還是有很多研究生表現出不太自在的神情, 甚至有的研究生直接表達很擔心導師知道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嘗試探討不同的排斥反應范式(如回憶范式、 網絡投球范式、O-Cam 范式等)如何影響我們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社會排斥對個體產生的影響可能會存在時間效應, 因此個體在被排斥后可能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反應, 下一步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將時間范圍考慮進來, 分別探討研究生的導師排斥感知對狀態情緒和較長期的穩定特質情緒的影響。第三,本研究未對游戲組的單機游戲類型加以控制, 未來研究中我們可以對不同游戲類型對排斥行為的影響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繼續探索一些低成本且容易獲得的干預方法。
總之, 本研究結果發現移動社交媒介能緩解導師排斥感知對研究生攻擊性的影響, 這個結果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社交媒介的作用, 讓我們看到社交媒介在學生遭遇挫折時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鼓勵學生在遭遇挫折時,采取多途徑進行應對,特別是利用移動社交媒介進行自我表露或者尋找社會支持,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預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