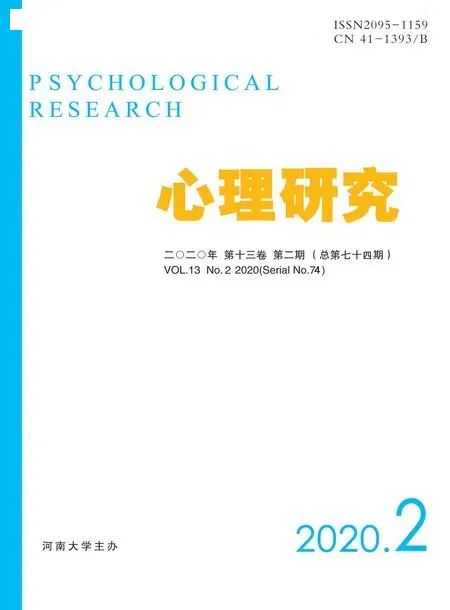論瓦雷拉神經現象學的邏輯困境
李莉莉 劉運全
(1 新疆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烏魯木齊830017;2 哈爾濱理工大學學生處,哈爾濱150080)
神經現象學是具身認知進路的提倡者之一瓦雷拉在20 世紀末提出的關于意識經驗的一種研究模式。 它基于現代心理學和認知科學一向忽視主體經驗維度的做法, 從而將第一人稱的現象學研究主題與第三人稱的神經科學研究路徑相結合, 試圖整合雙方的研究立場和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深入地反思這一做法, 就會發現這一整合進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其最初提出的問題,即“跨越意識研究的鴻溝,以解決意識的‘困難問題’”(Varela,1996)。 其原因不僅在于意識“困難問題”本身所隱含的哲學困境,也在于神經現象學的方法論糾葛。
1 具身認知進路的錯誤歸因
現代心理學的每一次危機都根源于那個在其成立之初的隱患, 那個在心理學家中甚至在所有將心智作為研究主題的科學家心中所信奉的方法論原則,即以實證的方法來研究意識的問題,以便突破傳統哲學研究的瓶頸, 并能在最大程度上促進心智科學的發展。 換句話說,在現代心理學家中“普遍流行著的一種嚴重錯誤的、 并往往不得不因此而要付出巨大的歷史代價的偏見或理論態度, 即無論是在研究方法、理論(體系的)形式,還是在思維方式等方面,都要拒斥和否棄哲學,似乎他們(的理論)對哲學的遠離同時也就意味著是對科學的接近”(高申春,2000)。 可以說,現代心理學發展的每一次轉折都是實驗心理學在誕生之初的這個隱患的危機性寫照,同時, 每一次應對危機的革命也因為這個隱患的殘留而無法在徹底的意義上真正消除危機。然而,這一決定心理學走向的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人們的充分重視,包括具身認知進路的提出者們。
20 世紀80 年代, 當早期認知科學的計算—表征立場使認知科學的發展陷入僵局時, 瓦雷拉等人將認知科學的問題歸結為科學與經驗的緊張關系,即認為早期認知科學“對日常的、活生生的情景中作為人類意味著什么幾乎什么也沒說”(Varela et al.,1991), 而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心智科學, 一方面把活生生的人類經驗和內在于人類經驗的轉化的可能性囊括其中,另一方面,一般的日常經驗要從心智科學已取得的清楚明確的洞見和所做的分析中獲益。從瓦雷拉等人的這一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看到了來自大眾對作為心智科學的心理學或認知科學的不滿, 這種不滿早在行為主義時代就已經出現了。 即人們日漸感覺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精神現象的學科,除了在心理治療中的技術應用外,幾乎無法為現實生活的人們提供任何有意義的經驗指導。 這種不滿情緒并未因認知心理學或認知科學取代行為主義而消除。于是,瓦雷拉等人將認知科學的發展困境與這種不滿聯系起來, 并認為二者的共同根源在于認知科學對人類經驗的忽視。因此,如果能夠將人類經驗納入認知科學的體系中, 那么就能將認知科學從困境中拯救出來, 并消除大眾對心理科學的不滿。 瓦雷拉等人認為自己準確把握到了問題的關鍵, 并努力塑造一種能夠在科學與經驗之間建立起循環關系的新的認知科學——具身認知進路。而實際上,此時瓦雷拉等人對認知科學問題的把握只是片面的。
由于心理學成為科學以來一直追求方法上的科學性, 從而使其不得不將研究局限在便于采用實證方法的主題上。或者更直接地說,這些便于采用實證方法的主題往往是來自第三人稱的觀察事實。 在這方面,行為主義表現得最為突出。雖然行為主義之后的認知科學開始關注內部過程,但是,這種內部過程絕非是第一人稱意義上的直接經驗, 而仍然是以便于觀察或便于進行實證研究的對象為主, 計算機程序隱喻就是這種方法論追求的最好立意, 在此基礎上,心理學家們爭相努力構建心理模型。這種研究對象對研究方法的適應使心理學以及認知科學在研究主題上偏廢了來自第一人稱主體的現象意識。 對于瓦雷拉等人而言,只要在主題上恢復這一研究對象,就可以超越早期認知科學的障礙。但事實上,現代心理學在研究主題上的偏廢是其追求實證科學身份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心理學對實證方法的應用使其不得不放棄對意識的現象性或主觀性的研究。 因為實證的研究方法在本質上與意識的現象性是對立的。 因此,在科學的視野中,如果僅僅在研究主題上恢復意識經驗的地位, 而不同時恢復與意識經驗相適應的方法, 那么現代心理學的根本問題就不會得到消除。 就像瓦雷拉等人最初所提倡的具身認知進路那樣。事實上,具身認知進路除了對早期認知科學提出了質疑和挑戰之外, 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關于意識經驗的新穎看法。 具身認知的提倡者們最后慢慢發現, 他們在主題上和研究思路上是多么依賴于以意識經驗為研究對象的現象學(Manganaro,2010)。這不僅體現在他們的具身認知觀得自于著名的現象學家梅洛—龐蒂, 而且瓦雷拉日后所提出的神經現象學在主題上同樣有賴于胡塞爾的時間意識現象學, 我們可以通過了解神經現象學的研究方案來進一步深入地理解這一點。
2 神經現象學的研究方案
2.1 以互惠約束應對意識的“困難問題”
1983 年,約瑟夫·列文在《太平洋哲學季刊》上發表題為《物理主義與感受性質:解釋的鴻溝》一文。文章指出, 在大腦的物理結構及功能與意識之間存在一個解釋的鴻溝,換言之,對結構和功能的物理說明不足以解釋意識(Levine,1983)。 此后,查莫斯在90 年代早期提出了所謂“意識的‘困難問題’”。 在他看來,對腦的結構和機制進行研究是容易的,而回答腦如何形成關于意識經驗的主觀性質的問題則是困難的(查莫斯,2013)。當然所謂意識的“困難問題”實際上是查莫斯從其物理主義的立場看待意識問題時因感到棘手和困惑而形成的提法。從根本而言,意識的“困難問題”是一個偽問題(李莉莉,2015)。在查莫斯提出這一問題之后不久, 瓦雷拉提出了應對這一問題的方案——神經現象學。
根據瓦雷拉的設想, 神經現象學旨在將來自第一人稱視角的(主觀體驗的、內在洞察的)與來自第三人稱視角的(自然科學的、觀察的)關于意識的資料結合起來, 將意識的“困難問題”“重構為在兩種‘不可通約’ 的現象性領域之間尋求有意義的橋梁(Barbaras,2002)。在這個意義上,神經現象學通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闡述‘困難’之義而成為對困難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Varela,1996)。 在瓦雷拉看來,關于意識的第一人稱視角的研究得自于胡塞爾及其他現象學家, 而第三人稱視角的研究來自于腦或身體的科學研究,二者的結合能夠使“體驗結構的現象學解釋與它們在認知科學中的對應部分通過互惠約束而相互關聯”(Varela,1996)。 對于這種 “互惠約束”,湯普森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 湯普森說,所謂“互惠約束”,“是指現象學分析有助于引導和塑造科學對意識的研究, 而科學發現反過來也有助于引導和塑造現象學研究”(湯普森,2013)。 瓦雷拉對自己的設想踐行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是, 他將胡塞爾對時間意識的分析用在意識的神經現象學進路中, 提供了一個關于時間意識的神經現象學解釋, 以此作為“對整個神經現象學事業的一個決定性檢驗”(Varela,1999)。
2.2 時間意識的現象學闡釋
以胡塞爾的時間意識概念為例, 胡塞爾認為存在著一種意識進程的時間, 它不同于客觀經驗世界的有關事物延續性的時間,而是一種內在時間。這種區分在這樣一個表達中最為鮮明, 即一個被體驗到的現在,就其本身而論,不是客觀時間的一個點,而是一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疊加物(胡塞爾,2009)。這與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觀點非常一致。 詹姆斯說,“實際被認知的當下并不是一個刀刃, 而是一個馬鞍, ……我們對時間的復合知覺單元是一個持續塊,有著一個船頭和一個船尾,好像是一個向后看以及一個向前看的端點。 我們并不是先感受到一個端點再感受到另一個, 然后從對該相繼性的知覺中推理出一個二者之間的間隙, 而是我們似乎將這個時間間隙感受為一個具有兩個端點的整體”(James,1981)。 以一段旋律為例,雖然聲音是一個一個響起的,但我們聽到或感知到一段旋律,而不是單個的當下的聲音。胡塞爾認為,這不能僅僅用“我有回憶”來說明這個旋律流逝了的部分對我而言是對象性的,也不能僅僅用“我有前瞻的期待”來說明我沒有預設這就是所有的聲音, 我們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事實上,胡塞爾認為時間意識包含三個機能,即原印象、滯留和前攝。原印象是對“聲音—現在”的意識,而現在這個聲音不斷地變化為一個過去,一再有新的“聲音—現在”來接替那個過渡到變異之中的聲音,不過那個過渡到變異之中的聲音并未消失, 而是為我們所持有,或者說我們仍在一種“滯留”中擁有它。如果對聲音—現在的意識、原印象過渡到滯留中,那么這個滯留本身又是一個現在、一個現時的此在者,它本身是現時的,同時它又是關于曾在的聲音的滯留。意識的每個現時的現在都從一個滯留轉變為另一個滯留,從不間斷,因而形成一個滯留的不斷連續,以至于以后的每個點對于以前的點來說都是滯留。 聲音響起,并且“它”不斷地響下去。“聲音—現在”變換為“聲音—曾在”, 印象意識流暢地向一再更新的滯留意識過渡。如果旋律成為過去的,那么我們在此生回憶中就將經歷與正在感知時相同的滯留串, 以及對尚未出現的聲音的期待或前攝。因此,像旋律這樣的時間客體只能在這樣一種形式中“被感知”,其所包含的時間區別就是在原意識、 滯留和前攝行為中被構造起來的(胡塞爾,2009)。
2.3 時間意識的神經動力學驗證
對于瓦雷拉而言, 神經現象學的任務就是將時間意識的現象學解釋與對意識的神經相關物的解釋以一種相互啟發的方式關聯起來。瓦雷拉認為,胡塞爾對時間意識的結構分析“與我們從物理學中習得的線性時間的點狀連續統表征并不一致。 但是它們確實與認知神經科學中的一系列結論有著天然的聯系, 即認為存在一種與一個認知事件關聯的神經事件所需要的最小時間。 這種不可壓縮的時間框架可以被分析為大腦中與廣泛的同步震蕩相關聯的一種長程神經整合的顯現”(Varela,1996)。 由此,瓦雷拉提議, 時間意識的現象學結構可以通過其動力學基礎的重構來闡明其性質,換句話說,時間意識的現象學結構可以通過動力系統理論的概念得以重新描述,而這些描述可以基于腦的生物特征來進行。事實上, 他的這一提議就是要為時間意識結構的現象學解釋提供“實證”。
瓦雷拉首先將現象學的時間意識結構轉化成神經動力學的描述。他假設:任何認知事件都有一個作為其涌現和運行基礎的單一而特定的神經集合,該神經集合是來自不同腦區域的大尺度整合, 具有某種時間編碼的特征。例如一個認知活動(知覺的或活動的狀態,流過的思想或記憶,或情緒評價等)完成所花費的時間大約是250~500 毫秒。 其相關的神經過程不僅跨越不同的腦區, 而且也跨越了一個時間段,瓦雷拉將這個時間段稱為1 尺度(1 scale)。而將基本感知運動花費的時間10~100 毫秒稱為1/10尺度,將記憶描述花費的時間稱為10 尺度。 這個大尺度整合的神經事件的時間編碼即相位同步(phase synchrony)。 由于認知事件是相繼發生的,因此相應的神經事件就會經歷大尺度的整合和解耦這樣的動態轉換, 也即相位的動態同步和去同步。 瓦雷拉認為, 相位的同步和去同步是我們體驗為當下認知時刻的神經基礎, 或者用神經動力學的可操作術語來講, 在1 尺度上的整合—放松 (integration-relaxation)過程是當下時刻的意識的嚴格相關物。以此為實驗假設, 瓦雷拉和他的同事進行了一個實驗研究用以闡釋這些觀點。
實驗以高對比度的黑白面孔的視覺識別作為當下時刻意識的范式例證, 向被試呈現正向或顛倒的黑白面孔圖。當正向呈現時,被試很容易將其識別為人臉,當顛倒呈現時,通常被試會將其知覺為無意義的黑白形式。 被試必須在看第一眼時盡可能快地決定他們知覺到的是不是一張臉。 在實驗過程中通過記錄被試的腦電圖(EEG)來獲得與有意識知覺相伴隨的腦區的同步活動。 結果顯示,在“知覺”條件與“無知覺”條件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在“知覺”到的情況下, 能夠觀察到一個顯著的1 尺度神經激活的同步化階段,而在“無知覺”的條件下卻沒有。在這個同步化階段之后是一個相位離散的階段,這表明,神經集合正在經歷解耦階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按照瓦雷拉的設想,神經現象學進路的研究模式“重又開啟了一條人類經驗與認知科學和諧共振的道路。 ……這首先要求對現象學描述的技能進行重新學習和掌握, 建立一種持久的現象學考察的傳統”(Varela,1996)。 這樣,從受到現象學訓練的被試那里收集第一人稱體驗的描述報告, 然后將這種來自第一人稱體驗的描述報告作為一種發現與意識關聯的生理過程的啟發策略。 神經現象學的研究規劃通過由經驗揭示的現象領域和由認知科學所建立的相關現象領域之間的相互約束來尋求接合點。
3 瓦雷拉神經現象學的實質: 方法論上的自負情結
從上述神經現象學的研究方案可以看出, 神經現象學并非是一種現象學研究, 即它并不是采納現象學的研究傳統來做進一步的探究, 而僅僅是主張其追隨者對現象學進行學習和掌握, 以為其神經動力學的描述提供“原料”,然后再采用實驗的方法提供相關的神經事實數據。 因此,從本質上來講,神經現象學并非是現象學,而是神經科學。 事實上,從認知科學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 神經現象學的研究方式更接近于認知神經科學, 因為對神經事件的研究不僅僅需要新的技術, 同樣需要理論。 如果沒有理論,任何觀測到的數據都是無意義的,這也是為什么近年來神經科學與早期計算表征立場的標準進路相結合的原因。 神經現象學將現象學與腦科學相聯結是出于同樣的動因。 即,一方面,它們在主題上依賴現象學,另一方面因為受實證精神的影響,不認同哲學的思辨式研究, 因此才會想到采用神經動力學的自然科學路徑驗證現象學的主題。
就目前來看, 神經現象學尚未成為一個系統而成熟的領域(張鐵山,2015),其所面臨的挑戰也將是嚴峻的(陳巍,郭本禹,2011)。對于神經現象學來說,一些質疑可能不可回避。第一,目前尚未發現神經現象學的研究在結論上有對現象學的突破(Slagter,Rawling,Francis,Greischar, & Davidson,2009;Quyen & Petitmengin,2002), 神經現象學研究如果只是對現象學結論的術語轉換和神經證實,那么,其獨特的研究價值是什么?第二,現有的神經現象學研究僅僅對現象學的第一人稱資料中的少數幾個主題做了考察,一個必然要提出的問題是,現象學的所有結論都能在技術上實現對應的神經動力學的同型解釋嗎?第三,神經現象學的目的在于橋接來自第一人稱的現象資料和第三人稱的腦科學資料, 然而從不同視角對同一事物進行的兩種描述有必要橋接嗎?從某種意義上講, 這種橋接的內在動力要么是對現象學研究方法的不認同, 要么是對基于第三人稱視角中腦科學研究的絕對自負,甚至兼而有之。 最后,正如國內研究者所言,“無論是將現象學還原‘前載’還是‘后載’于神經科學實驗,都很難在現象學數據與神經科學數據之間形成真正的、持續的互惠約束”(殷融,2016)。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瓦雷拉等人曾在《具身心智》一書中坦言,他們對新的心智科學的這種信念受啟發于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現象學中的具身性思想。而另一方面,由于瓦雷拉等人所墮于的自然科學背景,在他們看來,實證科學的方法較哲學或現象學的方法具有天然的優勢。 他們曾雄心壯志地意欲通過具身認知運動發起對傳統哲學的革命。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他們對胡塞爾現象學態度的轉變已經表明,他們最初的規劃失敗了。 事實上,現象學與心理科學或認知科學之間的關系不是主題和方法之間的關系, 而是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 自近代以來,對于人類心智就具有兩種不同的研究手段,一種是人們采用與自然科學對外部世界的觀察研究途徑相一致的腦機制研究, 一種是作為能夠思想和內省的人確立自身心靈存在時采用的省察途徑。 從神經現象學對現象學的主題依賴性便可知, 這兩種研究方案哪一種更具創建性。
從近代以來,在關于心靈的問題上,人們總被自己的兩種認識途徑所迷惑, 而在心—腦問題上陷入平行論,如笛卡爾。平行論引發的最為主要的動機就是, 人們總是努力想將兩個軌道的訊息對等并共存起來,如所謂的意識的“困難問題”和瓦雷拉的神經現象學。而實際上,除了病理學、診斷學、治療醫學的臨床意義和神經生理學對意識的神經機制的探索外,作為心理學家,并不需要了解每一種心理狀態或心理現象發生的同時在我們頭腦中生理事件的細節。 因此,神經科學與現象學的結合,既不是神經科學的必然需要,也不是現象學的必然需要,而僅僅是某些對哲學研究方法不認同, 又對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盲目崇拜的人所制造的一種思想怪胎。 瓦雷拉之所以會從具身認知進路進展到神經現象學, 并對現象學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Thompson,2004),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早先在方法論上的盲目自負,同時又缺乏對人的心理或意識本質的深刻理解。今天, 這種方法論上的自負情結仍然在很多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的研究者身上起著作用, 它已經成為我們進行真正的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障礙。 我們必須看到,只有重新恢復哲學的或現象學的方法論地位,重新增補心理學的哲學厚度, 才能使我們在對意識的本質理解中獲得長足的進步。